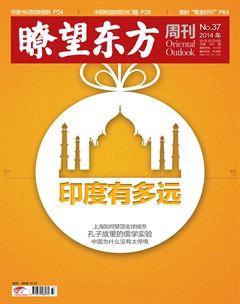这里有很多追问、反思,也有无奈
周小丹+周范才


《瞭望东方周刊》:影片为什么会用“黄金时代”作为片名?
李樯:以“黄金时代”命名,未见得是要求大家达成什么是“黄金时代”的共识。这里有很多追问、反思,也有无奈,包含着非常多的东西。
我也并不想告诉大家那个时代就是“黄金时代”。你可以认为是,也可以认为不是,它变成了一个带有幻觉性的词。它是开放的,里面包含着很多解读。这个电影不过是在用一种中立、中性的态度讲述一个故事。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人物传记类电影常常都是一种流水账式的、没有高潮的剧情,《黄金时代》能避免这个问题吗?
李樯:我当时也想,难道我要从小到大这么写萧红么?那岂不是我写任何人物都是这样落入了窠臼?
后来我想到,时间不是线性的,而是过去、未来、现在一直并存的一种东西,它一直绵延在你的时空当中。已经逝去的人,我们通过阅读她、观望她,她就会一次次在我们现在的时空中复活,只不过我们是以肉身的形式存在,而他们不是,但是那个时空是并存的。
所以,我这次写萧红就用了一个这样的方式:我让过去、未来、现在,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出现,我不再是按照对过去凭吊式的、追忆式的、对既往时光打捞的方式去写她,而是让人物随时随地在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当中穿梭,而不太受时间的限制,她可以随时站在一个多重空间里展现自己。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年有很多“大片”推广很成功,但观众走进电影院就会发现这些“大片”连一个基本的故事都没讲好,这是因为缺少好剧本吗?
李樯: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都缺好剧本,不只是现在。找到好故事、讲好故事,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但好故事贫乏这个问题又不能只从单一层面去思考,要结合当下的社会环境,意识形态的、市场的环境。
就像我们历史上唐朝诗歌很兴盛,那也是因为当时提供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历史背景、文化土壤、政治背景,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很综合、很大的背景下的问题,要观望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创作的空间、自由的程度,以及时代提供给你的可生活、可借鉴、可利用的创作资源,这都是非常复杂的,而不能只是单纯地指责现在所谓蓬勃的商业环境。
《瞭望东方周刊》:《孔雀》《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立春》以及《黄金时代》都是你的原创剧本,但中国有很多优秀的电影是在小说的基础上改编的,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李樯:剧作家本来就是一个很独立的行当,写剧本是一个单独的手艺,要单独对待。有时候即便你有一个好的小说基础,也不见得改编后的电影剧本是好的,这不是一回事。因为越是优秀的小说,排他性就越强,它就是小说,跟剧本不能画等号。
再者,文学还是相对自由的,作家可以自由去发挥,但一部电影就一个多小时,是很多人协作完成的成果。所以剧本创作者需要经过非常专业的训练,因为剧本本身的饱和度对电影有很大影响,这是必须经过艰苦探索才能做到的。
并不是说原创剧本就一定好,根据小说情节改编的剧本就一定有基础,这之间其实没有必然联系。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登上过“中国编剧作家富豪榜”,这些年国内编剧无论是在稿费还是社会地位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除了导演、明星以外,编剧也渐渐成为了观众选择电影的指标之一,你觉得这对中国电影来说是个好现象么?
李樯:编剧地位提升,电影就能好么?尊重编剧就有好剧本么?其实并不见得,一个编剧创作水准的稳定性就很难说。我不认为编剧地位的提升或者贬低会铸就一个什么样的格局。作为一个编剧,无论你地位的高低,无论是什么时代环境,都要保证剧本质量,这是一个编剧应该做到的,我们应该提高自身水平,然后才有资格去谈与之匹配的回报问题。
电影是个综合艺术,并不是哪个因素特别强大就能造就一个好电影。有可能剧本很好,但是演员不好,那也没有用。
确实,随着各种新媒体的出现,现在很多观众的视野开始变得世界化、多样化了,对电影的选择标准也已经多样性了,会因为演员、导演、编剧甚至摄像等等很多因素去选择电影,这是个好现象,说明我们的观众越来越专业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