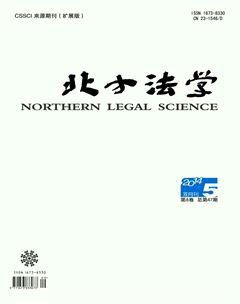结构与功能的背离:宋代州府司法中的长属分职与长官专权
汪庆红
摘要:宋代州级司法职能配置在长官与属官之间存在明确的分工。这种职能分工被赋予了防范长官干预属官司法行为的权力约束功能。但在审判实践中,长官往往借助官制特权或法定特权赋予的优势地位,干预或控制属官的审判行为,操纵州府审判的过程与结果,使州府审判过程呈现出鲜明的长官专权特质。从其司法制度演进的历史考察,两宋时期之所以出现司法体制上的控权倾向与审判过程中的专权特质并存的局面,根源在于其政权建设中难以克服的“祖宗之法”与“汉唐故事”之间的深刻抵牾。
关键词: 州府司法长属分职长官专权祖宗之法汉唐故事
中图分类号:D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4)05-0141-12
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上,宋代司法以其专职官员数量众多、官员法律素质较高、审判过程阶段分明、司法监督体制严密等诸多特点而独树一帜。而两宋时期所建立的司法权由诸多机构分散行使的运行机制,尤为研究者所称道。如宫崎市定认为这种司法体制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尊重人命、重视刑法的事实……可以认为是尊重个人尊严这样一种新理念的高涨”;①徐道邻认为,这种司法体制蕴含着“相制相成”的运行机理;②戴建国认为,这种权力分散而又集体负责的审判制度可以有效限制官府长官的审判权力,防范其“随心所欲违背审判法判决”;③陈景良认为,宋代司法审判蕴含着分权制衡等“现代社会司法理论的历史基因”,是中国古代所独有的“以实现司法公平为其价值的人文主义司法模式”。④
很明显,相对于人们所熟悉的中国古代集权主义司法传统的理论认知⑤和狱政黑暗的负面印象而言,上述研究结论不仅极富新意,甚至是令人振奋的。但从研究思路来看,笔者发现,已有成果对宋代司法审判的权力体制与运行过程的考察,至少就州级官府而言,主要集中在属官的职能定位及其司法活动上,而较少关注长官在司法审判中的权力地位和实际作用。事实上,史籍记载或今人研究都表明,两宋司法审判是一个包括长官、佐贰、幕职和诸曹官共同参与的集体活动。因此,在笔者看来,现有研究对两宋全体司法官员和整个司法过程均未展开全面考察,而将部分司法官员之间和部分审判环节上呈现的所谓“分司覆察”现象,提升为整个官府的全部审判活动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属性,这一研究思路缺乏应有的严谨和审慎,其研究结论也应受到更多的限制与质疑。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宋代州府各类司法官员的职能定位及其主持或参与的审判活动为考察对象,试图以州府⑥长官与其属官之间的职权关系及其参与的审判过程为切入点,探讨宋代州府司法运行过程的内在特质。
一、州府司法体制上的长属分职
根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两宋州级官府拥有司法权的官员人数远较前代后世为多。以其一般性职能定位为标准,宋志将这些官员分别列入长官、佐贰即通判、幕职官和诸曹官四个系统。但为了凸显长官在州府审判中的职权地位,本文将这四个系统的官员划分为长官与属官⑦两个系统。
(一)州府属官的司法权
1.诸曹官的司法权
宋代州府所设曹官主要由录事、司户、司理和司法四类参军组成。按照宋人的观察,相较于其他官员,诸曹官的职能定位有着鲜明的“各有职业”⑧特色。即南宋后期修定的《宝庆四明志》所概括的,“录事掌判院庶务,纠诸曹稽违;司户掌户籍、赋税、仓库受纳;司理掌狱讼鞫勘之事;司法掌议法断刑。”⑨可见,两宋州府曹官中,职掌审判的主要有录事、司理和司法参军。⑩
两宋时期,司理参军号称“专受命鞫狱之官”,B11以“专于推鞫”B12为职能定位。其职权内容主要在于审查证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借以查明案件事实;并以此为事实基础,参照律典对罪状的概括式描述,认定被告罪之有无及其归属。为维护司理参军审判职权的专职化特色,法律明确规定,“郡国不得以司理参军兼莅他职”。B13与司理类似,司法参军的职能定位也有明显的专职化特色,即以检法或曰“议法断刑”、“检法议刑”为主要职掌。按照《宋史·职官志》的记载,检法活动内容,一是审查推鞫官员对被告的罪名认定是否“事理明白,于法平允”,B14二是检索与本案罪名和情节相应的法律条文。由于该项活动对专门法律知识的要求较高,有宋一代,对于司法参军的选任都极为强调其法律素养上的要求。如建隆三年(962)八月,太祖下诏:“注诸道司法参军皆以律疏试判”;B15真宗时,法律规定吏部铨司须谨择明法出身者授职诸州司法参军;B16南宋时,朝廷也下诏“不曾铨试人不许注授司法”。B17这是确保司法参军议狱得平的重要措施。
⑥众所周知,宋代州级官府包括州、府、军、监四个类别,本文以州府统称。同时,由于北宋时期开封府的司法官员设置与一般州府并不完全一致,因而本文并不讨论北宋时期开封府的司法体制与审判过程。关于后者的研究,参见郑寿彭:《宋代开封府研究》,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0年印行,第63—131页。
⑦两宋时期,通判虽然号称“监郡”或“佐贰”之职,但在审判过程中,除在权摄长官职位的特别情形之外,如下文所揭,其职权地位和职能作用与幕职官并无本质差别,因此,本文亦将通判列为“属官”。
⑧《嘉泰会稽志》卷1《签厅》,载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732页。
⑨《宝庆四明志》卷3《诸曹官》,载前引⑧《宋元方志丛刊》,第5026页。
⑩两宋时期,州府司户参军虽然在事实上参与审判活动,但从史籍记载看,这些官员所从事的审判行为主要是以兼职(司理、司法或录事)身份进行的,而其本职则无审判内容。关于司户参军的职能定位,参见(元)脱脱:《宋史》卷167《职官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76页。
B11(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56,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605页。
B12(宋)钱若水:《太宗皇帝实录》卷30,范学辉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1页。
B1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雍熙五年正月庚辰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47页。
B14(宋)张方平:《张方平集》卷25《陈州奏监司官多起刑狱》,郑涵点校,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86页。
B15《宋史》卷1《太祖一》,第12页。
B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8,大中祥符五年七月壬申条,第1774—1775页。
B17《宋史》卷167《职官七》,第3976页。
B18(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41《司理参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81页。
B19(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8《本朝二·法制》,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74页。
与司理参军“专鞫狱”、B18司法参军“专检法”B19的单一性职能定位不同,录事参军在司法审判上的职能安排具有浓厚的兼职化色彩。一方面,作为州府“狱官”之一,录事参军有权以鞫司官员身份审理刑事与民事案件;B20另一方面,根据宋初太祖的诏令,录事参军也可以谳司官员身份参断州狱,B21驳议本府推鞫官员所定罪名是否合法。B22而根据苏轼的记述,至少在宋初,录事参军还可与长官共同参与录问。B23
2.幕职官的司法权
宋代州府内拥有司法职权的幕职官主要包括签判、判官、推官等官员。与诸曹官不同,各类幕职官之间似乎并无明确的职权划分。不仅如此,在司法审判方面,幕职官也没有明确的职能定位。如《宋史·职官志》将幕职官的职掌界定为“裨赞郡政,总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于其长而罢行之”,在这一职权范围中,司法审判并无明显的独立地位。
根据《哲宗正史·职官志》的概括,幕职官的职权行使方式可分为二,一是独员负责“簿书、案牍、文移付受催督之事”,二是“凡郡事与守、倅通签书”。在司法审判事务方面,根据学者的研究,幕职官独员从事的司法事务即为拟判活动,其内容是根据推鞫官员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和检法官员所检定的法律条款,撰写本案的初步处理意见,作为长官定判的参考。B24从《名公书判清明集》所录书判来看,绝大多数州府判决文书均由作为“幕职官联事合治之地”B25的佥厅撰拟,表明拟判应为幕职官的法定职权。至于“与守、倅通签书”之郡事,根据史籍记载,主要是录问与签书。前者包括与长官和通判共同参加对死罪囚犯的录问,或根据长官委派,独员主持对徒罪以上非死罪囚犯的录问;B26后者则集体审判,即与长官、通判共同参与对拟判文件进行的审核。
除此以外,两宋州府幕职官还有权主持当直司的审讯活动。B27按照史籍记载,当直司是负责对“事状章明”的普通民刑事案件按照简易程序开庭审讯的一种审判组织。其审判过程较为简单快捷:诉讼获得受理之后,首先由幕职官对罪人进行审讯,之后再由长官对罪人进行录问,如“对辨无所异”,即可由长吏“遣决之”。B28
3.通判的司法权
两宋时期,通判之职在于“郡政之治,佐而成之;郡政之戾,矫以正之”,B29这意味着,除主职监察州府官员外,通判也拥有一些庶务管理权。按照《哲宗正史·职官志》的概括,通判在政务管理上的职能定位在于“倅贰郡政,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所部”。可见,在州府审判方面,通判并无专任的法定职权,而主要以合议的方式参与司法事务。在审判实践中,除在特定情形下,如受路监司委派审理疑难案件、B30代理行使长官司法权B31以外,通判所从事的审判事务主要是录问和集体签书。与幕职官相同,通判录问囚犯可与长官和幕职官集体参加,亦可独员进行。B32
B20(宋)楼钥:《楼钥集》卷85《先兄严州行状》,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9页。
B21《宋史》卷199《刑法一》,第4967页。
B22(宋)张耒:《张太史明道杂志》,载王云五主编:《过庭录 明道杂志》,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B23(宋)苏轼:《苏轼文集》卷66《书外曾祖程公逸事》,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51页。
B24前引③,第217—218页。
B25《嘉泰会稽志》卷1《佥厅》,载前引⑧《宋元方志丛刊》,第6732页。
B26如姚锡签书光化军判官。有乡人被论为奸细,姚锡奉檄录问,“审得其情,因上谳,卒恕之”。参见陈柏泉编:《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B27《咸淳临安志》卷53《当直司》,载前引⑧《宋元方志丛刊》,第3829页。
B28《宋史》卷305《薛映传》,第10090页。
B29(宋)张咏:《张乖崖集》卷8《麟州通判厅记》,张其凡整理,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5页。
B30黄幹通判安丰军,受淮西帅司委派“鞫和州狱”。参见《宋史》卷430《黄幹传》,第12778页。
B31孙唐卿通判陕州时,曾“权府事”,判决“盗母之丧”一案。参见《宋史》卷443《孙唐卿传》,第13099页。
B32如程戡为虔州通判,“州人有杀母,暮夜置尸仇人之门,以诬仇者。狱已具,戡独辨之,正其罪。”再如仁宗年间,“应天府失入平民死罪,狱成未决,通判孙世宁辨正之。”分别参见《宋史》卷292《程戡传》,第9755页;《宋史》卷315《韩宗彦传》,第10301页。
B33《宋史》卷167《职官七》,第3973页。
(二)州府长官的司法权
关于宋代州府长官的职能定位,《宋史》、《文献通考》等史籍的记载大同小异,即所谓“总理郡政,宣布条教,导民以善而纠其奸慝……其赋役、钱谷、狱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焉”。B33可见,从职能范围看,与前代后世一样,两宋时期的州府长官仍属总揽州政的全权性官员。但从职权内容看,至少在司法审判方面,宋代州府长官并非研究者所称的既“主持庭审和作出判决,还主持勘查和讯问及缉捕罪犯”的集权型长官,B34其与属官存在鲜明的职能分工。
1.司法人事管理权
秦汉以来,作为州郡长官的郡守、刺史均拥有“对于本府官吏之控制权”。B35根据史籍记载,两宋时期,法律至少明确规定了州府长官对其通判之外的属官的举荐、监察、惩戒等项权力,即《哲宗正史·职官志》所记载的,诸州府长官既有权“察郡吏德义才能而保任之”,对属官中“疲软懈怠,或冒法”者亦须“随职事举劾”。B36
为了弥补专司铨选官员重资历、轻才干的缺陷,太宗初年,就曾诏令牧守“阅属部司理参军,廉慎而明于推鞫者,举之”;B37淳化四年(993)七月,又下诏:“诸道转运使、副使,知州、通判、知军监等,各于部内见任幕职、州县官,举通明吏道及精修儒行者各一人”。B38《庆元条法事类》则将这种荐举制度法律化,规定“诸监司、帅守任满赴阙奏事,许举部内廉吏二人”;B39“诸知州,听岁举承直郎以下改官,迪功郎充县令”。B40依此,幕职官、诸曹官均可成为长官荐举的对象。
另一方面,为了强化对州府官员的控制,宋代法律也赋予长官对其属官的监察和惩戒权。雍熙二年(985年)八月,太宗下诏:“近以新及第人为司理参军,恐其初列官常,未通刑法,令州郡长吏,视其不胜任者,于判司簿尉中两易之。”B41咸平三年(1000年),真宗下诏,“幕职州县官到任半年,令长吏、通判具能否以闻。”B42南宋时期,州府长官对属官违法行为的惩戒权得到法律的确认:“诸州县官,在官犯公罪杖以下,本州断罪讫奏”;B43“诸所部官有犯,监司、郡守依法按治,不得倚阁俸给”;B44否则,“诸所部违法,监司及知州、通判失按举,并奏裁”。B45
2.审判过程控制权
从史籍记载看,州府长官除负责本府司法事务的日常性督责管理之外,B46其参与审判活动的主要方式为决定案件受理、指派审判官员、监督推鞫和讼案定判等。
B34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峰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页。
B35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B36《宋会要辑稿》职官47之12,第3424页。
B37《宋史》卷160《选举六》,第3740页。
B38《宋会要辑稿》选举27之5,第4664页。
B39《庆元条法事类》卷14《选举门·荐举总法》,载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一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页。
B40前引B39,第295页。
B41《太宗皇帝实录》卷33,第360页。
B42《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6,第3458页。
B43《庆元条法事类》卷9《职制门·去官解役》,第158页。
B44《庆元条法事类》卷7《职制门·监司巡历》,第129页。
B45《庆元条法事类》卷7《职制门·监司知通按举》,第128页。
B46如督掌狱掾检视监狱、刊榜现行鞫狱条法等。分别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开宝二年五月癸卯条,第223页;(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丙戍,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832页。
B47(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17《慎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51页。
B48(宋)蔡襄:《蔡襄全集》卷26《送张总之温州司理序》,陈庆元等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7页。
B49《宋会要辑稿》刑法6之54,第6720页。
B50《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84,第6619页。
首先是决定收受案件的处理方式。依宋制,州府专司机构所收受诉状,须先经长官审阅并决定是否予以受理,即所谓“治狱之官,若某当追,若某当讯,……率具检以禀郡守,曰可则行”。B47决定受理之后,长官还需要根据案情,决定案件的处理方式:如为轻微刑事和民事案件,长官可自主处理;如为死刑案件,长官需在预先审查之后,交付专司官员依法处理,即所谓“守视其事之小者立决之,其大者下于理官”。B48天圣八年(1030年),朝廷下诏:“大辟公事,自今令长吏躬亲问逐,然后押下所司点检勘鞫”;B49乾道元年(1165年)也规定,“自今诸县结解大辟,仰本州长吏先审情实,如无冤抑,方付狱”。B50是为长官对死刑案件行使预审权的法律依据。
其次是选派审判官员。如前所述,在司法审判事务方面,宋代州府各类属官存在着较为普遍的职权交叉情形,负有推鞫、录问、检法、拟判等权责的司法官员人数众多,如狱案推鞫是司理参军、录事参军和幕职官分别主持的司理院、州院和当直司等司法机构的基本职责;录问、拟判则为各类幕职官的主职与主责。由此,具体某一案件的审讯、录问、拟判官员,需由长官选派和决定。宋代法律规定,“府有狱,司录参军必白知府,乃敢鞫治”;B51录问之时或行刑之前,人犯“有翻异或其家诉冤者,听本处移司”,B52“白长吏移司推鞫”。B53此为长官指派推鞫、录问官员的法定依据。不仅如此,按照韩元吉的理解,甚至于原本分掌推鞫与检法的“司理司法,则郡守得专对换”。B54
再次是对推鞫活动的监督。为了强化其对审判过程的控制,两宋法律赋予州府长官对本府推鞫活动的事中与事后监督权。雍熙三年(986年),朝廷要求“诸州讯囚不须众官共视,申长吏得判乃讯囚”。B55嗣后,这一要求成为定制:“治狱之官,……若某当被五木,率具检以禀郡守,曰可则行”。B56推鞫结束后,对于勘结的大辟案件,长官还须以录问形式对鞫司官员的事实认定进行监督。宋初,朝廷就要求断徒以上罪,案牍圆备后,须差官录问;B57咸平五年(1002年)下诏,长吏、通判、幕职官共同参与录问本州大辟狱案。B58嗣后,这一规定成为定制,并沿用至南宋时期。B59如果考虑到州府的诉讼管辖权限即为徒以上罪案B60的法律规定,就不难发现,州府初审的几乎所有案件均须经过录问——死罪案件,由长官率领佐贰、属官共同参与,其他案件则由长官委派属官主持录问。
最后,按照州府审判流程,在推鞫、检法结束之后,须由拟笔官员撰写本案的判决意见,交由长官、通判与幕职官共同审核,“众皆可焉,班而布之,然后乃得已矣”。B61对此,两宋法律有明确规定,如皇祐五年(1053年),仁宗下诏:“诸路知州军武臣并须与僚属参议公事,毋得专决。”B62南宋时期,法律也规定,“诸州公事,当职官公共平议,不得委官及所司定夺”。B63审核完成后,参与官员还需在拟判文书上签字画押,以负其责任。拟判获得签书之后,再由长官书写判语。这一审判过程,在史籍中被概括为“审狱具文,咨于从事,谋于监郡,上于太守”。B64可见,州府司法审判的最终决定掌握在长官之手,即所谓“州郡刑狱、词讼……专决于郡守”。B65
(三)州府司法体制的长属分职倾向
B5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5,嘉祐六年十一月庚申条,第4730页。
B5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景祐四年正月丙戍条,第2819页。
B5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66《刑考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45页。
B54(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10《看祥文武格法札子》,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7页。
B55《宋史》卷199《刑法一》,第4971页。
B56前引B47,第2851页。
B57《咸平集》卷1《上真宗论轻于用兵》,第22页。
B5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咸平五年十月戊寅条,第1156页。
B59《宋会要辑稿》刑法6之69,第6728页。
B60《庆元条法事类》卷73《刑狱门三·决遣》,第744页。
B61前引B48。
B62《宋会要辑稿》职官47之10,第3423页。
B63《庆元条法事类》卷8《职制门·评议公事》,第140页。
B64前引B48。
B65《宋会要辑稿》职官47之72,第3454页。
B66前引B48。
宋初以来,为了使法官尽心,狱讼得平,朝廷将以情察狱、检法议刑等司法权责专门授予司理、司法参军等州府属官,并通过制度化的法律措施,将这些官员的基本职权限定于司法审判。但根据时人的观察,狱官尽责,法司尽职,“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须以长官不夺其权为前提条件,即所谓“不夺则责之”。否则,理官“不得其专”,为长官“日召而前,颐指教敕,迎合其意则喜,违之则怒;至有锻炼迁就而为之,使寃者不得吐其臆,鞠者不得毕其虑”。B66南宋时期,也有臣僚认为,宋代司法职官设置上专司专职的目的正在于防范狱官对长官“有所迎合,且将锻炼之,致轻重其手而高下其心”,并鼓励其“与上官争是非曲直”。B67可见,在两宋时期的有识之士看来,确保狱讼公平的关键虽系于司法官员的“公勤尽心”,但又以长官不“以喜怒出入情罪”B68为首要前提。而防止长官干预属官的司法审判行为,有效方式就是实行长属分职,明确长官与属官的职能界限,防范一方对另一方法定职权的侵越,确保各自在法定职权范围内独立行使司法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臣僚认为,长官“小大之狱,必躬必亲”并不符合“国家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之意”。B69
从制度设置上,两宋法律似乎也坚持了这一分职倾向:一方面,宋代法律并不鼓励长官越俎代庖,参与属官所负责的推鞫、检法与拟判等审判活动。如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有臣僚建议,对于属县上报至州“情节不圆”的案件,由“长官审实推鞫,依限结断”,但朝廷采纳的处理建议是由长官“取会事件,仰行下所属取会,断结施行”。B70再者,按照宋人“监司、太守断事不检法,但决脊杖若干、刺配某州军”,B71“省曹之勘当,掾属之书拟,有司之按事,长吏之举贤”的说法,B72可知两宋州府长官也不负责检法与拟判等具体性审判事务。另一方面,两宋朝廷对属官侵越长官独享权力的违制行为设定了明确的禁令与严厉的惩罚。元符年间,开封府尹盛章以狱空觊赏而不受刑案,权知咸平县向子諲“直以闻,诏许自论决;章大怒,劾公以修学市木,不如其直,请御宝特勒停”;B73天圣年间,感德军司理杨若愚不申长吏,考决无罪人骆宪等,被“特追一官”;B74庆元四年(1198年),温州通判林叔秀因“凌蔑郡守,兜揽民词,擅自判押”而被罢官。B75
总之,州府长官与属官之间在司法审判事务上的分职,是两宋时期诸司分职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与前述录参、幕职官之间在推鞫、录问、拟判等私法活动上的职权交叉局面相对照,不难发现,是长属分职而非鞫谳分司,更能体现宋代州府司法体制上的职能分工特质。
B67前引B47,第2854—2855页。
B68《宋会要辑稿》职官72之23,第3999页。
B69前引B47,第2854—2855页。
B70《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82,第6618页。
B71(宋)魏了翁、(元)方回:《续古今考》卷25《附论弃市》,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55页。
B72(宋)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6《论士大夫风俗札子》,载《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737页。
B73(宋)汪应辰:《文定集》卷21《徽猷阁直学士、右大中大夫向公墓志铭》,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B74前引B49。
B75《宋会要辑稿》职官74之3,第4052页。
B76前引B36。
B77《咸淳临安志》卷53《当直司》,第3829页。
B78(宋)宋庠:《元宪集》卷23《十二考人前权保康军节度推官田颖可著作佐郎奏举人前陈州司理参军孙淮可大理寺丞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6页。
B79(宋)刘宰:《漫塘文集》卷22《真州司法厅壁记》,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B80(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公移·州县官牒》,载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14页。
B81(宋)穆修:《河南集》卷2《送鲁推官赴南海序》,载《宋集珍本丛刊》(第2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414页。
二、州府审判过程中的长官专权
如上所述,在立法建制的层面,宋代试图通过在州府长官与属官之间明确职能界限的方式,防范长官干预属官的审判行为;但从州府审判过程的角度分析,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这种分职体制并不能有效防范州府审判过程中的长官专权。
从立法思路看,两宋州府长属之间的职能分工并不具有现代宪政体制下多种权力之间的对抗意义。基于宋人的观察,州府长属之间权力关系的基调在于协作,而非对抗。如宋人多将幕职、诸曹官的职能定位为“以职事从其长而后行”:B76幕职官为“赞画之任”、B77司理参军“询狱辅州”、B78司法参军“奉三尺律令以与太守从事”B79等等。可见,在司法实践中,两宋时期长属之间“等级分明,大小相维,各有承属”B80的职能分工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令而行之者,其长之所专;从而辅之者,其佐之所守”B81的合作关系。
从二者司法权的性质与作用看,长官所掌握的主要是州府审判过程中具有宏观性、全局性和控制性的组织权、指挥权与监控权;属官所从事的则是事实查明、法律适用和判决建议等具体的和技术性的审判事务。就其对审判结果的影响而言,长官通过决定是否受理案件、指派审判官员、监督审讯过程、确认判案结果、监控司法官员等方式,对州府审判施加直接与间接的实质性影响,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属官所主持的推鞫、检法和拟判等审判行为,只有经由长官的监督与确认之后,才能对判决结果产生实际影响。
因此,从司法审判的过程机理分析,在两宋州府司法审判过程中,“佐理刑狱”B82的属官施展对“总理郡政”B83的长官“行使专断权力的制约功能”,B84并不具备有效的制度平台。由此,尽管在司法实践中不乏“凡断大辟狱,虽罪状明白,仍遍询僚寀,佥同而后决”B85的贤明官长,但法定依据层面,两宋时期并没有确认和维护州府长属之间审判权力相互制约的制度设置。相反,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长官与属官在职能定位和官品等级上的“分位阔绝”、B86官僚制下唯官长是从的为官理念B87的不当影响,尤其是借助法律赋予的对属官的人事控制权和审判过程监控权所形成的权威和权势,州府长官对属官审判行为的影响和控制更为常见,长官对本府司法审判的过程与结果拥有实质意义上的决定权,属官所主持或参与的审判行为并不具有制度化的自主性。
(一)长官滥用独任审判权,操纵属官的审判行为
如前所述,根据法律规定,州府长官对案件受理、官员选派、狱案定判等审判事务和自主处理的案件有单方作出有效决定的权力。在长属分职的司法体制下,这不仅意味着属官侵越这些独任审判权的行为即为非法,也意味着他们无法获得对抗或抵制长官独任审判行为的正当性依据。如李承之调明州司法参军,“郡守任情执法,人莫敢忤,承之独毅然力争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始至公,自为之则已;既下有司,则当循三尺之法矣。”B88
按照李承之的理解,专司官员法定权限范围内的司法行为,固然应免受长官的非法干预,但这也意味着,对于其法定权限内的独任审判行为,长官亦有完全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处置权,属官的对抗或抵制亦为不法。
B82《咸平集》卷28《陈州参军刘泽可光州司理判官》,第335页。
B83《文献通考》卷63《职官十七》,第569页。
B84[英]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页。
B85《宋史》卷274《翟守素传》,第9363页。
B86(宋)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46《成都府录事厅题名壁记》,载《宋集珍本丛刊》(第77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190页。
B87如司马朴调晋宁军士曹参军。“通判不法,转运使王似讽朴伺其过。朴不可,曰,‘下吏而?长官,不唯乱常,人且不食吾余矣,死不敢奉教。似贤而荐之。”参见《宋史》卷298《司马朴传》,第9907页。
B88《宋史》卷310《李承之传》,第10177—10178页。
B89《宋史》卷317《冯京传》,第10340页。
B90《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85,第6620页。
B91《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咨目呈两通判及职曹官》,第3页。
B92《宋史》卷310《李孝寿传》,第10180页。
B93(宋)《公是集》卷53《朝散大夫殿中丞知汝州叶县骑都尉陈君墓志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5页。
从权力运行的逻辑考察,这种长官专断的运行机制固然有助于充分发挥贤明官长在州府审判中的主观能动性,便于其力排众议,查明实情或审慎用法,维护狱讼公平和效率。如冯京为郡守,对于属县审结上报至州的案件,“即历究之,苟与县牍合而处断丽于法者,呼法吏决罪,不以付狱。报下捷疾,一无塞滞,人服其敏云”。B89但另一方面,在这种“州县狱多取决于太守”的审判机制中,B90“长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于下;僚属退然自默,不以情达于上”,以至于“上下痞塞,是非莫闻”的现象,B91亦难以禁绝。如吕嘉问知开封府事,受章淳、蔡卞指使,锻炼上书人,命李孝寿摄司录事,成其狱;B92陈耿为永定军司理参军,人有杀死于路者,其子疑怨家所为,囚无以自明,陈某审讯时察其不直,并向长官提出异议,但守丞却“遣他掾与司理杂治囚,笞掠数百千,囚不胜痛,诬服”。B93
从以上二例我们看到,州府长官都是通过滥用法定的委派审判官员的权力,控制推鞫与别推等审判活动,达到操纵州府审判的非正当目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两宋州府审判实践中,狱案得平,“州郡因事
推赏,必以守臣为先,倅贰次之,其他幕职曹掾官宣劳虽多,例弗及赏”;而一时公过,既付所司,“守倅常得佚罚,僚吏常被禁锢”,此“何轻重厚薄之不侔也”。B94如李夔任池州军事推官,民人乙因争塘水而殴甲至死,刑官欲定死罪。李夔拟判时,建议减等处刑,太守不予理会,“于是命他官书断。其后,大理详谳,以甲准盗论,乙乃止当杖。审刑、书断官以失入抵罪……公犹坐尝签书。”B95再如嘉定三年(1210年)十一月间,临安府有民行贿,事关武学生卢某等人,府尹赵某命将卢某等人付理院械系,检法官议刑为赎铜七斤,而府尹书判各决竹篦二十,押出府城。嗣后,诸生就府尹之判逐级申诉,乃至尚书省及御史台、谏院。“府尹伺知之,乃委罪于司理参军赵师。”嗣后,朝廷对府尹与司理的处断是并行放罢。B96
(二)长官滥用集体审判权,控制属官的审判行为
在州府审判过程中,除单独行使某些独任审判权之外,长官还要与其属官共同参与录问和签书等集体审判活动。但与现代合议制下注重维护审判人员权力地位平等的格局不同,两宋时期的集体审判行为并不强调长官与属官之间地位上的平等与协商中的民主,相反,长官借助司法制度所赋予的特权地位,肆意压制属官在集体审判中的异议权,控制录问和签书的过程与结果。
按照史籍记载,录问是推鞫结束之后,由应差官员审读案款、提审案犯,审查推鞫官员所认定案情是否属实的审判行为。录问过程中,如人犯或其亲属翻变,即可由长官“别差官推勘”;B97如未翻变,则进行下一环节的审判活动,即检法断刑。因此,从其内容看,录问既是一项防范狱案冤滥的慎刑措施,也是录问官员针对推鞫行为是否合情合法的监督手段,对审判过程及判案结果均有重要影响。
B94《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40《论州县官有公罪乞随事赏罚》,载《宋集珍本丛刊》(第51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428页。
B95《杨龟山先生集》卷32《李修撰墓志铭》,载《宋集珍本丛刊》(第29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529—530页。
B96(宋)佚名编:《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2,汝企和点校,嘉定三年十二月丙寅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22—224页。
B97《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51,第6603页。
B98《宋史》卷319《刘敞传》,第10385页。
B99《宋史》卷430《张洽传》,第12787页。
B100《宋史》卷343《陆佃传》,第10919页。
B101《长编》卷459,元祐六年六月壬辰条,第10979页。
B102前引B80。
如前所述,两宋法律虽然明确要求大辟案件须由长官、通判和幕职官聚厅录问,但并未对三者的职能分工作明确规定。从史籍记载看,在审判实践中,州府长官在录问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对录问结论的作出具有决定性作用;而通判和幕职官等属官所发挥的只是协赞作用,居于服从地位。如刘敞知扬州府:“天长县鞫王甲杀人,既具狱。敞见而察其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户曹杜诱,诱不能有所平反,而傅致益牢。将论囚,敞曰:‘冤也。亲按问之。甲知能为己直,乃敢告。盖杀人者,富人陈氏也。相传以为神明。”B98
在本案中,知州刘敞在预审中察觉冤情,在受委推鞫官员平冤未果之后,进而在录问时人犯未曾翻变的情形下,主动驳正原审认定事实,并亲行推问,最终查明案情。尽管最终有效防范了冤案发生,但在其间,发挥主导作用的仍为长官,而不容属官置喙。同样,在录问过程中,如与长官就原审认定案情是否属实的问题出现意见分歧时,属官并无强制性对抗手段。如张洽通判池州,有张德修者,误蹴人而死,狱官以故杀定罪。“洽讯而疑之,请再鞫,守不听。”最后,张洽是在说服监司官员“阅款状于狱”的情况下,才最终使“德修遂从徒罪”。B99陆佃知江宁府,句容人盗嫂害其兄,并诬三人同谋。众囚既讯皆服,其中一囚之父以冤诉,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狱已成,不可变。”而陆佃不为所动,“阅实,三人皆得生。”B100可见,在州府审判过程中,录问要能发现“推勘官出没其情”之弊,发挥“疏驳其失”的功效,B101主要依靠仍在于长官的态度与认知,而非通判与幕职官等属官的驳议或谏劝。
再就签书而言,按照朱熹的理解,两宋时期之所以实行集体审核签书的审判制度,是出于长官“一人之智,不能遍周众事”的考虑,试图“建立司存,使相总摄”,通过众官“商量详审,与决公事”的方式,以使审判“上合法意,下慰民情”。B102或者说,这种集体审判制度的基本目的与积极效能主要在于通过属官的参与,提高司法审判的效率和效益。这意味着,州府审判中的审核签书,实质上仍为属官对长官的协赞性制度,是避免长官决策疏漏的拾遗补缺机制,即如臣僚所坦陈的,“所谓幕职官,不过随例签书,岂能一一争执?”B103“凡政有害于公,有悖于理,知而必言,此己所可为尔。言而必从,岂己之所能哉?”B104对拟判的审核签书,决定权仍掌握在长官手中。
既然审核拟判只是一种兼听基础上的独断决策机制,那么,长官在签书过程中是否接受属官的意见与建议,就完全取决于长官的品行或属官的态度。如钱若水为同州观察推官,“知州性褊急,数以胸臆决事不当。若水固争不能得,辄曰:‘当赔俸赎铜耳。已而奏案果为朝廷及上司所驳,州官皆以赎论。知州愧谢,己而复然,前后如此,数矣。”B105王田领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乡民有得遗财于道,且遇卒拒捕者。府尹周式欲以“盗而后强”定罪,王公以无可据之法而“执不敢断”。周式曰:“尔有异识,何不以状来使吾按治耶?”王公果上议状,周式“意为解,止决杖而释之”。B106两起案件,长官与属官在签书中的两种态度,导致州府审判的两种结果。可见,真正对长官审判行为产生约束力的并非属官的签书权力,而是长官的为官风格与法律意识。
(三)长官滥用官制特权,干预属官的独任审判行为
宋代延续唐代各级官府实行的同职连署制度,B107要求在官府政务处理过程中,长官必须与佐贰、职事官共同处理文案,并在相关案牍上共同签押,以确保集体负责。因此,除录问官与签书官之外,州府幕职、诸曹官也须在其主持的推鞫、检法、拟判活动中形成的相关案牍上签名画押,作为其负责的文字依据。
《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公事应连书,若执见不同者,听各具事状申所属。”B108这意味着,在州府审判过程中,参与官员有权以拒绝签押的方式,抵制其他官员的不法或专断行为,并通过向上级官府甚至朝廷申诉的方式,纠正本府的枉法或不当裁断。如胡向为袁州司理参军,“有人窃食,而主者击杀之。郡论以死。向争之曰:‘法当杖。郡将不听。至请于朝,乃如向议。”B109
但从权力运行机理看,这种属官不署牍并向上级官府求援的制度设置所依靠的并非属官对长官的权力约束作用,而是上级对州级官府的司法监督权威。这不仅意味着司法效率的降低,更使长官任情执法的约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因为在审判实践中,州府长官往往依靠法律赋予的荐举、监察、惩治等项权力予以威逼或诱惑,试图迫使不署牍的属官就范。如郭永为丹州司法参军,太守“为奸利无所忌,永数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临永,永不为动;则缪为好言荐之朝。永因尽忠以报。后守欲变具狱。永力争不能得,袖举牒还之,拂衣去。”B110再如宋泌任吉州录事参军:“郡守治狱任情。君日抱案牍辨,数被摧辱,不惧不悔。有断兄足而取其财,狱成。守导囚声冤,劾君失入。刑部直君。守滋怒,穷治过失无所得。”B111
B103前引B94。
B104前引B81。
B10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淳化元年十月乙巳条,第705页。
B106(宋)《苏魏公文集》卷56《太常少卿致仕王公墓志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57页。
B107童光政:《唐宋“四等官”审判制度初探》,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B108《庆元条法事类》卷8《职制门·评议公事》,第141页。
B109(宋)郑克:《折狱龟鉴》卷4《议罪》,载杨奉琨校释:《疑狱集·折狱龟鉴校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7页。
B110(宋)汪藻:《浮溪集》卷20《郭永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27页。
B111《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75《从政郎宋佖君墓志铭》,第707页。
B112《宋史》卷381《吴表臣传》,第11731页。
B113(宋)洪迈:《夷坚支甲》卷5《游节妇》,何卓点校:《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7页。
更有甚者,长官利用官制上的优势地位,直接向属官施压,迫使其顺从己意。如吴表臣任通州司理,有武臣为盛章“诬以罪,系狱。表臣方鞫之。郡将曰:‘知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B112淳熙四年(1177年),建昌军南城近郭南原村宁六为其弟妇游氏所诬,赴县狱,并傅会成案,上于军。“军守戴顗不能察,且闾阎匹妇而能守义,保身不受凌偪。录事参军赵师景又迎合顗意,锻炼成狱”。B113
在以上诸例中,面对长官的软硬兼施,州府属官既有持法力争者(如宋泌),有装聋作哑的(如吴表臣),有阿附随顺者(如赵师景),有以去官相胁者(如郭永)。除此以外,还有委曲求全者,如叶文炳调筠州录参,“前后两太守宽严不同,文炳视其所偏资助之。……狱有巨援,文炳争守入之;守有所欲入,文炳故缓其事,待其自觉露既前”。B114而绍圣年间袁州司理黄令的经历,则向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州府属官是如何在知州合法与非法的威逼与压制下,在屡屡抗争无果的形势下,最终屈从长官,导致狱案冤滥的全过程。
(宜春尉遣弓手三人,买鸡豚于村墅,阅四十日不归,三人之妻诉于郡。郡守与尉有旧好,令尉自为计。尉谎称部内有盗,遣三人者往侦,久而不还,是殆毙于贼手。愿合诸邑求盗,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将以往,留山间两月,无以复命。使从吏持钱二万,倩村民四人诈为盗以应命。四人许之。遂执缚诣县,囚服实如尉言。送府,黄司理主治之,无异词。乃具狱上宪台,得报皆斩,既择日赴市矣。四人始具言其故。)吾大惊,悉挺其缚。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狱掾受囚赂,导之上变。”明日吾入府白事。守盛怒,叱使下,曰:“君治狱已竟,上诸外台阅实矣。乃受贿赂,妄欲改变邪?”吾曰:“既得其冤,安敢不为辨?”守无可柰何,移狱于录曹,又移于县,不能决。法当复申宪台,则置狱。守曰:“如是则一郡失入之罪众矣。安有已论决而复变者?”悉取移狱辞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款。吾引义固争,累十数日不得直。遂谒告。郡守令司户尝摄邑者代吾事。临欲杀囚,守复悔曰:“若黄司理不书狱,异时必讼我于朝矣。”令同官相镌谕曰:“囚必死,君虽固执亦无益。今强为书名于牍尾,人人知事出郡将,君何罪焉?”吾黾俯书押。四人遂死。B115
由上可见,无论是在长官单独负责的独任审判活动,还是长官与属官共同参与的集体审判活动,甚至是长官无权涉足的属官独任审判活动中,两宋时期的州府属官都很难找到抵抗长官恣意任性的合法性制度依据或正当性权力资源。在这些审判环节中,州府长官的擅权弄法之所以得到有效遏制,或者依靠属官的勇气与智慧,或者依靠长官的谦抑或忌讳,或者依靠上级官府乃至朝廷的纠察,而并非源于法律制度所赋予属官的强制性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刘宰所揭露“上官多以意用之,意所欲重,吏不敢丽之轻;意所欲轻,吏不敢丽之重”的长官滥权,B116恐怕并非两宋州府司法审判的个别现象。
B114(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6《通判和州叶氏墓志铭》,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37页。
B115《夷坚乙志》卷6《袁州狱》,第229—230页。
B116《漫塘文集》卷23《平江司法厅修造记》,第7页。
B117(元)王结:《文忠集》卷4《上中书宰相八事书》,第9页,载《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B118《朱子语类》卷128《本朝二·法制》,第3070页。
B119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页。
B120《历代名臣奏议》卷168《选举》,第2208页。
B121前引B47,第2852页。
三、州府长属分职与专权并存的形成原因
对于宋代州府长属之间“幕僚分掌事务,商确可否;长官提其纲而处决之”的分职体制,元人王结总结的优点在于其有助于“政出于一,有统纪伦序;事可集,而民可安”。B117可见,在后人看来,两宋时期州级官府内长属分职的司法体制,所发挥的实际效能在于维护审判过程中的长官专权。很明显,这与宋初“尽夺藩镇之权”B118的分职体制设置初衷大相径庭。推究这种制度变异的原因,笔者认为,宋代政权建设中“祖宗之法”与“汉唐故事”之间的冲突是最值得关注的因素。
众所周知,宋朝是一个极为重视“祖宗之法”的朝代。尽管如研究者所发现的,宋代的“祖宗之法”并非某种可以具象指称的实体,B119但将设官分职上“上下相维,内外相制”视为太祖、太宗二帝所创制的“祖宗法度纪纲”则是仁宗以后诸朝臣僚的基本认同。按照哲宗朝侍御史陈次升的理解,这一“祖宗之法”的核心精神在于分割事权,将政府运行中各类事务或各个环节上的主导权力赋予不同的政府机构,在各个机构“各有分守”的权力结构和政府管理“事有统制”的运行过程中实现不同机构之间的权力约束,进而“以防私徇,以杜奸惑”。B120由此看来,宋代州府审判中长属分职、鞫谳分司、翻异別勘等理念和原则正是这一“祖宗之法”的应有之义。如高宗朝汪应辰就将两宋时期中央到地方官府内“鞫之与谳者,各司其局”的分职体制和运行机制看作是“累圣相授”的国家经久之制,其基本理念正在于“并建官师,上下相维,内外相制,所以防闲考覆者,纤悉委曲,无所不至也”。B121而从其制度演变的历史进程看,这种“各有司存,所以防奸”的州府审判体制和机制,也正是宋初二帝创法立制的成果。摘其要者,如太祖“惩藩镇弊,置通判以分州权”,B122“建隆四年,诏知府公事并须长吏、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B123“建隆三年,令……凡诸州狱,则录事参军与司法掾参断之,自是内外折狱蔽罪,皆有官以相覆察”;B124“开宝六年始置诸州司寇参军,以新进士及选人为之,后改为司理,掌狱讼勘鞫之事,不兼他职”,B125等等。此后,这些制度设置及其防奸理念逐渐演变成为司法审判上的“万世不易之法”,并因此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至少在官方表达层面维持着不容质疑、不容违反的合法性权威。
但另一方面,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州级官府就是一个长官“主一郡之事”B126的集权政府。其中刺史、州牧或郡守等州府长官在地方政府中据有“六部之事系于一人”的主导地位。汉唐时期,作为治民之官的刺史或州牧就有“掌治其郡”、“秉一州之统”的职能定位,其“任重职大”,一州之内“信理庶绩,劝农赈贫,决讼断辟,兴利除害,检察郡奸,升善黜陟,诛杀残暴”,B127无所不包,因而历代均有为求“政平讼理”,皇帝“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B128或“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B129的观念或说法。及至宋代,前代的牧守之官“总理郡政……狱讼钱谷之事皆总”的职能定位及其与君主“共理”B130民政或“长吏者,民之性命”B131的政治地位,至少在官方是得到公开承认的。因此,既然州府长官对一州内诸如狱讼钱谷等事务均有“总而治之”的权力和地位,具体在司法事务上,州府审判过程中诸如讼案受理、委员审判、监督审讯乃至罪案定判等各项权力集中于长官,就并不违反,反而是符合包括宋代在内中国古代司法逻辑的正常现象。再者,汉唐以来,州级官府中,郡守、刺史、知州等长官无论是在职官品秩、政治地位还是司法过程上都享有优越于属官的特权地位,并可借助考绩、监察、举荐等合法渠道实现对属官的控制,在司法审判中影响州府其他官员的司法行为,进而操纵审判的过程与结果,这也构成了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实务上的一个传统。由此,我们才能理解,薛映知杭州时,“临决锋锐,州无留事”,得到朝廷肯定;B132范纯仁知齐州时,将司理院系囚未经审理,“尽呼至庭下,训使自新,即释去”的行为,亦被视为宽猛相济的仁政之举。B133
B122《景定建康志》卷24《通判厅》,载前引⑧《宋元方志丛刊》,第1712页。
B123前引B17,第3974页。
B124前引B21。
B125《文献通考》卷63《职官十七》,第572页。
B126(清)顾炎武:《日知录》卷9《守令》,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6页。
B127《职官分纪》卷40《总州牧》,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29页。
B128(汉)班固:《汉书》卷89《循吏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4页。
B129(唐)吴兢:《贞观政要》卷3《择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0—91页。
B130《宋会要辑稿》职官47之34,第3435页。
B131《宋会要辑稿》职官47之9,第3422页。
B13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4,景德三年十月癸巳条,第1431页。
B133《宋史》卷314《范纯仁传》,第10285—10286页。
B134(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00《绍述》,李之亮点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B135前引B65。
可见,宋代州府司法制度建设和审判运行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祖宗之法”与“汉唐故事”之间的紧张甚至抵牾关系:一方面,借助“祖宗之法”所承载的政治合法性,长属分职、鞫谳分司等分职体制与覆察机制维持着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由于宋初二帝并未否认汉唐以来州府长官集权的传统,进而使司法实践中长官借助司法制度内外的优势权位控制州府审判的过程与结果成为可能。尤其是北宋中期以后,人们对“祖宗之法”转为“归于治耳,不在于法令因革之间”B134的虚应故事态度,宋初二帝所确立的诸司分职等创新制度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形同虚设。即如嘉定十四年(1221年),权兵部侍郎陈广寿所言:“国初惩五代藩镇之弊,始置诸州通判,诏公事并须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今边方郡守往往欲事权出于一己,虑其相侵,率不谋于同列,自为剖判,曲直失当,不合事情。而郡佐复多远嫌疑,柔怯巽避,知享平分之乐而不能为□[关]决之助。”B135
四、结语
宋初二帝为了追求狱讼公平、国祚延绵,殚精竭虑,在二三十年间,建立起了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上独具特色的司法制度,尤其是其注重司法机构之间的职权分工,关注司法官员的法律素养,倡导司法官员之间的权力约束,强化司法审判中的程序约束功能,实为传统中国历代法制所罕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审判实践中,这套强调“诸司分职”的制度设置并未发挥“防闲考覆”的权力约束功能。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宋代州府审判制度建设“播种龙种,收获跳蚤”的根源实在于其零敲碎打式的制度建设路径。宋初统治者将防范州府长官专权的重心放在体制建构上,却忽视了司法运行过程上的制度改革和建设。这不仅不符合司法权力运行的应有逻辑,更使统治者所确立的“藩镇无擅权之势,郡县无专杀之威”B136的治世理想无从实现。因此,尽管在宋初,依靠二帝的励精图治和政治权威,创新制度在运行中尚能抵消长官专权司法传统的侵蚀,但二帝之后,随着“祖宗之法”权威的弱化,分司覆察逐渐沦为朝臣口中的“说法”B137而已。南宋中后期,州府司法便重蹈汉唐以来的覆辙,“狱官不循三尺,专以上官私喜怒为轻重。求民无冤,不可得矣”。B138
B136《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02《问汉唐官官外戚藩镇夷狄》,第657页。
B137前引B119,第13页。
B138前引B90。
因此,司法制度改革建设应当有整体设计,是宋代司法制度建设给我们的教训。
Separation of Judicial Function and Commissioners Judicial Autocracy in
Prefectures of the Song Dynasty
WANG Qing-hong
Abstract:The separation of judicial functions is clarified between the commissioner and his subordinate officials at prefecture level in the Song Dynasty, with the purpose of preventing the commissioner from intervening in his subordinate officials judicial behavior. While in judicial practice, by taking advantage of bureaucracy and statutory prerogative, the commissioner has often been meddling with his subordinate officials in their trials and manipulating both trial procedures and outcome. Thus, the judicial process at prefecture level bears the feature of the commissioners judicial autocracy.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judicial system evolvement in Song Dynasties, the inclination to power constraint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feature of the commissioners autocracy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coexisted, which rooted in the profou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surmountable “ancestors doctrines” and the “traditional practices followed sinc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Key words:judicial activ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separation of powers between the commissioner and his subordinate officialscommissioners autocracyancestors doctrinestraditional practices followed since Han and Tang Dynas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