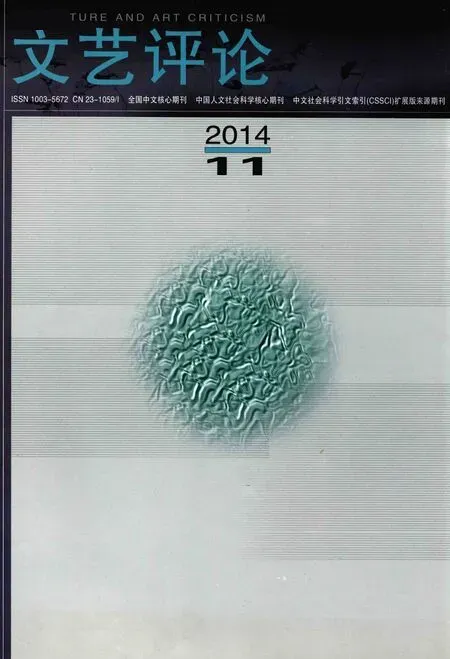文化形态上的认同与借鉴——纳博科夫文学观与我国后现代小说的精神缠绕
○唐 希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个前提是,研究中国当代的后现代小说,需要对后现代这样一个最含糊最不确定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进行大致范围上的界定。这里,我们特指中国当代文坛上曾经出现或在当下的文学文本中所反映出来的具有反叛传统叙事,强调和突出革新精神与前卫意识的小说创作。它可以是指在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先锋小说,也可以包括后来的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以及就作者本人而言算不上什么小说派别的代表性人物,及某一作家或他的某一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具有后现代倾向和风格的创作手法。
然而,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在讨论中国的后现代小说的时候便有了稍微明确的针对性。谈到我们讨论的正题,作为引领美国后现代小说滥觞的后现代大师纳博科夫对我国后现代小说有何影响。关于这样的问题,比较通常的看法是,于1984年被译成中文并引入到中国的法国先锋派剧作家欧仁·尤纳斯库的论文《论先锋派》,这篇对中国的文学家来说耳目一新的创作理论,使人们久被禁锢的大脑豁然开朗,中国的先锋小说家在把其中的理论视为经典的同时,开始将目光转向西方后现代的作家作品。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看法是,卡夫卡、博尔赫斯、罗伯-格里耶是我国先锋小说的实验宗师,对风靡于当时中国文坛的新锐小说家们发生着楷模般的影响力。纳博科夫,似乎是一个被遗忘的名字。像这样一个被称作20世纪以来美国文学继福克纳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作家,英语文学中继乔伊斯之后最有风格和最具有独创性的人物,事实上他在形象、语言、技巧、主题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被视为美国后现代小说的发端,而且推出了堪称楷模的后现代范式,他用他开创的后现代文化形态上难以企及的高度,影响和启发了美国众多的后现代小说家的创作灵感。本文拟就我国后现代小说在“怎么写”、“生存现状”和“超验现实”三个方面与纳博科夫创作上的相似性问题上进行探讨。
一、关于“怎么写”
“怎么写”的问题历来是传统文学与后现代小说在文学观上的重大分野。传统文学在固定的文学范式下,将写作的重心放在内容上。按照纳博科夫的话说,就是编故事。但纳博科夫认为这样的作家只能是末流的作家。中间层次是教育家,最好的作家是魔术师。他认为这样的作家能够突破现实的束缚,对文化、艺术和思想进行虚构,从而走向精神的真实。在纳博科夫看来,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他在代表作《洛丽塔》中,写一个37岁的成年男人亨伯特与12岁的少女洛丽塔热恋与性爱,后来又安排亨伯特当上少女的继父。老少恋本来就不合常理,再加上“乱伦”,更加为人所不齿。但纳博科夫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重要的是作者如何去写。在纳博科夫看来,亨伯特恋童癖的内容远没有小说的写法重要。同样的题材内容,但描写的手法可以多种多样。你可以用一种写法来赞赏亨伯特,也可以用另一种写法来批驳亨伯特的性变态。事实上,纳博科夫希望把亨伯特描述成一个恶棍。在表达这一愿望的前提下,去追求小说形式上的审美极乐和艺术美。因此,作者认为,“小说作品的存在价值,就是能够向我提供我所简单地称作审美极乐的那种东西,那是一种以某种方式、在某一场合与另类的生存境界发生联系的感觉。在那里,艺术(好奇、温情、仁慈、狂喜)就是标准”。①作者用重视题材处理手法而不是题材内容的做法,来表明作者对于色情的反对态度,认为形式对于作家才是更重要的。
基于这样的观点,纳博科夫在创作中将互文性结构,戏仿和语言游戏的技法发挥到了极致。在《微暗的火》中,作者将教科书似的前言、注释和索引作为小说中的一部分引入文本,将截然不同的文体并陈混杂。加之小说中散乱而漂浮的故事,如诗人谢德的爱情婚姻、谢德的写作活动与死亡、刺客格拉杜斯对逃亡国王的追杀、查理国王的流亡生活、金保特的学院生活与编辑工作、谢德之女的自杀等,使叙事成为小说重要的审美对象。作者将戏仿视为文学上的创造。他在小说《微暗的火》中借主人公金保特之口,建议读者不按文本顺序进行阅读,表现出作家对充满酸腐学究气的编辑的辛辣讽刺。作者用游戏的手法表现诗人女儿海泽尔的投湖自尽,并由注释者金保特探讨自杀的各种方式:
理想的掉下是从飞机上,你的肌肉松弛,你的飞行员迷惑不解,你打包的降落伞被甩掉,被丢弃,被不屑一顾——再见了,shootka(小降落伞)!
这种近似玩笑的写作态度,集中反映出纳博科夫写作上的重要观点,即“为了快乐”。作家邀请读者参与他的游戏,并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感到快乐,作者认为这才是作家所要追求的终极意义。再是“为了争论”,读者理解小说复杂的叙事结构,使游戏服从于读者的“智力组合转变”,将小说中不能确证的人物关系,由读者自主做出不同的解释和猜测。
我国的后现代小说家显然承袭了“怎么写”问题上的艺术探索。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先锋小说作家,如马原、洪峰、残雪、孙甘露、余华、苏童、格非、北村、叶兆言和吕新等人,在自己的作品中突破传统的叙事藩篱,他们或不惜把故事的因果关系分拆得四分五裂,将互不相关的故事淹没在拼凑起来的片段当中,使传统小说同一的思想意义转变为散乱的相对意义;或将叙述向语言展开而不是向故事情节上的叙事展开,用双重文本的互文性,将文体上的“仿寓言体”和叙事上的“仿梦结构”紧紧交织在一起;或直接走进小说而成为被叙事者,公开声明小说故事情节的虚构性,以强化和凸显小说叙事上的意义,指出唯有叙事才是小说真正的意义。马原是这条探索之路上的路标。他在小说《冈底斯的诱惑》中探讨西藏的神话传说与原始生存状态对现代文明的“诱惑”,作者采用后现代的“元小说”手法,在作品中探讨小说故事的“线索”、“结构”和“遗留问题”,质疑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标榜叙事本身的审美意义。作者在小说中安排穷布、陆高和姚亮观看天葬、顿珠兄弟俩的故事,但故事的情节发展却支离破碎。作者在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神秘未知的东西,仅仅是为了激发读者对叙事本身产生出更高的热情。他将现实主义文本中的“真实幻觉”转换成后现代的“似真似幻”,在小说的叙事中不时提醒读者,不要为虚构的故事所欺骗。在《虚构》中,作者更是直接闯入小说,将作者、叙述者、人物三者合而为一,使叙事的角色更加错综复杂,真假难辨。如他在讲述麻风病村的故事时告诫读者:
读者朋友,在讲完这个悲惨故事之前,我得说下面的结尾是杜撰的。我像许多讲故事的人一样,生怕你们中间一些人认起真……
这无疑是叙事上的冒险,但它客观上也在语言学和符号学意义上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的形式美学空间,使得这种典型的个人化的写作态度,成为我国后现代小说创作的重要艺术经验。
消解意义,同样被我国后现代小说家奉为法宝。他们认为,作家不需要对意义担负任何承诺,小说创作“只是一次写作过程,一大串语词的游戏,一大堆生活碎片的拼凑娱乐”。②基于这样的观点,我国的后现代小说家或是单纯强调语言的能指功能,如格非在《褐色鸟群》中使用的句式:
浅黄色的凹陷和胯部成锐角背部石榴红色的墙成板块状向左向右微斜身体处于舞蹈和僵直之间笨拙而又有弹性地起伏颠簸。
在这里,“所指”的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词语的“能指”功能,它们在不同语境条件下自由组合所产生出来的审美效果。
或是消解词语的明晰性,孙甘露的《来劲》亦能说明这一问题:
三天之后,也就是五天以前一年以前两个月以后……
词语所指上的不确定性,语义表现中的模糊性,仿佛“是”与“不是”的前后矛盾,正是后现代小说家通过似是而非的话语游戏所要最追求的文学意义。
“性”是王小波创作的重要话题。然而,他所描写的性主题,亦类似于纳博科夫的文艺观,即作者性描写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依然是写作的态度,看重的是对“性题材”如何表现的问题。如《似水流年》中的描写:
我现在明白了我爸我妈为什么对我的性生活这么操心。当时我是二十三岁,小转玲还未成年。万一走了火,她怀了孕要做人流,还得开介绍信。别的地方开不出来,只有我们公社能开。你替我想想,假如发生这样的事,我会怎么样。
在那样的环境下,开介绍信等于公开他们的私情。发生这样的事,意味着知青王二将丧失招工、参军或读大学的机会,他个人的前途将会彻底被毁掉。这里,人们看到的是作家对荒谬残酷的生存环境的悲情控诉。这正如纳博科夫所说:“并非艺术癖性是第二性征,像那些骗子和巫师说的,恰恰相反,性不过是艺术的附属物”。③
二、关于“生存现状”
后现代将目光聚焦到“怎么写”的问题上,它“不再是对生活的阐释,不再是超越生活的审美空间,因而也无需要像现实主义艺术家那样在本文里压缩进人类的集体精神,探视人的灵魂颤抖的频率”,④不再对意义担负任何承诺。然而,情况并非那样简单。撇开纳博科夫的前期创作,单就他二次大战后的后现代写作而言,作者在进行形而上探索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在文本中探讨一些永恒的话题,即普遍意义上“人”的生存现状。只是这种生存状态的表现形式,作者往往采用时间的方式表现出来。《洛丽塔》典型地反映出这种时间链条上的主题:主人公亨伯特为“过去”所压迫,于是期望谋杀“现在”并以此占据“未来”。表现在故事情节中,亨伯特早年的女友阿娜贝尔代表过去,洛丽塔的母亲夏洛特代表现在,洛丽塔代表未来。在夏洛特车祸死亡后,“现在”消失,代表美好“未来”的洛丽塔才能够相拥入怀。在《微暗的火》中,作者表达自己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生存状况的思考。小说中希德用诗歌的形式反映自己与死亡“不能允许存在的丑恶深渊”斗争的一生,金保特用注释的方式回顾自己从一国之君到流亡教授的过程。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即使最注重形式探索的后现代大师,他在将全部的精力放在“怎么写”的问题上时,依然要考虑写什么的问题,必然会在文本中显露出关于主题或思想倾向的蛛丝马迹。
我国的后现代小说创作,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当那些先锋小说家高喊着文学的语言不再象征或隐喻语言之外的任何具体意义,作家应集体转向去专注“怎么写”的时候,他们依然没有忘记用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来传递社会文化心理,或者纯粹个人化的理性思考。人们或者不重视作品要传递的终极意义,但不能不考虑作家本人对这个意义的理解与思考;就算经过作家后现代技法处理之后的故事片段,读者在阅读它们所表现出来的相对性意义的时候,依然能够整合出自己的审美判断。纵观我国的后现代创作,“生存现状”依然是后现代作家表现的题中之义。以马原为例,他在小说《冈底斯的诱惑》中描写散乱并行的三个故事及西藏的图腾崇拜、远古神话、天葬传统、寺庙文化、古王朝遗址、乱伦行为和狩猎行动,必然会传递出西藏这一特定地域人们生存现状的相关信息。即使作者不希望表达出统一的思想意义,仍然不妨碍人们对于意义理解的多样化可能。事实上,作家在小说中表现出西藏的迤逦风景与奇异习俗,展现了西藏高原充满传奇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氛围。苏童在《1934年的逃亡》中描写家族的陈年往事,并未因着力于形式上的探索而忽略对家族命运的叙述。祖母的五个子女相继死去,祖父逃离到城市所给家谱上写下动人的篇章,反映出作家家族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生存情形。余华在《世事如烟》中执著于表达人类命运的复杂性、怪异性和宿命性,在现实与幻觉相互重叠的时空中不断地逼近人类学本质。澳大利亚詹姆斯·乔伊斯基金会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
体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并把这种有关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回归到最基本最朴实的自然界……
作者的另一部小说《一九八六年》涉及文革背景,小说讲述一个在文革中被逼疯的人,在文革后继续着他的悲惨命运的故事。整篇小说与其说反映了文革时期底层人们痛苦的生存现状,还不如说它是对这种丑恶的现状的愤怒揭示。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文革结束十年后陷入了疯狂,小说的叙述者,在对疯狂过程的描写中同样显示出近似癫狂的非理性状态。作者用戏仿的手法,在对主人公自戕的描述中揭示出当时人们生存状况的恐怖与荒诞。在小说《活着》中,作者用书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与乐观态度的对比手法,张扬一种“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人生处世哲学。徐晓鹤在《疯子和他们的院长》、《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标本》等小说里,将卑琐的疯子的错乱行为以戏仿的方式加以表现,体现出对荒谬时代人们生存现状在后现代话语状态下的重现。格非在小说《大年》中,讲述村民豹子带着村民抄地主丁伯高家的故事。表面上看是写村民暴动,深层则暗示了另外一个神秘的原因,那就是唐济尧对玫的情谊,同样是我国农村生活的现实写照。王小波的写作呈现出不遗余力地批评专制和愚昧现状的理性特色,在思辨性思考的背后,隐藏着对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现状的担忧:
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
沉默,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现状。基于这样的理性认识,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于不动声色之处对极权主义的清醒认识和决不妥协的批判态度。在《时代三部曲》中,作家以饱满的生存感受,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种时间维度中反思知识分子“可以拥有什么样的生活”。他批评中国人长期以来在权势面前卑躬屈膝的丑陋行为,使自己丧失尊严的同时,也毁掉了聪明才智。作者借《时代三部曲》描写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难史,反映出纳博科夫式的时间链条上的主题:《青铜时代》描写“古代中国”极权专制对智慧的阉割,《黄金时代》描写“文化大革命”极权专制对智慧的阉割,《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描写“未来中国”技术专制对智慧的阉割,表达出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中,作者展现被丑恶现实扭曲了的人性,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不幸的生活本质。小说《万寿寺》展示人类精神家园,《红拂夜奔》展示人类生存境遇,《寻找无双》展示智慧遭遇等等,无不反映出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
三、关于“超验现实”
就对现实的反映来说,后现代借助康德的哲学术语,用“超验”现实来替代一切可能的经验现实或日常现实。在纳博科夫看来,现实带有主观性,它是一种信息逐渐积累和专门化的过程。在小说的注释部分,主人公金保特用想象虚构了赞布拉的故事来与诗人希德诗中的故事相抗衡,强行将读者引向金保特的想象世界。并认为,这种想象的超验现实才是小说要表现的真正内容,小说越是突破现实原则的束缚,走向想象中的虚构,就越接近精神的真实。此外,作者还刻意表现了孤独性、异化现象和死亡意识等超验现实。就孤独而言,作家强调,它是人生的基本状况,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就异化而言,作者将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美国后现代创作中的概念,用来表现被扭曲了的人物个性。如诗人希德在小说中被描写成异化了的艺术家。作者认为,艺术家在他本人与创作之间所造成的距离越大越好,作者就会愈加满意。将金保特处理为性别异化和身份异化的人。当他还是王子的时候,他沉湎于同性恋,以致他不能拥有圆满的爱情和履行繁育后代的责任。革命爆发后,他由国王异化为大学教师。就死亡的表现而言,作者将之贯穿在创作的始终。如描写诗人希德的女儿因为肥胖丑陋而受到男友怠慢去投湖自尽,但女儿认为面对丑陋的现实生活,死亡反而更加壮美。金保特则对死亡充满了恐惧。他闯入希德的诗中,让诗人去充当他的替罪羊。
我国的后现代小说家不赞同后现代的虚无主义,认为直面生活,关注现实生存,特别是用艺术的虚构来表现生活,乃是后现代的应有之义。他们赞同纳博科夫小说创作的本质是虚构的理论主张。王小波曾说,作家可以在文学的事业中投入彭拜的想象力。他同时认为,小说创作并非超离了一切,是小说家随心所欲、漫无边际的天方夜谭。它要坚守它的内在精神,成为对生命真实的一种探索。因而他的创作被人视为是“通过解除遮蔽而照亮存在”。然而,在我国,更多的后现代小说家借助虚构来表现自己对丑恶现状的反讽和对未来道路的思考。他们突破现实原则的束缚,奋不顾身地祭起虚构的大旗,追逐和探寻着精神上的真实。在这种虚构的精神领域中,同样蕴涵了想象当中的神奇现实,自我意识中的孤独现象、处在扭曲环境或苦难状态中人们精神上的异化,以及面对死亡时的复杂感受。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作者采用纸牌的方式,每天想起一点写一点儿,没主题也不联贯,等到写的纸头多了,把它们串起就成了一部小说。作者用这样的叙事方式对传统创作进行挑战,使整篇小说充斥着想象虚构的色彩。马原在小说《冈底斯的诱惑》中描写穷布追踪熊,陆高和姚亮观看天葬、顿珠顿月兄弟俩的故事亦颇具传奇的想象色彩。穷布发现自己穷追不舍的熊,原来是传说中的喜马拉雅山雪人的时候,似乎把读者引入想象中的生活幻象当中去了。而这种民俗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空白,远远超越了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初始意义,超越了大多数从未踏上这块神秘土地的读者的经验联想。余华的小说《四月三日事件》从一把钥匙入手,借助主人公“他”对小说情节展开假设的想象,使一些虚构出来的事情始终没有答案,一个个的悬疑,超越了读者对现实的想象空间,以致形成一个个虚幻的现实。作者在小说中借助虚构和想象表现了自己关于社会主流价值对人类生命摧残的理性思考。
想象之外,异化亦是超验现实的另一重要领域。王小波在创作中曾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的描写对象。他在《时代三部曲》中探讨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表现出他们在专制主义束缚下心灵被规训被异化的状态,没有尊严,没有平等,也没有自由,面对这样的痛苦现实,有人却说“这很幸福”。这里,作家把某类人被扭曲了的变态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红拂夜奔》中写李卫公证明毕达哥拉斯定理,在被拉去衙门打了一顿板子,落了一个“妖言惑众”的罪名后,不得不煞费苦心地把费尔马定理的证明写成谁也无法破译的春宫解说词,表现出智慧被暴力异化的万般无奈。而对于知识分子智慧的成果,小说直接把它们异化为屠杀生命的各类机器,使智慧的成果变得不伦不类。
再是对死亡的描写和对死亡意识的表达。苏童在《1934年的逃亡》中,用虚构的笔法描述家族中那段过往的历史往事,刻意表现了锈迹斑斑的家族画面中的死亡话语,乡村中五个孩子难以逃离的死亡,祖母一人用坚强的意志承担着巨大的痛苦,祖父逃离祖母的同时也逃离了死亡,表现出人们在死亡面前的不同命运。王小波在小说《万寿寺》中对刺死女刺客的描写,在《红拂夜奔》中描述卫公夫人殉节的过程,在《寻找无双》中表现鱼玄机被执行绞刑的画面,透射出人们在死亡面前所持有的不同的心理状态,极具虚构夸张的成分。
当中国的后现代写作面对强势卷入的世界性话语的时候,作家们不可能独善其身,继续抱着传统与现代的精神品质。他们无论是对外来文化的“舶来”,还是对本土社会文化境遇的改造,紧跟世界文化发展脉搏似乎是后现代小说家的必然之举。我国的先锋作家在这样的文化潮流面前不甘落伍,尝试着将中国的本土文化历史与模仿得来的外来文学形式进行艺术嫁接,用后现代性的文化形态来表现现代性话语,我们从中似乎能够感受到纳博科夫的创作身影。
①刘建华《危机与探索——后现代美国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31页。
②④陈晓明《冒险的迁徙》,沈阳《艺术广角》[J],1990年第3期。
③廿一行《王小波十论》[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3年版,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