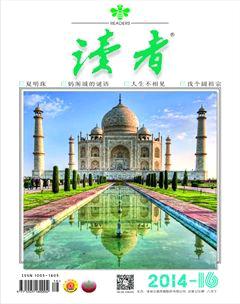妈阁城的谜语
严歌苓

第一次踏进拉斯韦加斯的赌场是1988年,亲戚们是把赌城一游作为一道美国文化盛餐来款待我的。我们乘坐的大巴上赫然印着“发财团”的大字,车上座无虚席,大部分赌客是来自台湾又在美国定居的中国人,一小部分是到美国走亲戚的大陆同胞。大巴的行李箱爆满,因为不少旅客带了成打的软饮料,可乐、雪碧之类。赌城的饮料比其他城市要贵,因此他们宁可劳其筋骨随身携带,能节省一听是一听,八分、一毛的财富也是财富。即便赌博,他们照样勤劳谨慎,一看就是中国人中的规矩人,中华民族的美德差不多就写在他们的气质和容貌上。入住的米高梅大酒店,目光穷尽处,望不断的赌台、赌局,眼睛和耳朵根本盛不下那么多声和光。女招待的着装比当地法律还开明,让人看到赢钱的下一步可以通向哪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堂而皇之的赌窟。回程的车上,绝大多数人比原先穷了几百或几千,3天前的陌生旅伴因为共同吃了赌场的亏而亲密起来。相互热议的都是如何与赢局擦了个边,似乎每个人都得到过财神爷刹那的眷顾,但由于种种的小意外又与财富失之交臂。几乎没人怪罪赌场不公正的设置,在输的定局里看到赢的幻影就够了。
在赌场里逛了3天,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赌场里的中国人从比例上要比美国人多,社会层次要比美国人高。美国赌客中很大一部分从气质上看都是离犯罪不太远的人,明显地带有一种自我憎恶但更憎恶社会的眼神,而中国赌客基本上个个是良民。
几年后,我结交了一个朋友,她向我诉苦说,一个从北京来的老教授跟她借了不小的一笔钱,理由是国内老家发洪灾,急需修房子和治病的钱。他还要我的朋友保密,绝不告诉他的女儿,因为女儿刚毕业,工作婚姻都还没着落,做父亲的不忍给女儿增加压力。钱借出了,就此一去不回。我的朋友唯一可宽心的是,这位老先生是北京名校的教授,知书达理,从哪方面看都是正人君子,迟早会还钱。两三年后,老先生的女儿告诫她,假如自己的父亲背地向她借钱,千万借不得,因为老教授染上了赌瘾,背着她向她周围的人都借过钱。一旦钱到他手里,他就乘上华人“发财团”的大巴跑去拉斯韦加斯,带上预先做好的9份三明治——够3天的伙食,至于睡眠,干脆就戒了,连轴转地坐在老虎机前,跟机器熬,直到输光最后一个角子。在一次聚会上,我也见到了这位老教授,典型的白面书生,想到他仔仔细细做出9份三明治,克己自律地奔向赌场,输掉几万美元,实在难以置信。赌场和他,谁是更大的谜?
于是我写了第一部有关赌徒的故事——《拉斯韦加斯的谜语》。那是十几年前,我初次对人性中的赌性产生感触,开始探索。
后来,我无意中接触到北美华人的移民史,其中写到早期的美国华工赌博的故事。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沿海地带的华人远渡重洋,参加美国西部开发,淘金、修筑大铁路、填沼泽造田,初衷是要用这些工程的所获给家族脱贫,为父母盖上一座房,为自己娶上一房媳妇,再生一群儿女,却在回乡的轮船底舱赌场里输得一无所有,到达家乡码头的时候,甚至比离开时还穷。很多人因为没钱娶许定的媳妇,没脸见乡里父老,便直接乘船原路返回彼岸,再签一单5年或10年的苦役契约,忍受种族迫害和歧视,为别人的家国富强继续出生入死。其中有些人,居然又在回乡的船上屈服于赌瘾,又一次沦落得不名一文……
读到这些段落,我想,这些悲剧都惨得引人发笑了,这些人是怎么了?
前年,我偶然又听到了另外几个赌徒的故事,相较于老教授和华工的故事,它显得更加壮烈、血腥,甚至魔幻。故事中的赌徒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历经艰辛并靠自己的智慧获得财富的人。他们来到一海之隔的澳门(妈阁),一夜输赢往往几百万、上千万,有的人进赌场时是亿万富翁,出赌场时却欠了一屁股债,被黑白两道的追债人全世界索命。也有决心改过自新的,甚至还有断指起誓的——你不能怀疑他们的沉痛和真诚了吧?但最终还是输给了赌场,也可以说他们是输给了让赌场夺走魂魄的自己。
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更好的关于赌博的故事。接下来的两年,我一有时间就去澳门赌场,学赌博,体验赌博心理,采访赌客和赌场经纪人,终于得到足够的细节来丰满故事和人物。
我原先以为,人之所以成为赌徒是因为穷,穷红了眼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赌,因为没什么可输的。但我最近听到的故事中的人都是阔人,都是掌握了致富规律,具有一定致富经验的人。这样的人竟会舍弃必然,随偶然去摆布,放弃规律和科学的可重复性,听信无序和所谓的天命,实在是令人失望。这些故事再一次引起我的怀疑:赌性是不是我们的先天弱点?我们是不是被动惯了,被世世代代的统治者摆弄惯了,不做主惯了,理性和规律总是让王者权贵颠覆,那就不如把自己交给未知和侥幸,以被动制被动,反而有了点主动——这种宿命观是不是积淀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里?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对财富的渴望是那么热切、危急、致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连年战乱饥荒,天灾人祸。不说远的,就说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战争、灾荒、政治动乱留给中国人多少的空暇来创造和积累财富?基本上是刚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净自己的血迹,就要迎接下一场灾难了。因为我们最缺致富的机会和时间,所以在致富时就难免带有紧迫感、危机感,也难免短视,急功近利。似乎我们冥冥中感到限期要到了,政策要改了,不抓紧时机,时机就过去了。因而,富要暴富,财要横财,在一切没来得及改变之前,捞一把是一把,捞了还来得及跑,来得及躲。而一切财富得来之快,快不过赌台,尽管那些大款阔佬已经有了生财之道,已经致富成功,但他们战胜不了几千年的遗传密码,那就是灾民意识,是贫穷给我们留下的心灵耻辱和创伤。中国人摆脱内忧外患才多久?不到一个世纪。我们占据足够的居住面积、吃饱穿暖才多久?还有多少中国人仍然缺乏吃、穿、住的体面和尊严?这些都继续作用于我们的集体潜意识,继续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对于贫穷、饥荒的忧患和恐惧。这种与生俱来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恐惧和忧患意识使我们的狩猎者和当家人——中国男人,永远暗怀一个梦想,就是闪电般地获得巨大财富。赌台似乎成全了他们的梦想,提供了“三更穷五更富”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缩写。一头是赢,一头是输,与其把命运交给一个个陌生的主宰,不如把它交给未知的老天,老天暗中给你洗的牌未必更不公平。赢是生,输是死,求生不得求死总可以,但凡是求,总有点抗争的意味,好歹纸牌筹码自己还过了一下手,往哪里下注,下多少注,还是归你选择,总比一觉醒来的未知要让人甘心一些。
(李中一摘自《文艺报》2014年5月9日,勾 犇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