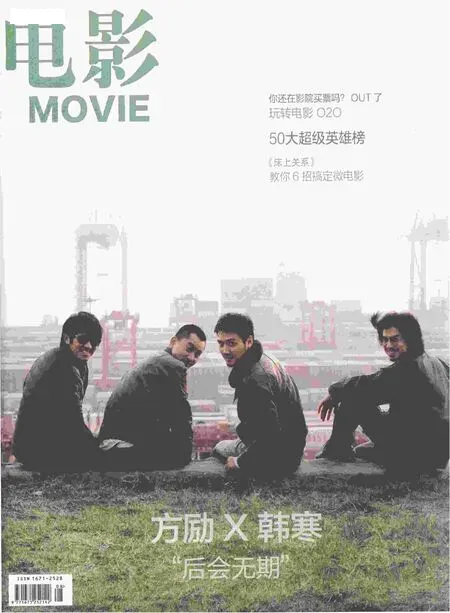阳光灿烂的日子
按照王小波的说法,“生活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这样看来我们年少时干的那些蠢事儿也许是为了对抗庸俗的世界和庸常的自己,比方说我,少年最爱干的事儿是跑步、打架和四处游荡,这大概跟我那时候最喜欢的三部影片有关,它们是《猜火车》、《香港制造》、和《坏孩子的天空》。三部片子不由分说地给我的少年时代贴上了这样的标签:脏、乱、差。脏得像马克·瑞登潜入的那个全英国最腌臜的厕所,乱得像中秋生活的那个动荡的社区,差得像小马和新志的操行成绩。
《猜火车》教会我跑步,高中时阅览室的杂志五花八门,让我有机会在一堆电影杂志过刊里看到《猜火车》的海报。那是一张大幅海报,主人公横卧在铁轨上,双手被反绑在身后,愤怒、嘲弄、反叛都凝聚在一个坏笑里,那个姿势和表情像一道异色的强烈阳光照进我的大脑。当天下午,我从窗户翻进阶梯教室,在巨大的投影上观摩了马克·瑞登们疯狂奔跑的动人姿态,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人可以那样跑,像是把自己抛出去,像一颗子弹穿透这个世界的身体,就和《百年孤独》里的奥雷里亚诺上校第一次看到冰块那样,我感到不可思议,当想到自己的年轻身体也可以这样跑的时候,我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满意和惊喜。
没有台湾电影和日本电影里那些干净清新的阳光绿树、课桌校服,《猜火车》里只有泥泞的英国街道和主人公们抹布一样的旧T恤,但它们更蓬勃,更不可抑制,散发着生命力的清香,一个毛头小子迅速被这群疯子一样的年轻人征服了,看着他们的生活我开始明白脏和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衣衫褴褛但是有一块拒绝所有杂质的透明心灵,有的人西装革履下面藏着一个不可见光的卑鄙灵魂。看到肮脏马桶下面那片澄澈清蓝的海水时我暗下决心,想要任性活着,我开始听朋克音乐,尽可能地为所欲为,觉得奔跑的姿势属于青春期,并在每一次跑步的时候像一颗子弹一样射进这个世界体内,这之中的某些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比如奔跑,每当鞋子和橡胶跑道摩擦的刹那,好像能打开一扇门,穿过它就能回到那个充满力量的过去。
我忘了自己年少时是怎么理解萨特的那句“他人即是地狱”的,只记得那时候没少和他人打架,我成年后才看《古惑仔》,所以,这事儿和刘伟强没关系,倒是陈果的那部《香港制造》让我看了几遍,主人公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个人遭遇都跟我挨不上边,我身边没有黑帮也没有自戕的女同学,但每次看这部电影都会有一种共鸣,那个好勇斗狠的中秋好像我身上某个部分。后来渐渐明白,打架,不只是因为年轻人血是热的,而是因为每个少年身上都有种孤独,我们急于和这个世界沟通却无人理睬,我们急于认识自己却无处入手,打架是种笨拙又极度有效的方式,你可以通过施予或感受疼痛来体会世界的温度,可以通过极端的情绪确认自己的存在。明白这些的时候我已经很久没有打过架了,但我再看《香港制造》里中秋与别人拳脚相加依然觉得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姿态,年轻人之间打架和成人世界的暴力有本质上的区别,少年心中的英雄情结让他们不会为了私利或剥夺动手,更鲜有以众欺寡或以强凌弱的情况。除了一些号称军事化管理的监狱式学校,每个高中都有打群架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刻,但是别担心,马小军已经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为我们讲解过了,人多的群架往往打不起来。
彼时我在遵规守纪方面绝对是个差生,仗着“无因的反叛”把“操行零分”当骄傲。大正是我升入高中的第一个死党,也是最铁的一个,在老师觉得这两个人无可救药的时候,我们自我感觉极其良好,坐在秋天的操场上喝啤酒的时候大正跟我说,我们完了。我说放屁,我们还没开始呢。那时候,我还没看过《坏孩子的天空》,后来才知道小马对新志说了同样的话。其时,我们正因为多次逃课和夜不归宿被强制停课,每天在办公室罚站等待“调查结果”——这个结果通常是开除。我们索性更加放浪形骸,老师们去上课的时候,我们溜出办公室到操场上打球,喝从校外顺进来的啤酒,去食堂找大厨聊天蹭饭,停课持续了三天,我们把那座不算小的高中每个角落都晃了个遍,那可能是高中里最快乐而漫长的三天,因为无所事事,也因为有朋友,坏孩子那片跟他人不太一样的天空,就是靠朋友撑起来的。当然,和所有快乐的故事一样,我们后来也没有被开除。
青春期那阵刺鼻的清香在生命中轻轻一掠便随风而逝,从回忆中脱身而出的一瞬间就像浮出海面,所谓脏乱差的少年成长史也许只是海水中飘忽的幻像,年少不是永恒的,但你知道有些东西是永恒的。

《猜火车》剧照

《坏孩子的天空》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