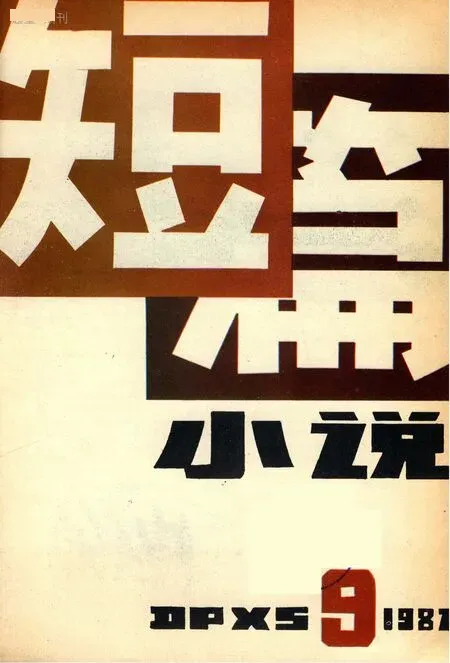安眠药
◎杨智俊
安眠药
◎杨智俊

(一)失眠症患者自述
患者姓名:姚小山
年龄:31周岁
职业:出租车司机
医生,我老婆和女儿都说我应该来看看心理医生,其实,我也不知道这管不管用——哦,医生,我没有贬低你的意思,听说在国外你这一行很吃香——我是说我失眠很严重,这个病折磨了我差不多快二十年,吃了好多的药,也试了很多偏方,统统不管用。有一回,一个工友说生吃东风螺可以治失眠,我信了他,生吃了两只,结果我被送进了医院。医生说我感染了啥管圆线虫病。类似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 (冷笑一声)结果呢,啥偏方也不管用!你看我的眼泡、眼睛,是不是红肿得厉害?我很多年都没有痛痛快快地睡上一觉了!每天晚上老婆睡着了,我却一点也睡不着,睁着两只眼,头疼得要裂开一样。那种痛苦没有失过眠的人根本不能体会……有几次,我都想从楼上跳下去死了算了,可是,一想到女儿还这么小——她还没上初中呢——我的心就又软了。
医生,你问我是从啥时候开始失眠的?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从十一岁起就开始失眠了。那时我才上小学五年级。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坎儿……(说着眼眶有些湿润,嗓子变得沙哑,揉了揉鼻子)医生,我能抽支烟不?一回想起这些事情,我就受不了!……(摸出一支烟来,自己点燃后猛地吸了一口,缓缓地吐出)
(神情逐渐恢复镇定)我小时候本来挺幸福的。父亲从部队复员后买了辆解放大拖挂,自己跑货运,那时跑运输的少,挺赚钱的。我们家在村子里算是比较富裕的。母亲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没啥文化,能写自己的名字,会简单的加减乘除。不过她很能干,父亲不在家时——父亲经常出车,一走就是十天半月的——家里地里的活儿全是她干,完全能顶一个壮劳力。她还要照顾得了绝症的爷爷——爷爷得了食道癌,晚期,多亏了母亲的精心照顾,他才能又活了那么长时间。爷爷逢人就夸,几辈子修来这么好个儿媳,比亲闺女还要亲。我还有一个妹妹,叫姚小莉,长得很可爱……如果她还在世的话,今年也该有二十八岁了……(闭着眼睛,用手抹了抹眼眶和鼻子的交界处)
那件事情到底是咋发生的?到现在仍然说不清。在那之前,父亲与母亲的关系已经不太好了。他们常常争吵,要不就是冷战。为啥不好呢?有一个传言这么说,说母亲在父亲不在家的那些日子,难耐寂寞,跟在砖厂干活的一个叫根生的河南人好上了。更难听的说法是,妹妹小莉其实就是母亲跟那个河南人生的!当然这些话都是胡说八道。
其实母亲就是太善良了。记得有逃荒的人到村里挨门讨饭,别的人家塞给他们一个硬馍馍,或是一碗稀粥就打发了。可到我家,母亲会把那些浑身脏兮兮的人请进家来,当客人一样待。她请那些人吃手擀面,卤子不是炒鸡蛋就是猪肉,临走还要往他们布兜里塞满干粮。母亲就是这么一个好心肠的人。所以,当母亲看到根生一个人住在野外的庵棚里,生活艰难,就动了善心,常常周济些米面瓜菜给他。根生知恩图报,常帮我家浇个地,喷个农药什么的。事情就是这样。
可是,有人却编排出那些难听的话。父亲相不相信呢?我想起初也是不信的,可是他经不住那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耳边嘀咕——人都有这个缺点,是吧?也许后来,父亲就有些相信了。
十一岁那年春天,父亲像往常一样往山东蓬莱跑了一趟长途,托人捎信回来说,他想好好歇一歇,这次回来就在家住一段时间。几天后父亲回来了。但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还带着一个年轻女人。
女人约莫二十岁年纪,比父亲小差不多一轮。长得结实矮胖,大圆脸,肤色有些黑,外地口音,说话快,有点像唱歌,得仔细听才能听懂。她在我家里住了多半个月,就住在搁粮食和杂物的南屋,单独支了一铺床。父亲说,那女人是他的徒弟,跟他学习开车,因为和家里闹了些矛盾,所以跑了出来。
父亲让我和妹妹喊她“红姨”。我曾奇怪哪里蹦出这么个红姨,对她有那么一点抵触情绪——说到底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嘛。但是这个红姨对我太好了,糖果饼干地哄着我,还又教我唱,又教我跳,很快就俘虏了我的心。她似乎还有些文化,甚至有传言说村里的小学校长预备请她做代课老师,当然后来证实这只是个谣传。
红姨管我母亲叫 “大姐”,喊我父亲为 “师傅”。在我的印象中,开解放大挂车都是像父亲那样的彪形大汉,像红姨这样学开大挂车的年轻女子绝无仅有。不过,红姨似乎并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和看法,她活得很坦然,很自在,手脚也不懒,会帮着母亲干些家务活,有时也下地干活。不过,母亲不会勉强她,毕竟红姨是个客呢。
但是爷爷不喜欢她,看红姨的眼神总是冷冷的。有几回爷爷还和父亲争吵了几句,声音压得很低,我听得不是很清,但我感觉他们争吵的原因和红姨有关。他们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就那么僵持着。不一会儿,父亲从爷爷屋出来,脸色铁青,看到我就朝我挥挥拳头。
不过,红姨对我好,我也就很喜欢她。这是很自然的。除了上学,我几乎整天黏着她。当我黏得太紧的时候,父亲就有些不高兴,喝令我干这干那,还骂我不用心学习之类。我一噘嘴,刚要生气,红姨就摸出一块水果糖塞进我嘴里,真是让人气也气不得,恼也恼不成。后来,母亲偷偷警告我:不许天天黏乎着红姨。我问为啥。母亲突然生了气,说,还为啥?不许就是不许!
母亲对红姨客客气气的,两人经常在一起聊天,天气好的时候,还一起步行到四里地外的小镇上,挑挑布料买买东西什么的。甚至母亲还准备为红姨张罗谈对象的事。当母亲把那些小伙子的情况说给红姨听时,红姨就用手掩了嘴,只是笑个不停。
不过很快,不知道为啥,母亲和红姨闹翻了脸。那天,母亲像平时一样出了门,说是要回娘家一趟,傍晚前回来,要我和妹妹在家听话。午饭是红姨做的。吃过饭后,父亲递给我一只水桶,让我和妹妹到村外的小河沟摸鱼。他催促我们快去。他这种举动让我感到奇怪——平时他总是责怪我玩心太大,学习不用功——可是小孩子能去外面玩玩总是开心的。我们就高兴地去了。多半个钟头后,我和妹妹提着一水桶小鱼喜滋滋地回家,刚走到院门口,就听到里面传出一个女人尖厉绝望的呼喊声,就像是有人拽着她的头发,狠命扇她耳光似的。喊叫的间隙,伴随着父亲粗重的吼叫声,玻璃破碎的声音,还有重物摔倒的声音。
我吓了一跳,不觉丢了水桶就往家跑。恰在这时,红姨慌里慌张地跑了出来,与我跑了个撞头!她披头散发,脸颊红红的,眼眶里还噙着泪,上身只穿了一件小背心,吊带歪斜着挂在膀子上,乳房像只小兔子,几乎就要蹦出来。低看一头,她还赤着两脚,裙子穿得也不端正。
我喊了一声红姨。她瞥了我一眼,竟没有要理我的意思。这时我才注意到,红姨左脸颊上还有两道鲜红的抓痕,就像是被猫抓的。我好奇地问,红姨,你这脸上是咋了?红姨没有回答,也没有迟疑,踮着脚尖,一溜烟地朝村外跑去了。她跑得那样快。树底下纳凉的街坊都觉得是刮过了一阵风。红姨!红姨!红姨!我连喊了几声。
背后响起一声冷笑。回头一看,母亲就站在身后,头发有些凌乱,脸涨得红红的,上面同样有些新鲜的抓痕。母亲冷冷地对我和妹妹说:记住,你们没有这样的姨!
从那以后,红姨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后来,我还多次想起过这个神秘的女人,想起她对我的种种好。只是,她再也没有出现过。
就在那天,父亲和母亲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战争。家里的东西几乎被砸净。他们开始互相指责、谩骂、殴打,并且越来越严重,逐渐成为一种常态——两天一小闹,三天一大打。家里能摔的东西基本全摔了,除了那台十四寸的熊猫牌黑白电视机。那是父亲托人从天津买回来的,花了五百块钱,当时还是个稀罕物。每天晚上看电视时,街坊邻居家的大人小孩都快把我家屋子坐满了。有一回,盛怒中的母亲抱起这台电视机想摔了它,后来犹豫了下,还是把它放下了。就这样,这台电视机幸免于难。可是,因为我们家天天吵架,邻居们都不到我家看电视了。
我和妹妹的日子过得心惊肉跳。放学回家,常常看到地上一片狼藉,冰火冷灶的,饭也没人做。我们只好上二婶家吃去。有人传言父母快离婚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偷偷躲到一个没人的角落流了半天眼泪。
有一天,我跟妹妹小莉在外面薅猪草,她问我,哥,如果爸和妈离婚了你跟谁过?我吃了一惊,妹妹比我还小三岁,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了?我感到了茫然。我反问她,你呢?妹妹愣了一下,说,我会跟妈妈过的。我说为啥呢?妹妹说,爸爸不喜欢她,老早前她就知道了。我说,怎么会?爸爸妈妈都喜欢你——你多可爱!妹妹说:你以为我小,其实我都明白了——我不是咱爸亲生的!我生气了,冲她吼道:小莉,你别听那些人乱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净瞎说!妹妹叹了口气,将一棵嫩生生的面条菜从泥土里拽出来,扔进了荆条篮子里。她看了我一眼,说,我什么都知道!
很快,父母就分别找我们谈话了。先是父亲把我叫到跟前,神情严肃地问我,如果我跟你妈离婚,你跟谁?我说,谁也不跟,我跟爷爷过。父亲说,不准赌气,我是认真的。我顶了他一句,说,你要跟妈离婚,我一辈子不原谅你!父亲一下子愣住了,半天没说话。我这么说当然有我的理由。因为我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残缺的家庭里面。我有个女同学,她父亲与母亲离婚后,又给她娶回个后妈,后妈待她不冷不热,她因此成了同学们嘲笑和戏弄的对象。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与父亲的绝决和冷酷正好相反,母亲对于离婚这件事倒是显出几分犹豫和软弱。有一天夜里,父亲不在家,她抱着我,流着眼泪说,她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婚,她舍不得我,舍不得我妹,更舍不得这个家。那时妹妹正在熟睡中。母亲的这番话让我的心稍稍安定了些。
自红姨走后,父亲一直呆在家里,也不出车了。他的脾气变得相当消极,或者说是相当暴烈。他整天游手好闲,不是跟他的狐朋狗友喝酒,就是打牌赌钱。偶尔回到家就跟母亲置气。摔锅摔碗的已经算不了什么,父亲一生气就要砸一块玻璃。窗户上已经没有一块完整的了。爷爷的病一天重似一天,可是他却全然不放在心上。我听到母亲在爷爷跟前哭诉,可是爷爷人老了,他管不了父亲了。本家的长辈也试图劝父亲回回心,把日子过下去。可是父亲铁了心要离婚,谁的话也听不进。大舅也来过几次,父亲都把人家干晾着,不理也不睬,弄得大舅也没脾气了。
农历五月十七的晚上,父亲和母亲大打出手,又干了一架。父亲把母亲摁倒在床上,把她的头往床沿上磕。母亲又踢又踹,总算腾出手来,扇了父亲一耳光。父亲捂着脸,走到门口。那里摆着一个脸盆架,上面搁着香皂毛巾之类。母亲冲父亲的背影丢了一句:想离婚,除非我死!父亲抓住一块香皂,朝母亲掷来。母亲头一偏,没掷中,投中了梳妆台上的镜子。镜子破裂了,但镜片还在那里拼凑着,没有掉下来。父亲头也不回地走了。母亲坐在那里愣了半天。我和妹妹被吓哭了。那天晚上父亲没有回来。
第二天是五月十八,母亲要到漳河对岸的一个镇上赶集。她有个表姐嫁到了那里。她和那个表姐自小一起长大,比亲姐妹还要亲。那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母亲正坐在梳妆台前给自己编辫子。她的心情好像很好,似乎将昨晚的事情全忘了。她一边哼着歌,一边给自己编辫子,还换上逢年过节才穿的新衣裳。我睡眼惺忪地问母亲,妈,你要出门啊?
母亲说,去河南你姨家赶集!傍晚我就回来!你好好看家。我耍无赖要一起去。母亲说,你爸不在家,爷爷又病着,家里没人不行。再说怪远的,还要穿过一大片河滩地,荒无人烟的,也没有什么正经路。你还是在家看门吧!我吵着不依。母亲哄我说,赶集回来给你买炸糖糕吃。我这才破涕为笑。这时妹妹也醒了,听母亲要去赶集,死活就跟了去。母亲起初不同意,后来实在拗不过妹妹的哭闹,就答应带她一起去。
母亲对我说,她和妹妹傍晚前一定赶回来,记得中午要喂猪,爷爷要有什么事的话,就去喊你二婶。我应一声,看着母亲给妹妹穿戴整齐,她们出了门。妹妹还回头朝我笑一笑,歪着头说,哥哥,等我回来带炸糖糕给你吃!
我苦熬了一天,做好晚饭,还不见母亲和妹妹回来,心里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爷爷催问了几遍,我心里也是火烧火燎的,就到大门口去等。不一会儿,父亲回来了,黑着脸说,别等了,你妈和你妹跟着那个河南人跑了!
我不相信。可是那个叫根生的河南人确实也在同一天失踪了。他住的庵棚还在那里,锅碗瓢盆衣裳铺盖还在那里,可是人就是不见了。问那砖厂老板,老板也不知他的去向,他还生气地说,根生还欠着我二百块钱呢,这下没了人影,我找谁要去?
大舅、二舅纠结了一帮人闯进家来,问父亲要人。父亲只是冷笑,说,她是一个大活人,她要跑,我咋拦得住?大舅见多识广,思路清晰:谁看见了,有证人没有?父亲又是冷笑:这种事,还要证人?满大街都知道她跟那个河南人搞上了……二舅是个急脾气,一听这话就要干架,被人硬是给拦住了……吵吵了半夜,也没有理论出个结果来。
后来报了警,警方也找了好几天,仍然找不到母亲的踪影。据河南安阳县那个镇上的姨妈说,我母亲和妹妹确实是到她家走亲戚来着,吃过午饭,大约两点多点,两人就回家了。她眼看着她们踏上了那条通向漳河河滩的路,至于为啥没回家,她也不知道。警方又去查那个根生,结果是个流浪汉,什么也查不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我母亲和妹妹是跟着那个河南人根生跑了!
也就在那段时间,我养成了一个怪癖。放学之后,我喜欢一个人钻进屋里那口大立柜里去。那是母亲结婚时的嫁妆。关上门,里面一片漆黑。我蜷缩成一团,两手抱头,将头埋在两个膝盖间的空隙里。就当我不存在好了。我闻到了母亲衣服上的味道。我摸到了它。仅凭感觉我就知道那是一件军绿色的外套。因为我太熟悉它的颜色、式样和质地了。我想起了母亲穿着这件衣服时的样子。我忍不住啜泣起来。但没有人知道。
我想去找我的母亲和妹妹。
一个夏天的清晨,是个星期天。我偷偷上路了。我没有钱,就步行朝漳河南岸走。穿过一个叫下七垣的村子,就是漳河河滩。那里漳河水被截在上流的岳城水库,只剩下一大片干涸的石头滩。我曾多次去那里捡带有花纹的鹅卵石。但是那天,偏偏赶上漳河发大水,平时玩的地方都淹了,河水流得急湍湍,浪也大,一眼看不到边。河的对岸隐约能看到一些山峦、树木,还有更远处的村镇。不知怎么的,我相信,母亲就生活在那其中的一处。她在那里。妹妹也在那里。
我在河滩一直坐到天黑。爷爷一定在心急火燎地找我了,但我就是不想回去,不想回那个破碎的家。清冷的星光在天际闪现了,夜里的风也很凉。我必须回家去了。
在村口,我看到爷爷在那里等我。他一句责备的话也没说,只是用他那瘦弱、无力的胳膊哆哆嗦嗦地抱住了我。一大滴热乎乎的水珠掉在我脸上。我奇怪怎么会有热的雨。抬头一看,才知道爷爷在哭。突然,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大声哭起来。声音大得自己都感到吃惊。我感到非常害怕,我觉得我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个大窟窿,无论我怎么填补,都没法把它填平。
就是从那天晚上起,我开始失眠的……
(二)一封死囚犯的遗书
小山:
我的儿子!当你看到这封信时,应该有十八岁了吧(我恳求狱警帮忙,一定要等你满十八岁再把此信交给你看),是个大人了。我为你的成长感到高兴。而我肯定已不在人世,到另一个世界与你的母亲、妹妹团聚了。我要向她们表达我的负疚,我要向她们赎罪。我不乞求她们的原谅,因为我的罪过实在是太大,即使枪毙我十次、百次、千次、万次我也心甘情愿。可是我只能死一次……小山,希望你能够理解此时一个父亲对于儿子的那种心情。
在监狱的这段日子,我的心反而踏实下来了。即使知道死期已近,我的心也不再感到害怕。甚至我还期待着那个日子的到来。我唯一(原文如此)放心不下的就是你爷爷,他的病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可是我作为他的长子却不能守在他的床头,伺候他,照料他,尽一个人子的孝心,反而因故意杀人罪坐了牢,也许还要死在他的前头,这让他怎么忍受?唉。不说这个了。另一个我不放心的就是你。你小学还没有毕业,就遭受到这种不幸,实在是我的罪过。上次你跟着二婶来看我,本来我想再抱抱你的——我真的很想再抱抱你,紧紧地抱你——可是看到你那冷冷的眼神,扭着身子不面对我,我就知道你还不肯原谅我。也许在我死之前,都不可能得到你的原谅了。
我干的糊涂事——我怎么干的?我怎么会?——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好像那是一个别的人,一个不相干的人去干的。我宁愿相信是那样,怎么会是我呢?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也许是我太冲动失去理智了!我不该那么做,害我全家,害了你,也害了我自己。后悔已经晚了。我只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去承担罪责了!死吧,他们会判我死刑的。我必须去死。只有死才能让我解脱!
小山,不知怎么,现在我想到的都是你母亲的好。我和你母亲的婚姻虽然出现了种种问题,但是她对这个家是出了力的,是有功劳的。自从贷款买了拖挂开始跑货运,我就基本把家里的事丢给她了。有时我一出去就是一个多月,你母亲就在家里操持一切,上有老,下有小,种着几亩地,又养着猪,家里的重活、脏活、累活还不是她一个做?想一想,秋收农忙,地里的那些活她又该怎样犯难,怎样求人呢?但是你母亲都挺过来了,家里家外的事情打理得很好,老人、小孩也都说她好,这多不容易!可是我,竟然干出了对不起她的事。在那之后,你母亲也没有非要和我离婚,她是想包容我犯下的过失(“过失”两字被重重地划掉,改作“错误”)的,可是我竟然干下了那件混事!唉,我真恨不得一头撞死!!!
小山,千言万语也说不出我对你的愧疚,我没有给你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我希望你能原谅我。最后让我以人生的惨痛教训给你提三点告诫:一是要理智地对待生活的困境,切不可冲动行事;二是要为你所作所为负起责任;三是要对你的亲人好,将来有了妻子,有了子女,要对他们好,万不可像我这样!切记!
祝一生平安!!!
父 姚建国 绝笔
199×年12月4日
(三)一篇旧闻
×县公安局成功破获6·26漳河滩特大杀人案
据×县公安局报:日前,在全县公安干警的日夜排查下,震惊全县的6·26漳河滩特大杀人案成功告破,犯罪嫌疑人姚××对其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今天上午,记者随姚××对犯罪现场进行了指认。其隐匿的凶器、作案时穿的血衣也被一一找出。
199×年6月26日,一场特大暴雨过后,漳河河滩××乡段惊现两具无名女尸。其一年约三十岁,体貌粗壮,身高1米65左右;另一年约八岁,身高1米25。两人均是腹部被利器捅伤,脾脏破裂严重失血致死。因死亡多日,尸体严重腐烂,面貌难以辨识。后经当地村民贾仁民辨认,两人疑似附近×村前不久失踪的曹××、姚××母女。
犯罪嫌疑人姚××系死者曹××丈夫,姚××父亲。姚××疑心曹××与人有染,怀疑姚××非自己亲生女儿,又因家庭琐事遂对曹××怀恨在心。趁曹××携女儿姚××外出之际,将其残忍杀害,并埋尸荒野河滩。姚××对外宣称,曹××母女随奸夫私奔。本以为天衣无缝,孰料一场暴雨将其罪行暴露于天下……
(四)一件小事
陈振山看到姚小山蔫头耷脑地从街角拐了出来,他截住了他。陈振山说:“小山,你知道吧?我是咱村里跑得最快的一个。”姚小山点点头。的确,陈振山跑起来像风一样快,两只脚就像踩着风火轮一样。
“可是,西曹庄的大奎跑得比我还要快。”陈振山说。
“嗯。他确实比你跑得快些。”
“这太糟糕了!”陈振山说,“爹答应我,这次乡里举办运动会,只要我能拿到长跑冠军,就给我买一辆新自行车。”
“嗯。”姚小山明白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对于陈振山和他的诱惑,“所以呢?”
陈振山搂上了姚小山的肩膀,嘴里呼出的热气直扑姚小山的脖子。他说:“小山,你帮我个忙呗?”姚小山不解地看着他。陈振山说:“我想出了个好主意。只是那个东西只有你才有。”
“啥? ”
“安眠药片。我们把安眠药片和进汽水里给大奎喝,他还能跑那么快吗?”陈振山扬起眉毛,两只眼睛闪着光。他笑了起来。
姚小山哼一声扭头就走。陈振山急忙拽住他:“嘿,听着,我赢了比赛得了自行车,你啥时候想骑都行!”
姚小山的眼睛倏地亮了一下。他抿了抿嘴唇,使劲咽了一口唾沫。
母亲和妹妹姚小莉就坐在跟前。头上、身上挂着几条褐绿色的水草,衣服破了好几个洞。眼神空洞、呆滞,好像在看着一处并不存在的地方。
姚小山被吓醒了,出了一身冷汗。他一翻身,看到父亲正坐在床前。“我听你二婶说,近来你老睡不安稳。”父亲说。
姚小山没有吭声。他不想搭理父亲。自从母亲和妹妹离家不知去向后,他根本不想与父亲说话。
父亲叹了口气,用粗糙的大手摸了摸小山的头顶。他说:“小山,心事别那么重。一切都会好的。咱们还要生活下去。”
姚小山突然扯起被子把头和身子全蒙起来。等他掀开被子,父亲已经走了。但父亲这次出车回来,给他买的那本《笑话大全》还放在床边的桌子上。姚小山把它狠狠摔到了墙上。挂在墙上的全家福照片掉到地上。玻璃全摔碎了。
“凑够药片了吗?”一天放学后,陈振山将姚小山拉到偏僻处,悄悄地问。“够了。”姚小山说。他们的头凑到一起交谈,像特务接头一样诡秘。“到时,你就这样做,明白?”陈振山说,“要自然,热情,不能让人看出破绽。”姚小山郑重地点点头。
阳光空前的耀眼。天气也热得不行。站着不动都是一身汗。姚小山口干舌燥,手里拿着两瓶开了口的汽水,但他没有喝。他的眼睛在左顾右盼。他在找人。运动场上到处是人。可就是看不到他心中的那个目标。
陈振山出现了。凑到姚小山耳边低语,眼睛却瞟着不远处的一个高个子黑皮肤的男生。那个男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两条大长腿,站在人群里犹如鹤立鸡群。“呶,大奎在那里。”他说,“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
“药片放到哪个瓶子里了?”
“这个。”姚小山右手动了动,“商标上撕了一个小豁口。”
陈振山迅速瞟了一眼,他看到姚小山右手那瓶汽水的商标确实被人撕了一个雪白的缺口。“你要记准。别把有药的瓶子给我。记住!”陈振山叮嘱着。
“嗯。放心吧!我还等着骑自行车呢!”姚小山说着笑了,但是笑容却在瞬间凝固了。陈振山看到有两名警察正在朝这里走来,他们一边走一边打听,像是找什么人。
陈振山不再关注那两名警察。警察找人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朝大奎打了招呼,说要请他喝汽水。大奎迈着两条大长腿走了过来。他的额头上正在流汗,嘴里干得像是要冒烟。他跟陈振山很熟,因为他们每年都要参加乡里办的运动会。“嘿,你们有好东西!”大奎说着,从姚小山手里夺过一瓶汽水。
陈振山和姚小山目瞪口呆。大奎夺走的那瓶汽水商标是完好无缺的。姚小山看了一眼陈振山。陈振山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大奎将汽水瓶送到嘴边,仰起头,咕咚咕咚喝起来。他的喉结在一动一动地,瓶中的汽水在迅速减少。陈振山眼睛一眨不眨盯着他。“真痛快!”大奎喝完了,将空的汽水瓶扔到一边,“你们喝呀,你们不渴吗?”
两名警察走了过来。“请问,你们谁是姚小山同学?”
“他是!”陈振山和大奎一齐指向姚小山。
姚小山看了看那两名警察,又抬头看了看天。云彩像是软绵绵的面团。连一只鸟也没有。姚小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手里那瓶汽水,送到嘴边,仰起脖儿,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了它。
“真痛快!”喝完后,姚小山抹了抹嘴说。丝毫没有理会陈振山朝他投来的诧异的目光。
责任编辑/乙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