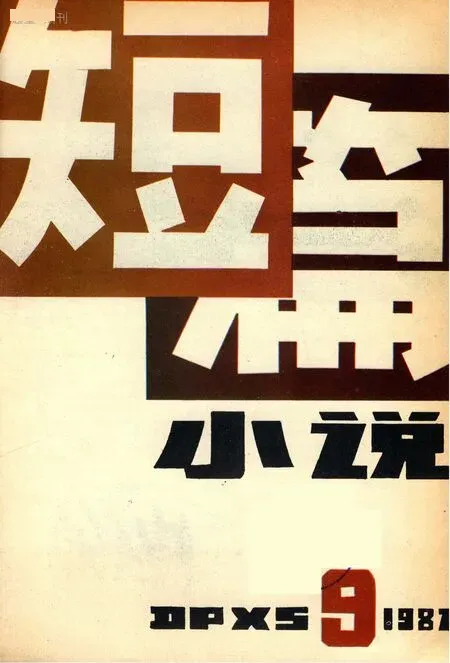小纸人
◎哈 利
小纸人
◎哈 利

天佑从天晴的坟头经过,如果不是横在他面前的石块,他几乎就从天晴的尸骨上踩过。他低着头看那石块,青灰色,露出规整的一角,微微上翘,如同“泰坦尼克号”沉入水底的前一刻,做着最后的挣扎。周围长满杂草,他的脚陷在里面,格外松软。他带着好奇心去搬那石块,惊动了一米开外草堆里的雏鸟,它们毫无怯色地对着这个陌生人尖叫,似乎早已确信他不会伤害它们。看来这家伙很大,他卷起衣袖铆足了劲猛地去掀石块,杂草被他踩得纷纷向后倒去,植物又腥又涩的气味蔓延开来。原来是一块石碑,他喃喃自语道。石碑底下是虫蚁的洞穴,它们常年在潮湿阴暗的环境里生活,因为他此刻的打扰,它们飞奔着逃命。他被宏伟壮阔的搬迁场面震慑住了,便试着以虫蚁的方式去看待自己此刻的行为,毫无成效。石板上面刻着字,是的,刻得很深,那应该是蚂蚁们最方便的住所了吧。他用那四位数价格的衬衫擦着上面的泥土,毫不心痛,多少年以前,他也喜欢这样擦东西,多么方便,多么干净。一会儿之后,那破败不堪的石板上完完整整地显现出了四个字——徐天晴之,后面一个字是“墓”,他在附近刨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天晴是天佑的双胞胎妹妹。生前是个傻子,也许死了不是。
“快点呀!快点呀!”
天佑左手抓着线团右手拉着线在大片的麦田上奔跑。麦苗刚从寒冬中醒来,脑袋怏怏地垂到枯苗间。踩在这被新生的嫩绿色分隔的支离破碎的土地上,他的脚步落得并不平稳,也许是因为脚下的泥土尚未解冻,也许是为了避免踩到麦苗。只要妈妈没有拖他回去吃饭或者麦田的主人不轰走他们,他都不打算结束。初春的寒气像动物的绒毛,扫过他的皮肤,唤起似有若无的痒意。他犹豫着去抓,不应该太用力,否则就不会留下指甲尖尖的痕迹。他的手指轻轻拨线,小纸人的身体微微往下扣,他加大奔跑速度,猛地抛出一节线的时候,小纸人慢慢地舒展身体,徐徐飘向高处。他张着嘴,不敢轻举妄动。多么轻盈美好,仿佛它一早就属于天空。
“等等我们啊……”胖子喊道。
天佑回过头,胖子的风筝还抱在胸前。是一只展翅的老鹰,羽翼丰满、眼神犀利。牛皮手里攥着风筝线,在跟胖子吹牛皮。他的鱼在空中飞得并不顺利,忽高忽低。之前还挂在胖子家的屋顶上,他爬上屋顶取风筝的时候踩掉了两片瓦,胖子的姐姐伸着脖子骂道:“死孩子,这群死孩子,怎么不去死呢……”她的话语明白无误地展示了她极其差劲的语言功底。她骂人就这几句,他们早已习惯,但是猛地听到还是会头皮发麻。村子里人不常说“死”字,死字不吉利。
天佑继续跑,枯草在他的脚下吱吱作响,越冬的田鼠刚探出脑袋就被吓进洞。天晴跟在他的后面,像一片空气,无声无息,他有时候故意转过身看她有没有跟来。大部分情况下,他都会失望。天晴面无表情地跟着他跑,全身上下没有任何关于跑步的痕迹。她的体力惊人,这得益于她惊人的饭量。鉴于她是傻子,一家人从来不会觉得吃三碗面很奇怪。
天佑从一生下来就讨厌天晴,更讨厌她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好像他们真的彼此离不开对方似的。他俩本来长得就很像了,所有人都知道天晴又是个傻子,天晴还要跟他走在一起。要不是他经常手里攥着一个小纸人而天晴没有的话,那些老的早已不知道自己年龄的老人会拉着他的手说:“傻闺女,来……”。
小纸人啊小纸人!这个小东西,比他本人更加具有标志性。
天佑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剪小纸人的。当剪刀跟白纸一起摆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想都没想就剪出了一个小纸人。他的技法并不熟练,因此小纸人的脑袋周围长满了刺,身体扭成了一团。他回过头看了一眼坐在地上的天晴,那时候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天晴是个傻子了。天晴手里拿着一个被啃得乱七八糟的苹果,蚂蚁排着队,从门口排到她手里的苹果上。对着这样庞大的侵袭者,她无动于衷,她甚至将落后的蚂蚁捉起来搁到了苹果上,苹果已被氧化,棱角处发着黄。太阳从天晴的后面跨了过来,她的影子并不大,但完整地投在了前面的空地上,很具体,一个明白无误的小纸人,天佑照着那影子,剪掉脑袋上的刺,舒展开身体,没错,是一个人形。
天佑减慢速度,天晴猛地冲过来撞到了他的背上。他的身体因为惯性滑出了一米多,线团落了地,风筝在天空中降了一截,他委屈得快哭了。他出门前没来得及吃妈妈刚蒸好的红薯,都是为了让自己的风筝飞得又高又远,最好能飞进天堂。天堂是他奶奶的住处,奶奶临走前想摸他的脸,他没走近奶奶就闻到尸体腐烂的味。他跑了,出门之前,他听到阴阳先生在说天堂的事情。他凶狠地抓过天晴的手臂,坚硬而冰凉。天佑觉得自己抓住的不是什么人而是一个树干或者其它什么,总之是不会自己撞到他的活生生的人。天晴流着涎水,毫无想法地嘻嘻笑。天佑受了冷似的,打了个颤。天佑盯着天晴,就像是盯着自己。他们多么的相似,要不是他以前经常听人说起,今天又突然仔细追究的话,他将会毫不知晓这个事实,或者只是他迟迟不肯承认。他们的鼻子直直挺立,上嘴唇微微凸起,眼睛大而圆,不,是天晴的眼睛大,简直就像是深不见底的井口,天佑坚信,即便是在里面扔进去一个石块,回声也不会顺利传到井外。
“你们快点赶上来嘛!”天佑故意将目光越过天晴。
这时候胖子的鹰跟牛皮的鱼已经缠在了一起,牛皮丝毫不在意。他还在给胖子讲自己的见闻。
“我昨天在那条河里钓了两条大鲤鱼,那鱼可真是了得,有这么大……嗯,是这么大,大吧?反正我们一家人没吃完,剩下的都给我家的猫吃了,说起我家的猫,哎,你知道我家的猫是从哪里来的吗?不知道吧,前几天我爸上城里逛,那只猫一直跟在他身后。你说怪不怪,猫这种动物,什么时候会缠人的?可它偏偏就认准我爸了,我爸觉得一个小动物在外面闯荡很不容易,就带回来了……”
“你说那条河里有鲤鱼?”胖子打断他。
“对呀。那条鱼长得可真是漂亮,它在水里吐泡泡,我想将它养起来,我爸说养鱼的男人没出息……”牛皮说。
妈妈经常去村头的小卖部里买白纸,一次买一沓,人们都很奇怪。那样厚实致密的白纸都是那些老先生买回去写毛笔字的。妈妈告诉他们她家的孩子,没傻的那个,也就是天佑,喜欢剪纸。她说那话的时候心情格外的激动,仿佛一早就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了。天佑想那时候人们肯定不怎么相信妈妈,妈妈的一个孩子是个傻子,人们唯一能够想到的是另一个也聪明不到哪里去。大约一两个月之后,天佑家的窗户上贴满了小纸人,开口大笑的、撇嘴皱眉的、忧愁无奈的……刚开始妈妈觉得窗户上贴着白色的纸人有点奇怪,说不清为什么奇怪,就像在吃东西的时候咬到石子了似的。慢慢地看习惯了,也就释怀了,不碍事,不碍事……不管怎样,现在大家都知道天佑会剪小纸人了。对于这个消息的传出,人们先是惊讶后来又慢慢地想通了,现在外面大部分的人都这样说,“肯定是天晴的聪明劲在娘胎里就被天佑给吸走了,不然天佑这孩子手怎么这么巧,剪出来的小人简直跟真的似的”。他们是双胞胎,大家都很认同这样的说法,妈妈也是。因此妈妈也开始细心照顾天晴,她是个可怜的孩子。当然,这也不能怪罪于天佑,孩子们泡在羊水里的那会儿,脑袋都是不大开窍的。天佑倒想,如果可以,他宁愿自己不会剪小纸人,也不要自己的双胞胎妹妹是个傻子。
天佑的风筝开始往下掉,他必须用手不停地拉线以保持高度。以往这样的季节风总是很大,今年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空气里像加了黏合剂一样,紧巴巴的,困住了所有的东西,除了天空,天空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他真想住在那里,但那里是天堂,只有死人才可以去,阴阳先生一早就跟他讲过了。所以天佑的家只好一直被困在那里——田野最东面,前几年那里还是人声鼎沸,现在稀稀拉拉地只剩下几户人家。在这短短的几年里,邻居们因为得知他家那地方风水不好,容易冲着祖宗,所以前前后后搬走了。风水上的东西,自有阴阳先生来解读,天佑管不了那么多,但每次还没到门口就能听见妈妈在院子里哭泣,心里总有点犯嘀咕。没准真是冲着祖宗了。妈妈哭的时候天佑都会逃难似的离开,然而妈妈总是需要一个人来聆听她的苦楚。每次当天晴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妈妈便已经扑过去抱住了她。天晴在湛蓝的天空下嚎叫起来,像一只即将被宰的猪。妈妈不在乎那叫声的惊天动地,因为迟早都会被自己的哭声盖过去。妈妈从头开始讲,妈妈说,我小的时候父母把我当宝待,我要什么父母就给我什么,要不是那个天杀的……呜呜,你们一出生,什么都变了,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天晴啊,我的傻女儿,为什么那么多的活物偏偏傻掉的是你……这些话她一直都在说,她似乎从未厌倦。她哭完之后,站起来掸掉她跟天晴身上的土,轰走门口的孩子,去门口的柴堆里捡一捆柴开始点火做饭。她扯着哭哑的嗓子告诉天佑今天还是吃面吧。
胖子解开了他们原本纠缠在一起的风筝,牛皮双手挥舞着跟胖子比划着什么。他们眼看着要跨出田野了,天呐!田野不是一望无际的吗?为什么他们几步就走出去了。天佑绝望地站在原地,握紧拳头说,不,不能,风筝一出田野就会挂住。他一边拉着风筝线,一边喊他们的名字。他们都没有回头,他们就是这样,不想回头就不回头,有时候他们会喊天佑是傻哥哥,也就是傻子的哥哥的意思。他明明不是傻子,可是他为什么要承担一个傻子的屈辱。是谁在尖叫?太过刺耳。天晴,又是天晴。你就不能不发疯吗?!天佑想也没想甩了她一巴掌:“傻子!都是你!!”天晴停止尖叫,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她歪着脑袋,用那双空荡荡的眼睛盯着他看,又是两个深深的井口。
转眼二十几年就这样过去了。路被重修了,老房子也新修了,就连以前寸草不生的荒地里也被合理化利用了。人们在那里建了几座工厂,那些高高耸立起的烟囱源源不断地将烟送到云的位置。村头村尾的小超市门口搁满台球桌,人们穿着入时的衣物谈论火箭与比尔·盖茨。只有脚下的田野还是原样,长满麦苗,它们已经齐人的腰了。再过一两个星期也许就会被轰鸣着的收割机收割轻轻松松地装入粮仓。
几个小时前他启动发动机之前跟妻子吵架了,因为他又借钱给朋友了。他那朋友正在创业,时时刻刻都需要钱,他没有钱就没法创业,他跟妻子解释。妻子没有多听,在他说了钱字之后就开始数落他。妻子说他是乞丐的命,存不了一点钱,孩子以后要留学要买车要买别墅,为什么他就不能为这个家考虑一下!?他受不了了,他们家已经过了缺钱的时间段了,他一点也不理解妻子为什么会考虑二十几年之后的事情。吵来吵去,整天吵来吵去……太累人了,他需要休息休息,是的,他很需要休息。这地方他原本没有放在心上,虽然他在这生活了将近二十年,但是他早已不属于这里了。他当初开着小轿车接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会儿,他已经打算好不回这里了。那时候妈妈已经不再哭自己的命苦了,自从天晴死后,他们家突然变的跟其他孩子的家一样幸福安乐了。两个老人起初还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后来等他孩子一放假,他们也就都去疼孙子了。如今他们也开始悠悠闲闲在公园里打着太极,操着一口变味的普通话跟人们聊天气。而这里,要不是因为一望无际的田野可以扩展视野,他根本不会将车停在这里。
他的目光再一次落在了石碑上,那石碑上是被什么东西突然撞断的,横断面格外的整齐。因为缺了“墓”字,怎么看都觉得是缺憾。
“哈哈……天佑啊!真的是你?我在村口看到你的汽车了,多少钱?我也想换个。”一个高高胖胖的男人走近他说。
男人刚吃过羊肉,一张嘴就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膻味。他的肚子像充满了气的气球,圆鼓鼓地对着天佑。天佑不敢走近一步,他怕他走近一步,那肚子就会破掉。
“你不记得我啦?想起来没?哎呀呀……你看你,贵人多忘事,才十几年没见,你就把你兄弟忘了。”胖子表现出来的失望与心痛让天佑不知所措。
“哦,胖子呀。”天佑说,他觉得自己的语气还不够热烈,于是说完之后,只顾着傻笑,好像真的久违了似的。
胖子现在是真正的胖子,胖子大概没想到小时候孩子们给他的称呼会成为他今后生活的真正的写照。不管怎样,在此刻胖子还是显示出了任何一个成年人都应该有的豁达。
“哈哈,想起来了吧,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呀?”胖子问道。
“哦,没什么事儿,回来看看。”天佑连忙应付道。
“怎么?这是谁的墓碑?徐——天——晴——之——哦,这不是你们家那个傻子吗?呐,抽烟不?不抽?你小子现在越来越扭捏了。这烟贵得跟女人的奶子似的,味道嘛,也还凑合。”胖子说。
鸟妈妈叼着一片塑料,朝着他们飞来,等到接近他们时犹犹豫豫地不敢落地。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它叼着那塑料落在了不远处的草堆里。那塑料片看起来眼熟,很像孩子们经常喝的酸奶吸管上的包装塑料,单薄透明。
“说起傻子,她也算死得其所。不管谁家要是摊上这样的孩子,谁还不得盼着她早点入土,你说要不是那会她自个跑到河里,那河正好又是有个沙坑……”
妈妈说:“不要带天佑去河里!”妈妈是说给牛皮跟胖子听的,他们总是一起出现在天佑家,他们像连体婴儿一样,齐刷刷地站在天佑家的院子里逗天晴。天晴跪在地上给母鸡捉虱子,他们用树枝挑着地上的一块鸡屎喂天晴,天晴用脏兮兮的手接过去一直看。妈妈看到后冲出来指着他们边骂边哭:“你们这些混蛋都欺负我家天晴是傻子……”随后他们跑了,喊着天佑的名字,于是天佑也只好跟着他们跑。房屋跟树木纷纷向后倒去,空气被他撞得横七竖八,躺了一地。他的身后传来妈妈的声音:“不要带天佑去河里,河里有坑。”
“河里没坑,谁说有坑?”那天他们收起风筝之后,牛皮这样说道。
牛皮还说:“我跟我爸在那地方游过水,就像青蛙那样,双臂展开,划呀划,你个死胖子,你不跟着我学……”
“可是,我妈说……”天佑手里抱着小纸人。
“你妈生个孩子都是傻子,知道个啥?”牛皮说。
“走吧,怎么会有坑,人家都在那里钓了鱼。要是真有坑,鱼早就掉进坑里了,怎么能钓上来呢?”胖子拽走他。
那天,他们一致决定不再放风筝,这样的天气就不应该放风筝,没有风放的啥风筝。天佑每走一步天晴就跟着走一步,天佑停下来天晴也跟着停下来。天佑真想甩掉天晴,就像甩掉黏在手上的脏东西。但是他无能为力,这件事他真的无能为力。他记得曾经有人跟他说,双胞胎都有心灵感应。妈的心灵感应,如果真的有,为什么天晴还一直跟在他的后面。胖子的姐姐穿着花衣服,扭着肥大的屁股在他们的前边走着。她今年二十岁了,是该嫁人的年纪了。她看起来一点也不着急,每隔一段日子便悠哉游哉去街上相亲。年轻的小伙子都看不上她,都说她的嘴毒,会毒死人。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牛皮油着嘴唱道。
“你们这群死孩子!怎么还没……”胖子的姐姐还没骂完,牛皮就跟胖子一起喊道:“死!”
那声音过于洪亮,尤其是在初春的正午,太阳都还是眯着眼上工。树木没站直,牛羊还在畏寒,虫子蜷在洞里不敢叫的时候,那声音像是碎在头顶的玻璃,清脆响亮。
胖子的姐姐拍着大腿,两只眼睛瞪得跟斗鸡似的,嘴里的唾沫如热锅里的油噼噼啪啪地往出溅。她说:“你们这群死孩子!怎么不去死。”
一辆黄色的巨型吊车轰隆隆从他们的面前开过,吊车前面挂着的巨大的钩随着吊车一晃一晃。他们张着嘴看着那个类似于凶猛异常的动物的嘴一样的钩。那钩被他们盯得毫无表情,只顾着炫耀自己嘴里那两排光滑锋利的锯齿。等那车过去之后,胖子的姐姐不见了踪迹。胖子说她姐准是跑着去相亲的,他爸命令他姐必须在今年找到对象。
那条河不知道从哪里流下来的,也不知道它要流向哪里,但它总算是经过了这个村庄。水面本不宽阔,还被周围的芦苇围绕,这样一来原本称之为河的那条河,就只剩下狭长的一道,远远看去就像是掉到村子里的一条脏兮兮的布条。河水的浑浊,众所周知,大老远人们闻到那里的腥臭味就溜了。这哪是河?简直是牛皮家的嘴。牛皮一家都喜欢吹牛皮,人们都心怀怨恨,说他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是臭的,当然最臭的还是他们的嘴。水面上还零星飘着些草叶、塑料袋,都是从前面的大路上刮下来的。
“就是这里,这里有鱼。”牛皮说。
“水好脏呀。”胖子嘟囔着说。
“就是这里,你别不信,我跟我爸就是在这里钓上来的。”牛皮将手里的鱼塞给天佑说。天佑发觉那鱼的背已经折了,以后都不能飞了。
“那你帮我钓一条吧,我们今天都惹恼了我姐,我回去肯定要挨揍的,只要我有了这条鱼……嘿嘿。”胖子说。
“啥?上次能钓到这次不一定就能钓到的嘛……”牛皮失落地说。
天晴站在河边看自己的倒影,十分入神,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她很少回应别人,即便是回应那也不一定真的是回应。
“哈!有了!……傻子,喂,傻子!跳下去给我们抓条鱼吧。”牛皮兴奋地喊道。
天晴没做反应,她蹲下来,用芦苇不停地拨着自己的影子。看着自己的脸与身体随着水纹波动,她张着嘴像小孩子一样在那里咿咿呀呀地叫。
“不行,水里有坑。”天佑说。
“什么不行不行啊!有茅坑!我跟我爸还在这游过泳呢。傻哥哥……傻哥哥……怎么样?要不要让她跳下去,待会儿上来之后,我们用火给她烤一烤。”牛皮说。
“我妈说河里面有坑……”天佑说。
“没有坑,肯定没有!别听人胡说,你看你,以后都不想跟着我们啦?”牛皮说。
“你不想跟着我们啦?傻哥哥。”胖子说。
“你们?!太过分了……你们。”天佑不是傻子,为什么所有人要把他跟天晴连在一块呢。
“傻哥哥……傻哥哥,有个傻妹妹,傻哥哥不让傻妹妹下河,傻妹妹不知道要不要下河。”牛皮这一会工夫就编出了一个顺口溜。
“哎,胖子,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傻的吗?听说他们的妈妈年轻时候,很放荡啊,到处种孩子……”牛皮说。
“什么是种孩子?”胖子说。
“来!过来,我告诉你。就是一男一女睡在一起,扑通扑通,像鱼一样,然后就会有孩子。天佑跟天晴就是这样来的,啊……说不定你俩不是一个爸呢,你想,可能是天晴的爸先跟他们的妈扑通扑通,然后天佑的爸又正好遇到了,所以又开始扑通扑通……总之就是扑通扑通……”
“哈哈……扑通扑通。”
“哈哈……扑通扑通”
……
他们的对岸是芦苇丛,芦苇扎根这样的河底却异常茂密。它们跟麦苗一样并没有完全苏醒,浅绿与深褐夹杂着向上生长。河水呈黑褐色,流得很慢,有石头的地方水面会突起。
天佑将手放在天晴的肩膀上,天晴转过脸望着他笑。天晴总是对着人笑,毫无内容的笑。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干净却毫无透视感,目光很容易被这白色折断。
天佑一直想如果当时他的手没有放在天晴的肩膀上,而天晴没有对自己的影子着迷的话,也许她就不会掉到河里,也就不会死掉。但是他那天拍打天晴肩膀时,手上的力度确实有点大,天晴自己的一只脚原本已经耷拉在水边了。
天晴从河边翻滚下去,仅仅用了几秒时间。她庞大的身体将黑色的水面砸出了一个洞,在此之前,天佑从来没有发现天晴很健壮。她落水时,跟平时一样无声无息,也许在那一瞬间,她还在琢磨着些什么。但是落水之后,他们三个人都发现了其中的异样。坚硬的河水的碎片到处飞溅,打在芦苇叶上,簌簌作响,天晴的双臂在水面上拍打着,这动作很像母鸡拍打尘土,她的衣服上缠上了芦苇叶,她的脖子处的污迹是她很久没有洗澡的缘故……小纸人并不难剪。有太阳的时候,天晴站在院子里,天佑按照天晴在地上投下的影子剪小纸人,没太阳的时候只好直接照着天晴的样子剪。这两种方式剪出来的是两种效果,前一种没有表情需要他慢慢添加,后一种轮廓不好确定需要不停地改动,天佑自己比较喜欢前一种方法。
“天晴掉下去了!天晴掉下去了!!”
天佑回过神发现天晴的脑袋在水面上一上一下地挣扎,像有什么东西按在她的脑袋上似的。
“把那东西拿开!”天佑说。
“把你脑袋上罩着的东西拿开!”天佑又说。
水面在咕嘟咕嘟地冒了几个泡之后,像鱼吐完泡似的,天晴的脑袋掉下去了。
几秒之后,水面慢慢恢复了平静。
没有人会游泳,那时候。尽管牛皮将自己的游泳技术吹得非同一般,可是他的一只脚沾到水时就吓哭了。他说他不想死。天佑不知道怎么办,他站在河岸上,喊天晴的名字。那名字格外的陌生,他每喊一次都会怀疑一次,以前他跟着别人叫她傻子。没有人回应,胖子早已跑得不见了踪影。天佑站在那里,青灰色的天上飘着几只风筝,因为没有风很快就要落地。天上没有小纸人,小纸人在刚才的混乱之中不知道掉到了什么地方。周围的芦苇凭借自己的韧性恢复了原样,只是那后面似乎多了一种颜色,黄色,对,是他们从路上经过时那个吊车的颜色。从他那个角度看去,吊车上的钩如同一张受了惊的嘴,正对着他。
记忆是巷子,可以前进也可以后退,但是有关天晴的那一段正好截止在溺水那一刻。即便是天佑重新站在天晴的坟前,他依然记不起多少。也许天晴死后他们给她买了一个棺材,小小的,精致的,正好可以容得下一个十五岁孩子的棺材。他们会吹着唢呐将棺材埋在地下,妈妈会流着泪挽留她女儿,她那跟她命运一样不幸的女儿……幸好还有眼前这个坟墓,不然,连他自己也会怀疑她是否存在过,或者他根本不愿意承认她存在过。
胖子邀请天佑去他们家的高级餐厅看看,天佑推说自己还有其它的事情。胖子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小子太扭捏啊,叫你吃个饭也不赏脸。天佑难为情地笑,胖子也跟着笑,他的笑宏伟壮阔,震得远处的草叶微微发颤。胖子挪动着自己那两条臃肿的腿走了,天佑看到他走得奇快,彷佛不是走在土地上,而是乘着什么神秘的交通工具。一阵风从田野深处吹来,麦田向前倒去,很快就掩埋了胖子的身影。他蹲下身刨了一个洞,将石碑重新插入了其中,并不顺利,少了“墓”字那一块,底座是倾斜的,所以很难平稳地竖起来,他只好重新考虑。鸟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了雏鸟的身边,雏鸟们叽叽喳喳,吵得不像话。鸟妈妈不予理睬,双脚蹦直跳到旁边一个鸟窝里,那鸟窝看不出新旧。它将叼来的塑料搁在了鸟窝里,随后陷入了沉思。跟他一样,鸟儿们也有鸟儿们的难题。他用手继续刨,他的白嫩的手指起初还因为碰到了石子而出了血,但遇到泥土时很快伤口黏住了。自从他离开这里他再也没有碰过泥土,他的卧室里、办公室里虽然也放着几个盆栽,但里面的植物都用的是营养水。它们不用土却欣欣向荣,但是现在看到地上的肆意生长的杂草时,他隐隐觉出了其中的可悲。这种可悲感还没有强烈到妨碍他继续在卧室里养用营养水供养的盆栽。十几分钟之后,一个长方形的坑浮出了地面。他蹲着去拖那个石碑,脑门的汗珠噼里啪啦地往手上掉,他抬起头,正午的阳光劈头盖脸地泼了下来。往日这样的时候,他正在清爽宜人的办公室里看文件。他给石碑掩上土,又从旁边抓起一把野草盖在了上面。多少年前,人们埋葬天晴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的过程,不知道那时候人们是怎样想的。在他准备起身的那一刻,他瞥见那鸟窝高出地面许多,而隔着草木,他隐约可以看见在鸟窝没有完全覆盖的边缘,有着与石碑一样的颜色——青灰色。对!就是它,等到他站起来走近那鸟窝时他便更加确信那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墓”字。即便他看不到那“墓”字,但那颜色已经昭示了一切。鸟儿们的智商不容忽视,他想。这石碑的高度已经足够防止夏天地面上的积水淹掉自己的家了。而那鸟窝看起来经历了许多风雨,旁边还有一个小洞,小洞上面补着几片塑料,格外醒目。他不需要迟疑,可是在蹲下身子的时候,鸟妈妈挡在雏鸟们的前面,对他怒目而视。
“我又不是想伤害你。”他说着将手伸向了那鸟窝。
“啊!!”鸟妈妈啄了他,惊讶胜于疼痛,他瞟了它们一眼,躲在鸟妈妈身后的雏鸟们依然毫无怯色地望着他。
“算了,也许那只是个普通的石块。”他说着离开了。
责任编辑/乙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