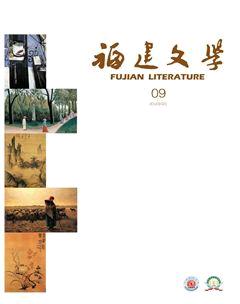佳佳的米店(外一篇)
曾建梅
小妹和男友去民政局排了六个多小时的队,把证给领了。晚上来电话,轻描淡写。倒是她男友在一旁兴奋得不行,说前一天晚上觉都没睡。
这是我最小的妹妹,尽管此前一直盼着她早点找到合适的人嫁了,但真正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五味杂陈。我最疼爱的小妹就这样变成别人家的人了?真是舍不得。
我们家姐妹仨,二妹打小像个男娃,没事儿把收音机拆着玩儿的那种,长大结婚当了妈妈,大家开玩笑管她叫“大哥”,她也欣然应之;小妹则是纯粹的小女生,工作之余最大的娱乐恐怕就是逛街买衣服,扮靓自己,——但常常是只逛不买,过干瘾,比起她那些月光族的小伙伴可高明多了,毕竟上班也蛮辛苦的。
成都的冬天冷风浸骨,她上班离家远,早上七点天还没亮就得挣扎着从被窝里起来,迷迷糊糊吃点东西,把自己从头到脚裹得跟粽子似的骑电动车去上班。到了夏天仍然裹得跟粽子似的,怕太阳把脸给晒黑了。曾经也想过做生意练摊儿,我说你干脆开服装店吧,反正你自己也爱臭美,但她仔细考量后还是没开,在这点上她倒还理性,兴趣和工作还是分开的好。后来跟二妹两个在楼下捣鼓早餐车,跑到批发市场买了几大包银耳、杂粮,半夜起来熬银耳汤、小米粥,搭配白煮蛋、小菜,整得跟营养餐一样,可惜上班族们的早餐是顾不上营养的,他们宁愿抓着锅魁煎饼边吃边跑,少有人愿意坐下来慢慢喝粥。坚持了大概一个月,没赚到钱不说,还被城管赶过几次。她气愤地给我发短信说这些的时候我是又心疼又愧疚,只能跟她一起骂城管。她倒一会儿就没事儿了,问我要不要把没卖完的银耳寄些过来熬汤,“美容养颜哟!”
我比她大六岁,小时候还能罩着她点儿。大概我上初中的时候她进小学,有天中午回家吃饭时发现她手背上两条红红的印痕,问她,她不敢讲,一再逼问才说是被老师打的。我憋了一股怒气,等她慢慢吃完饭,我课也不上了,跟她一起去学校找老师。那时候老师们都在一间办公室,有的是曾经教过我的,她们大概也没想到一直听话乖巧的我哪来那么大的泼劲儿,把打人的老师数落得哑口无言,直到校长出来说软话,承认打人不对。从那以后她的班主任再也不敢打她,当然,估计那以后也不会好脸色对她。
后来她上高中,我已经离开家到外地打工。那段日子自己也过得不好,很少跟家里联系,偶尔回去看到她也是沉默的,不开心。她不是那种很会学习的学生,我知道那段时间她压力很大,但无能为力。她没有考上大学。来福州的时候,我曾经托朋友给她介绍在长乐机场航站楼上班,有次去看她,远远的,她那么小,穿着不合年龄的套装制服,站在熙熙攘攘的候机厅,身边都是拖着行李往家赶的旅人,真不知道她暗地里有没有想家哭鼻子。但朋友说起她,都夸她聪明机灵,很懂得待人处事。
因为机场离市区远,她只能趁周末休息的时候搭顺风车来看我,我们就一起买菜做饭,吃一顿好的。我知道食堂菜不合她胃口,就买来金针菇、大头菜,瘦肉末、豆干,切成丁和着辣酱一起炒,然后装到罐子里给她带着,美其名曰“下饭菜”,炒一罐大概也能凑合着吃好几天。那个时候我们都没钱,但仍然改不了臭美的毛病,常常去学生街或夜市淘便宜好看的衣服,回来对着镜子一件一件地试穿,互相夸赞,满足得不得了。她比我高一点,胖瘦差不多,我们俩的衣服就就可以换着穿,一件抵两件。
再后来她回到成都,与二妹住在一起,找到更好的工作,也遇到了疼爱她的人。我很为她开心。她从小就是家里最被疼爱的幺女儿,理应有人好好疼爱照顾她。
对于即将到来的婚姻,她既有过小女生的幻想和期望,又心怀恐惧,犹豫茫然。我没有办法为她找到一个最正确的答案,正像我自己也是糊里糊涂坠入婚姻一样。但有些事情只有试过才知道吧。
电影《牯岭街》里有个场景是让我记忆深刻。片中小四儿的爸妈有天晚上吵架,爸爸一气跑了出来,站在院子里不知该往哪里去。这时妈妈也出来,寻见爸爸,紧紧抱住他说:这个社会已经如此冷酷了,你不能再丢下我。大概是这样的。我想这也道出了一部分爱情的意义,就是相互陪伴共同取暖,不然人生真的是荒凉孤单。
其实生活本身是平淡庸常的,幻想或期待终究会破灭,但情感是真实的。今后她将学着和相爱的人在柴米油盐里相见,两个孩子一般的性格,一起磨合成长的过程一定会经历许多的磕磕绊绊,但我相信他们总会找到一种让彼此都温暖的相处方式。
我常常想起我小姨结婚的时候,姨父家的迎新队伍来了,敲锣打鼓地要把小姨接走,新娘子开始还高高兴兴,真要走的那一刻却抱着外婆大哭不撒手。我那时候很小,很难理解,这一天不是新娘子最开心幸福的日子吗?为什么小姨哭得如此伤心呢?大人说这是哭嫁,习俗如此。后来长大了慢慢懂得,这或许不光是一种习俗,更多的是情之所至——这女孩从今往后就要告别自己熟悉的家,离开疼爱她的家人,去和新的家人组合过日子了,这实在是件让人恐惧的事,所以,男人应该要尽全力好好保护她,疼惜她,给她至亲至好的爱,在她闭上眼睛往下跳时做她背后张开的降落伞,让她在落地的那一刻踏实安稳,不后悔这一生最冒险、最重要的决定。
放上张玮玮《宜宾的米店》,不知道为什么,听这首歌我老想起我即将出嫁的妹妹:“三月的烟雨 /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著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
总有些稻穗来不及收割
严姐嫁到我们村的时候才十六岁,很漂亮的一个小媳妇儿。
她性格开朗,跟谁都自来熟,哪里都可以见她大声叫嚷着玩笑、打闹,一副没心没肺的傻大姐样让她一来就成了女人堆里的焦点。
和村里所有闲在家的婆姨们一样,她也爱打麻将。可她输了也不恼,笑着骂两句“老娘今天‘狗火不旺,改天老娘再捞回来——”“狗火”就是牌运的意思吧,至今也没弄明白这二者之间有何联系。赢了钱转手就在小卖部买一大堆瓜子花生请大家吃。
她身上有股邪气,经常会干一些顺手牵羊的事情。
每年农历二月初一是我们老家“偷青”的节气,在这天夜里去别家菜地摘一两片青叶子,可以除去一年的病忧,被偷的人家不能追究,相反,而应该感到幸运。
她就趁着这天和几个媳妇儿背着背篓跑到人家菜地里去偷菜,偷回来满背篓的青菜萝卜——事实上在农村这也值不了几个钱,但就是觉得很好玩儿,半夜里几个人偷偷摸摸,忍住笑偷回来,还张扬谁的收获最丰。而这种时候往往是她最得意:青青的豌豆尖儿人家只是采最嫩的一点芽,而她则是毫不留情地连藤一起薅了往背篓里塞,当然是最狠最多啦。第二天她会偷偷把摘好的豌豆尖送一大篮到我们家,少不得又挨妈妈一顿骂,但她只是说笑着,叫我妈有的吃就吃别太认真。
不仅邪气,她的恶也是出了名的。因为要强的性格,她经常跟老公吵架打架,一打起来,全村人都扶老携幼地跑出来围观,跟看戏一样。后来村干部来调解,话说偏了,她连村干部一起骂,直到现在,提到小严,还是说,就是那个敢骂村长的恶婆娘。
但她显然不惧这些,因为,喜欢她的人照样喜欢,不喜欢她的人她也不在乎。
跟老公吵完架没地方去,她就经常跑到我家。妈妈那时候也是村里跟妇女主任一样,很多年轻的媳妇家里闹矛盾了就爱来找她哭诉,而妈妈也会耐心地安抚。严姐也是因此喜欢来家里串门。一来一往,跟我也要好起来。算起来,她也大不了我几岁,加上性格相投,自然跟她熟络起来,叫她严姐,她也把我当妹妹一般看待。
那时候农村还没有卫星电视,夏日的晚上很是无聊,我们在一起商量着搞点什么带劲儿的节目。我说很想去看电影,她就真的骑上二八的自行车带我直奔县城。记得那晚看的是《红粉》,王姬和王志文主演的一部很文艺的片子,可她居然像看喜剧一般从头笑到尾,笑得邻座一对情人盯着她看。我也不好意思起来,想告诉她,这电影讲的可是一场凄婉的爱情,可是又想想,凭什么你说是爱情就是爱情呢?凭什么爱情就不能笑呢?有多少貌似凄婉的爱情到头来不过一场荒唐的闹剧。
那些夏日的夜晚,跟着她到处跑经常被老爸骂。像她这样疯疯癫癫的女人在农村,尤其是老辈人眼里是很不相容的。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女人看她走过,总会在后面翻起白眼、撇下嘴巴。可是她无所谓,“反正老娘又不是活给你们看的”说完她也一撇嘴,大笑着走过。
我仍记得她穿那件翠绿的连身裙走过人堆时,掠起的那一片惊艳的目光。
她瓜子脸,鼻梁上几粒雀斑,反而衬出她皮肤的白嫩;眼睛不大,但笑起来弯弯的,很勾人,像早期的港星关咏荷,但比她野一点。我常常想起她搬个板凳坐在小院里,举着小圆镜修眉毛的样子,一根一根地拔去多余的眉毛,修得双眉又细又长,再仔细地涂上鲜红的唇膏,虽然看起来又土气又艳俗,却又有种毫不收敛的不知死活的美。那个时候她多年轻啊!
可她毕竟受不了和老公常年吵闹的日子,一气之下跟着打工的队伍去了广东,一去就是十几年。其间曾有传闻说她被老板包养,也有人说她当了小姐,但我从不相信。越是外表张扬的女人,内心往往对传统和世俗更多的顾忌。在我高中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里,一度想外出打工,曾经一个人跑去广东找过她,亲眼看到她的生活。她只是进了一家家具厂,凭着自己的勤快和泼辣当了一名车间组长。当然身边也不乏男人追求,但都被她拒绝。反而是一个年纪偏大的老实的贵州男人在她身边照顾了好几年,可惜最终没能给她一个安稳的家——在外漂泊的打工者就是一片片散落荒野的飘萍,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仅此而已。
在那边过完暑假,我还是老老实实回到学校。跟她偶尔电话联系。隔一年半载,她会打电话来聊一聊她跟那个贵州男人之间时断时续的感情,她开始怨天尤人,也开始诅咒命运,一到这种时候,我都不得不嗯嗯啊啊地敷衍,然后借口有事,匆匆挂掉电话。
最近一次见她,是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回老家探亲,而她也刚好从广东回来,听说是为了买房的事情。算起来她已经四十好几,的确苍老了好多,已经不太注重自己的外貌了——唯一为她高兴的事,是漂泊这么多年,到底有了一套房,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哪怕这个家只有一个人。
刚好在她家闲聊的时候,听她接电话,是一家婚介公司给他介绍的一个男人,要她去看看,似乎对方条件还不错。她表面上不愿理会母亲的担忧和催促,但看得出来,心里还是有些着急切和期待的。她佯装不情愿地答应去看看。我赶紧拿出化妆盒,帮她简单地打理一番。她对着镜子看看,有点兴奋转而又有点心酸,叹一声:“老了!”
似乎是为了给自己一些勇气,她要我们一同去,帮她过过眼。
在公园角落的一条长椅上,坐着两个男人。一个是婚介的,另一个嘴里叼着烟,衬衣松松地一角扎进皮带,一角翻出来耷拉着,胡碴满脸,满口黄牙,正拿睥倪的眼光打量我们。我耐着性子和严姐坐到一边,看两个男人像挑选商品一般看我们一眼,又交头接耳一番,从头至尾没有和我们打一个招呼,过了一会儿竟站起来扬长而去。什么鸟男人!我在心里骂道。可是看看严姐,她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等待那婚介所的男人告诉她此行的命运。听说那个男人自己开了个茶馆,我想她是有点动心。她问我,我不知道该给她怎样的意见,是勉强找个人过日子还是继续一个人漂泊。
她最终还是没有留在老家,在我离开后的第二天,她又踏上了开往广东的列车。她来电话说她现在升为课长了,上月天天加班,工资拿了六千多。然后说在厂里认识了一个四川老乡,对她挺好……我听着听着,又想起她坐在流水线上,一边干活一边跟着手机里的音乐唱歌的样子,那些歌声啊,听起来又美丽又忧伤。
责任编辑 贾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