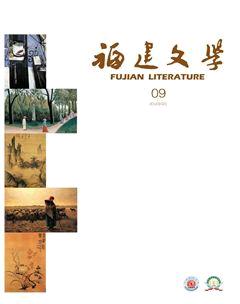笔记小品五题
詹昌政
追 蜂
秋风起,蜂蛹肥,斗蜂的时节又到了。
蜂是野生的,带着一枚剧毒的尾针,飞来飞去,就像一架高性能的战斗机,原本是奈何它不得的。但是,正如大侠也有他的弱点,再凶悍的野蜂也得回巢——不像蜗牛,背着安乐窝行走江湖。于是,野蜂的危险来临了。
对蜂而言,巢是温暖的,也是致命的。
换句话说,巢里的蛹——还没出生的蜂子,将会因自己的肥美而害死族类。当然,蛹是无辜的。甚至可以说,是族类的不慎引来了灭巢之祸。
以天下之大,原本是藏得住一个蜂巢的。但是,千万只野蜂四处乱飞,可就难保不泄密了。乡人轻易就能捉住一只蜂——这是微不足道的收获,因为不能像杀一只鸟那样取肉,也不能像逮了一只小松鼠,让它陪人玩耍,相反,稍不留神就会被蜇,乃至有性命之虞。只是,人与蜂习俗有别,语言不同,要想获得蜂巢情报,靠哄、诱、吓是无效的,即使刑、逼、供定然也不肯招。
不过,乡人自有妙计:取一丝细线,系在蜂身,线的末端系一小纸片,然后放飞。反特片中,管这叫“放长线钓大鱼”。蜂一获释,急忙飞去,虽然觉得不对劲,但因智力悬殊,一时破不了人类的计谋,就气冲冲地回巢请诸葛亮开会,这就把灾难引来了——那个满脸笑意的乡人已尾随而至了。当然,也有个别野蜂,毕竟去过书房、教室附近,悟得些许反侦察的技法,飞来飞去,就是不往蜂巢里飞。直到有一天,那个乡人挟起一筷子肥蛹,恨恨地咬了一口,说:害得我追了几天才追到,哼!
追到了,或撞见蜂巢,乡人不急。他会在附近的树枝上系一布条,一来做记号,二来告诉后来者:我先找到了。
巢有两种:挂在高枝,隐于地洞。这都难不了乡民。他们约了伙伴,不时吞咽着口水,熬到天黑就去夺巢——做爱与作恶,都喜欢摸黑干,说明人类还有羞耻之心。不过,在他们看来,那巢已是囊中之物了。
和所有的强盗一样,他们先放火,以烟熏巢,众蜂受惊,纷纷追烟而去。这时,乡人猴子一样爬上树,将结在枝间的巨巢捅了又捅,直到捅落,掉入树下早已张开的大嘴似的布袋。对付地洞里的土蜂,他们故伎重演:放火、烟熏。不同的是,这回用上了锄头,将一窝蜂连巢带土刨进了麻布袋,扎紧,扛了就走。
剩下的细节就不堪描述了。据说,先用热气把袋子里的活蜂熏蒸致死,捡出,泡酒;再将巢中之蛹也一一挑出,是炸,是炒,任由处置了……
意外的消息也是有的:某夜斗蜂,某人受蜇,尿屎失禁;某人终因被蜇多针,死了。
天高云淡,好个秋啊,候鸟开始南飞了。所有会飞又会招惹人类食欲的,请把你们的巢全都迁往云里去吧!
撰 栗
走过农贸市场,见农家女摆摊卖板栗,忍不住拈起一粒,看看,嗅嗅,似乎家乡的气息隐约可闻。啊哈,秋了,栗子熟了。
板栗,球状,外长“猬毛”,扎人手脚,剥去,内有三粒栗实——两粒各如半球,偏在中间插入了一粒扁形的,叫作栗楔,据说能治血理筋骨风痛。古人惊呼:“缜密啊!”将栗的防身术视为智的典范,有《礼记·聘义》为证:“缜密以栗,知也。”
更奇的是采栗。古人说,“八月剥枣”,“八月栗零”。剥,就是扑击;零,即为掉落。枣熟了要用竹竿去打,而栗熟了会自己掉落,满地刺球,提蓝捡取而已。农家女说,她是用竹竿打下栗子的,我不禁一笑:太急了。
急什么呢?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然而有报道说,许多孕妇赶在9月1日之前生产,剖腹赶早产出,不然,孩子入学将推迟一年。这样的速生、催产,在果蔬种植中尤为常见,美其名曰“反季节”。违反自然规律的,除了满足口腹之欲,不见得会有什么好结果。这不,都市流行乡土味了,返璞归真是正道。
板栗个个饱满,蒸食须先剪个小口子,农家女乐为代劳。只见她以钳铰栗,拈取,铰罢,一气呵成。末了,她抛弃一粒,又补入一粒,说:枯了,不实,剪了才知道。这与栗的别名相符:《礼记·内则》说,“栗曰撰之”,撰,意为选择——栗子容易长虫,是一种需要挑选的果子。
我不禁蹲在了栗子摊前。虽然无法选择天下走势,但挑拣一两粒实打实的栗子,还是有闲空的。我不急。
插 蛏
对于山里人来说,通往海边的一条大路就像一根强有力的缰绳,刷的一声,就把大海拽了过来。哗啦啦,生猛的海鲜倒进了山沟沟的粗瓷大碗里。
这些海味中,必有竹蛏。
闽中旧习,婚嫁上桌的要有目鱼、蛏干,不然就算不得请客。早年闭塞,所有的海味都是晒过了的,吃得最多的是盐。从供销社买了带鱼,闻起来臭臭的,细看倒还不曾腐烂,没有冰箱的年代,盐巴充当了最好的保鲜剂。清蒸或油炸,山里人是舍不得细细清洗带鱼的,洗掉了盐和腥味,不就等于多花了钱?当时,紫菜不多见,过年了,外出工作的人寄回一小袋,嘱说用于煮汤,老阿婆就把它全扔进了锅,望着一团紫色的滚涌,竟然不知所措。而吃蛏干就有经验了,就像穷人花钱,懂得精打细算:蛏不多,汤管够,不就尝个鲜吗?
不过,山区只有今人吃的蛏,才够得上“鲜”字。店摊摆卖的海鲜,仅贝壳类就有十几种,去海鲜城点菜,许多海产品是叫不出名的,连厨师都得与客人商讨烹饪之法。我时常盯着竹蛏看:真怪啊,两片细长的薄壳竟然包不住蛏肉,蛏的脚和头总要探出两端,就像肉还在长,壳子来不及更换。
我没在海边生活过,怎么也想不出竹蛏是怎么游动或爬行的。友人告诉我,蛏是直立生活的,插在浅海的滩涂与泥沙为伍,潮来了,它探出泥外的竹节模样,有如玉树临风。要是遇到了险情,它会身子一顿,悄无声息地沉潜入泥。想象一下吧:修长的竹蛏敏如按钮,一触,就深水炸弹似的垂直向下,向下。哦,望不到边的海洋是何其的苍茫啊,一个小生命的惊心一刻,注定淹没在了汹涌的波涛之下。当然,再大的潮水也有退去的时候,浅滩裸露,就会引来成群捡小海的钩子。此时,竹蛏就像田里失去了水的泥鳅,气孔泄露了自己的行踪。据说,往沙孔里倒些盐水,蛏就嗖地跳了出来。它是以为海潮回来了,还是气不过人类的戏弄?——蛏的脾气跟它的长相一样直。
关于钩蛏的技法,友人是教过的,但我不说——总不能害了蛏们吧?
山里人说,田螺可怜啊:没有脚,逃不了,一个被捉,壳里那么多的螺子也跟着死了。所以,寺院的放生名单里总有田螺。蛏呢?可就悲壮了。你看吧,清蒸上桌的蛏却是直立活着的样子:一个个竖着,密密地插在窄口的深碗里。人类的生活中,比如,集会、挤车、抢购、逃命……类似的挤成一团的扎堆景象,不也常见?听听,这是谁在呼救——
“挤死掉啦!”此时,抱怨者往往加了一句,“怎么跟插蛏一样啊!”
悯 鳅
江南的水田里,常见泥鳅。青黑色的手指模样,是极滑溜也是极滑稽的家伙:嘴小而尖,竟然有须,既为水生动物,却偏喜欢钻入泥里。当秋水浅去,泥田可以行鞋,它的踪迹就因钻洞而暴露无遗了。少年用一指循洞而掘了下去,便可找到泥鳅:蜷在泥洞,以沫濡身,以期过冬。然而,纵然躲过了手追,也难逃锄截:农民冬翻水田,一锄掘起,鳅便落入那人腰间的竹篓里。更何况,春耕时田泥翻卷,夏夜里松明火和渔叉指指点点,以及油茶饼水的毒杀,无不直取长不及箸的泥鳅性命!
泥鳅,真乃弱者,一生如同悲情的哑剧。
然而,泥鳅另有一个名字:鰌!此名一出,非同小可了!民间传说:鰌,就是海鳅,是龙王的外孙,东海的水族皇帝。而且,长相也不再那么委琐了,明人顾岕的《海槎余录》说:“海鳅乃水族之极大而变异不测者。”大到什么程度呢?《水经》说:“海鰌鱼,长数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则海水为潮,出穴则潮退。”当真是巨无霸,简直堪比鲲鹏了。
帅到这地步,崇拜者就多了。古人把渔船头雕成尖嘴的巨鳅之首,索性命名为“海鰌船”,以此壮胆、吓唬大海。问题是,真有海鳅吗?嘉靖年间的顾岕详述了他的海南见闻:
“梧川山界有海湾,上下五百里,横截海面,且极其深。当二月之交,海鳅来此生育,隐隐轻云覆其上,人感知其有在也。俟风曰晴暖,则有小海鳅浮水面,眼未启,身赤色,随波荡漾而来。土人用舴艋装载藤丝索为臂,大者每三人守一茎,其杪分赘逆须枪头二三支于其上。溯流而往,遇则并举枪中其身,纵索任其去向,稍定时,复似前法施射一二次毕,则棹船并岸,创置沙滩,徐徐收索。此物初生,眼合无所见,且忍创疼,轻样随波而至,渐登浅处,潮落搁置沙滩,不能动。举家分脔其肉,作煎油用亦大矣哉!”
至此,我相信,顾老先生说的是捕鲸的场景。而且,传说中的海鳅,极有可能就是鲸。
哦,烂泥田里屡被追杀的小鱼鳅,竟然会是纵横海疆的鲸鱼!但也许,鲸(鰌)是鳅之梦?若你俯看失落在水缸里的小鳅,想想海鲸,或许就不至于轻易嘲笑了吧?烈士暮年,是血酒一样悲壮的,几人堪配举杯呢!
飞 鸟
在我记忆的天空中,一直盘旋着一群鸟:成千上万,遮天蔽日,突然呼啸而过,没了踪影。
我说的是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怪异。当天上午10时许,“有海鸟数万,成群飞经县治而去”。从何而来?飞往何去?形状?啼鸣?习性?一无所知,但这一点也不妨碍闽中《大田县志》的断定:那是海鸟!
时已冬季,候鸟南飞。这群鸟反而从东南边的海上来吗?抑或是飞回海外去呢?数万只群飞造成的鸟浪波动,至今不息!
近百年后,又一群鸟从闽西北的天空飞过。民国版《清流县志》记下了这一壮观:1941年十二月初六日,“有水凫数万自东北飞向西南,蔽空而过”。哦,又是数万成群!是从哪里飞来?要往哪里飞去,飞向海外?凭什么断定是水鸟?它们飞过时是否栖落?吃什么?是否被人吃了?这些行色匆匆的天上来客,操着山民所不识的鸟语,是何其陌生的一群啊,突然闯了进来,又倏忽飘然而去,让人觉得受到奔袭,却又不觉得威胁。难道它们是上天派来的友好使者?一年一度巡视南北,警告人类好自为之!
候鸟过境,年年都会发生。候鸟是守信的,当然,不为人类,而因生存。它们呼朋唤友大迁徙,庞大的鸟群飞过城郭的上空,引得万众仰望。这种鸟事,无关生计,不干政治,飞过也就不见了,无非传说一时而已。直到有一天,蓦然惊觉天上不再有鸟飞过,这才惶惑,探头探脑,寻寻觅觅,在某一本古旧的县志某一行,撞见零碎的字句:万鸟,蔽空而过——不由得怅然久之了。
应当感谢让鸟事入志的人。他的好奇心是一座青山,让后人有柴烧,有水喝,有景赏玩。他明白:一部县志,代代相传,其实是代代删削!多少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物,被下一代人的笔尖轻轻抹去了;多少刻成碑复又收入志里的纪功之作,简缩成了后人的一句讥讽;多少豪杰、志士、权贵、名流、奇才、逸客的一生风化了,能在地方志里大浪淘沙,留下形状各异的名字,补在纪念碑底座或耻辱墙的一角,都属强悍。至于众生,安放在广大的时空之下,岁岁枯荣,无非是祖传的草民而已。然而,群鸟飞过,虽只一时,却在志书里筑下了小巢故居!它们的翔姿逃过了一代又一代修志者投枪似的目光,让后人仰视、讶叹。
有个可笑的念头,不妨记在文末——每当鸟叫,我总不由一惊,悄然环顾,暗想:小心了,鸟是入了志的,它可不亚于圣人!
责任编辑 贾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