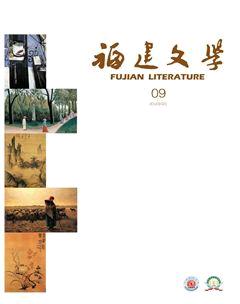老友张毓茂的人和文
一年前,我出散文集,请毓茂写了序,此番他出散文集,要我写序,也不怕人家背后嘲笑,一搭一档,互相吹捧。我想,干什么也得有个资格,要捧张毓茂,一般人恐怕还不大够格。
第一,在青年时代,尤其是,反右那一场惊心动魄的经历中,我们是难兄难弟,都是“差一口气”的角色。
第二,他谈恋爱那阵子,我荣任首席顾问,一大车子私房话,多少绝密的策略,至今还不想免费奉献给后现代青年参考。恐怕要学世界级的大作家,写成回忆录,藏诸名山,等到一百年后,由我们孙子的孙子,联合拍卖给研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恋爱史的博士,说不定发笔小财。
第三,论了解之深,在这世界上,我是世界第二(世界第一让给他太太比较妥当,免得产生无谓的争论)。
第四,除了他太太和我,还有谁敢臭他,指出他文章中的不足?在这方面,我暂居世界亚军。
写到这里,想起来,我骂过他,本来,是只给他一个人听的,可却被他综合在给我写的《序》中,大公无私地让天下读者共享了,原文如下:
他(按:指鄙人)不止一次地在口头上和书信里斥责我,说我在‘自我扼杀,说‘你的文章不像你写的,你被自我被流行的套子窒息了。你的文章不如你这个人生动……甚至不惜用粗话骂我:‘你怕什么?怕谁咬了你的x x!我得承认,他骂得有点道理。
凭良心说,骂人是我的一大业余爱好。最佳境界是:事前没有任何准备,全凭即兴、灵感,大笔写意,淋漓泼墨,天马行空,风行水上,云收海隅,雨乱珠帘。潇洒飘逸,汪洋恣肆,我有篇文章,叫做《潇洒骂一回》,写我骂人骂过瘾了,就非常幸福地睡去,不到屁股上有阳光金色的手指在抚摸,绝对不知东方之既白;起床以后,仍然非常潇洒地,兴致勃勃地,过着同样浑浑噩噩的日子。
我骂他一次,能幸福一晚上,一想到能把他的思想搅乱,就乐不可支。不过,坏事能变成好事,我刺激他动了一点脑筋,他的散文大放光彩。其最佳成果就是他给我写的《序》。所有读我那本散文集《灵魂的喜剧》的熟人都对我说,你那本书整个儿加起来,还赶不上人家那篇《序》。
妙哉!快哉!美哉!
不但我那本书里,最有才气的他的那篇序,而且在他这本散文集中,最妙的也就是那篇《序》(请看官注意:在本书中,文章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如是说孙绍振》)。
自从我有了一点小名气,写我的文章不少,大都是我的学生和读者写的。他们不知是真是假,都用一种仰视的目光来看我,把我写得很有点了不起,有的还给我来一圈光环。只有毓茂知道我的底细,他用中国史家传统的实录的笔法,把当年的我写活了,不但天真、幼稚,而且脆弱、卑微,顶不住压力,还把他给供了出来,弄得两个人狼狈不堪。和我学生们写的比起来,在他笔下,我的形象真是有点寒碜,可是那就是历史。人是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历史的,更不能欺骗自己。
有了他这篇序,我第一次找到了骂人骂出好结果的例子。
我对于自己骂人的水平,颇为自负;特别讲究灵感,(虽然常常被他形容为“一团乱草”。)行文随意性很大,兴之所至,什么句子先涌到笔下,就先写下来再说,不管他好话坏话,图个痛快,等到思路理顺了,更严密的句子姗姗来迟,可是篇幅已经差不多了,也就掷笔而起,拉蛋倒了。
他和我不同,思想比较缜密,深刻,但是不如我浪漫,我那股疯劲,他很是羡慕,可是,他就是不想学习。而我倒是不断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有些东西学不到,就做梦也羡慕。
我除了羡慕他的沉着、深邃以外,还羡慕他头发比我多,但不羡慕他后脑勺上那“地中海”,不过我们两个都由于这不可改革的地中海,被人称为“聪明绝顶”。
兴许是为了再引来我一次高水平的痛骂,在把本书清样寄给我的时候,在前面用相当工整的笔触(不亚于他当年写情书),写了几句话:“请您写序,要快!把别的活儿,先放下。 我这许多所谓文章,其实狗屁而已。然而尽管满嘴鼻涕,到底是自己的崽儿,敝帚自珍,未能免俗也!”
他这么一说,我却不想骂他,说正经的,谦虚谨慎,并不一定能使人进步。
我反复诵读他在标题上打钩的文章,绝对不同意他的说法,相反,越读还越觉得余香满口,不由得不佩服起来,忍不住要讲讲正经话:
我说的主要是两类文章。第一类是写他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师友的。笔锋如梁启超,常带感情,这种感情很可珍贵,不但是真情,而且是多年的积累,这是生命超重内涵,连模仿也困难的。他的老师公眉先生,在他笔下尤为感人。除了师德感人,更令人感佩的是落难之时的恬淡,把老师养在家里的农民同学,也令人感动,感动得我都有点惭愧了。我想起自己虽然从九十年代每年给我中学语文教师寄五百大洋(本世纪增加到一千)书报费,还寄过一笔钱让他去把牙齿全部重新装过,比起那个同学来说,就小气得多了。
写温小钰的那一篇,当然也属上品。但是为什么用来做开头第一篇,就有点令人莫名其妙。论文章质量,似乎不如写我那篇,论个人关系,温小钰算老几啊,几曾和他共过患难?除了是个女流以外,有什么理由猴在这本散文集的第一篇。莫不是他当了市长以后,步猪八戒的后尘,去西方极乐世界访问若干次,在洋人那儿取到了lady first的真经?
在写师友的时候,往往有动人的情怀,但是他不善于抒情,他的气质和我不同,他深沉,诗于他是不适合的。他不是用抒情诗的笔调,而是用一种叙述的风格,写出了自己生命的记忆,常常有异常的情趣。在《人格的魅力——怀念吕公眉先生》中,他写到老师正直孤高,对于一些阿谀逢迎之徒,极其蔑视:
记得有一回,学校搞春季卫生周,我们几个学生帮助老师打扫办公室。工作完毕,空气新鲜,窗明几净,阳光灿烂……几个老师在议论一个“进步分子”的卑劣行径,征询先生的看法。先生仰起头,冷冷地说了句:“干干净净的屋子,不说这种人,太脏。”
这几句话,潜在量却很大,不但可以想见这位吕先生的为人,而且可以感到毓茂日后愤世嫉俗的语言风格的萌芽。
他也并不是永远那么愤世嫉俗,他往往也追求一种随意自如的风格,他自称“胡扯”。他并没有刻意表现自己的个性,但是他个性中的谐趣却往往在不经意中表现了出来。
他写大学时和一个姓邓的同学,共同办一个手抄的墙报《小火星》。这位姓邓的同学说:普希金年轻时也办过墙报。接下去,他说,到毕业的时候,这位“姓邓普希金”被分配到大西北去了。每说到他自己的时候,也常用这种颇有调侃的笔法,随意间流露出一种幽默。我在《北大读书》中,曾经说到他建议我读弗洛伊德、柏格森,因为这些书离开北大就很难借到了。他在文章中纠正说,其实,他当时着迷的并不是弗洛伊德、柏格森之类,而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可是后来分配工作时,却干了别的,“什么‘斯基也不是”。
每每在这样的语气中,轻而易举地显出张毓茂式的自在和自如的性灵。这里有他为文时并不经常流露出来的自嘲和自慰。很可惜,他的身份不给他充分的自由。在许多场合下,他不能像我一样任性,不怕人咬掉什么部位。他在写一些怀念领导岗位上的同事的时候,他就不能不严肃起来。这样文章,比起他写自己的生命的回忆,在深度上和分量上就弱一些。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文章中,有时也还闪耀着他性灵的光彩。他写沈阳市市长接待萧乾,很有点出格。学理工的出身,也学过一点点文学,就在萧乾面前大谈起意识流、后现代来。毓茂好生着急。而萧乾对市长明显离谱的言谈,很是宽厚地笑笑。说,难得有你这好见解。或者说,这个问题,我不熟悉。接下去他这样写:
这情景使我联想起鲁迅对其爱子的海婴的态度。海婴上小学认识了一些字以后,兴高采烈地对鲁迅说,爸爸,我认识了好多字,以后,你写文章有不懂的字,就来问我。鲁迅宽厚地笑了,说好的,好的,我一定问你。
我把这想法后来告诉了迪生(按:市长)他哈哈大笑,拍了我一掌,说:“你这家伙总是这么刻薄。你看萧老人家多宽厚。
他比我们这些人深刻,他常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难得的是没有居高临下的感觉。这一笔的好处是,不但写出了当时当地的情景,而且写出了朋友之间,那种难得的心灵不设防。只有心灵真正沟通,才能这样开怀地说他“刻薄”。
当然,要说在写师友的文章中,写得这么好的,在他的集子里,并不是多数。
这里头有个讲究。
写师友的,大都是一些抒情文章,可是,他从气质上讲,缺乏抒情的基因,如果从我钻研的“创作论”来看,他长处在于平静地叙事,他的冷峻使他与诗意的抒情格格不入。
如果光是凭他这抒写师友之情的文章,是不够出一本集子的。
当然十个指头不一般齐,我忍不住要评头论足,他这本集子里,写得最好的文章,并不是抒情的,而是另外一类,叙事的文章。就从上面举的沈阳市长的例子来看,虽然是写友情的,但是最为传神的,却是叙事的细节。
他的这种叙事的工夫,在写到他最为热爱的萧军和他周围的人事关系的时候,就大放光彩了。他往往能用极少的对话或者动作把历史氛围和当事人的气质和个性表达得淋漓尽致。他写到萧军在1948年挨批判的时候,是这样的:
东北局宣传部负责人刘芝明是批萧军的挂帅人物,为了写那篇批判萧军的长文,需要萧军过去的作品当靶子,萧军便主动提供。刘把文章给萧军看,问:“觉得怎么样?”萧摇头笑了,说:“不怎么样!”“为什么?”萧军轻松坦率地告诉刘芝明:“若是我批判萧军,就不这么写。你把萧军比作狼、虫、虎、豹,还有什么老鹰狮子等凶兽,但凶兽毕竟不是巴儿狗!你不记得吧,鲁迅说过,自己的血肉宁愿喂鹰喂虎,也不给巴儿狗吃。养肥了癞皮狗乱钻乱叫,可有多么讨厌!”
刘芝明当然非常生气。此后批判萧军的声势越来越大。萧军却对刘芝明挑战说:
“你要能批得我少吃一碗饭,少睡一个钟头觉,我都佩服你!”
刘说:“你和共产党耍什么硬骨头!”
萧反问:“共产党净需要软骨头吗?”
张毓茂的冷峻的气质就在这种没有任何形容和渲染的叙述中显示出来。
也许,他并没有刻意要刻画萧军的形象,只是本着实录的精神,把历史的真相记载下来,但是他的叙述,是这样干净,三言两语,就把萧军作为一个作家却富有绿林气的特点表现得如此鲜明。除此之外,还显示了建国初期,比较宽松的文化氛围,是很有历史特点的。在抒情上不见什么工夫的张毓茂,在叙事上,尤其是在写到他所最为热爱的萧军的男子汉气概的时候,给人的印象常常是妙笔生花。如写他早年当兵,为了打抱不平,要把队长劈死,在上海,他悼念鲁迅的方式,受到了一个文人的嘲弄,他把这个家伙(张春桥一个小兄弟),狠狠揍了一顿。尤为精彩的是,写萧军1938年,第一次到延安:
毛泽东听说萧军到了延安。就派秘书邀请萧军见面,萧军却以不便打扰为由辞谢了。想不到第二天毛泽东却亲自登门拜访,并在招待所宴请了萧军……在延安逗留期间,萧军曾应邀参加了不少活动,不止一次见到毛泽东。如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的会场上,毛泽东看见萧军时,就把他介绍给在场的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同志,拉着萧军一起在操场上会餐。
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轮流共喝一个大碗里的酒,开怀畅饮,高谈阔论,放声大笑。那种“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壮观的场面,非常投合萧军的脾气。
张毓茂的功夫就在于完全凭借于叙述,而不事任何渲染、感叹、形容,不用夸张和描写,就把一种精神氛围给再现了出来。这种人与人之间心领神会的精神交流,是很有历史特点的。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政治文化生活,已经有了许多电影和回忆,但是达到这样深度的历史传神的篇章还不多见。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历史氛围的再现不是静态的,而是和文化人物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就显得不但有历史文献价值,而且有艺术的审美价值。
这一点最为显著地表现在萧军和王实味的关系上。王实味和萧军本来没有什么关系。王实味遭到批判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请萧军,以他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为王实味说情。萧军根本不了解批判王实味的复杂缘由,“自恃与毛泽东有友情,便轻率地承担了说情的使命。毛泽东听了萧军的倾述后,是很不高兴的,但却宽厚原谅了萧军的鲁莽。毛泽东告诉萧军,王实味的问题很复杂,不但犯了政治错误,还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问题,要萧军不要管自己管不了的事情。萧军碰了个软钉子,但他一向粗心,以为不要管就不要管吧,也没有多想。可是,萧军找毛泽东给王实味求情的传闻,很快不胫而走,引起一些同志的误解和强烈不满”。
六月初的一天,萧军随“文抗”的同志们到王实味在的中央研究院参加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会场比较乱。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军坐在会场的后边,根本无法听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
“喂……让他(指王实味)说吗,为什么不让他说话!”会场上人们的目光,从四面八方,一时间集中到萧军身上,萧军也毫不在乎。
这样的场面,不但对于学习和研究现代文学史,而且对于学习中国现代思想史都是不可多得的史料,这种史料的好处,还在于它是活生生的,而不像一般史料,那样带故纸堆的气息,缺乏历史的生命的律动。
以后萧军和周围的人冲突步步升级,他还把自己认为的事实真相,写了个《备忘录》给毛泽东。过去他给毛写信总是马上就有回信。这一次毛泽东却置之不理,萧军还是不清醒,继续为王实味向毛泽东转信。毛泽东仍然不予置理。萧军却锋芒不减,顶风而上。在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的大会上,他突然宣读了他的《备忘录》。
这一下子像滚油锅里倒进一桶冷水,立即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丁玲、周扬、陈学昭等党内外七名作家轮番上阵。萧军孤身一人,舌战群儒,毫不怯阵,越战越勇。整个两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无一人退席,都想看个究竟。从晚上八点一直轮战到深夜两点……
后来吴玉章说了几句安抚的话,萧军压下了怒气:
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考虑一下你们的百分之一……
这时丁玲却盛气凌人地说:
我们一点也没有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
萧军刚平息下去的怒气,立即爆发了。他腾地起来,拍案大怒,说:“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你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个‘毛。从今后,咱们就他她妈的,拉,蛋,倒!”
萧军那种绿林气,他对政治的无知,他的纯洁和天真,他品格上的高尚和政治上的愚蠢,在张毓茂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萧军不像胡风,他是一个独行侠,他没有一帮子哥们兄弟,他也没有任何理论指导,他完全凭着个人的直觉和民间的正义感。他的可爱、他的幼稚,张毓茂几乎是毫不费劲地表现了出来。但是我知道,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为了把这样的历史氛围化为他自己的生命的体验,他耗费了多少生命,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他就对萧军有了兴趣,大学一年级,那是1955年,我们俩就私下议论,胡风根本不是反革命。到了五七年春天,他以老乡的身份私访萧军,他告诉我,问起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萧军那时处境已经很严峻,只是笑笑说“历史会作出回答”。他笔下的萧军,明眼的读者可以感觉得到,岂但是萧军,其中又何尝没有他自己对于人际关系的期待,人身自由的向往。
对于萧军和他周围的文化人物的表现,无疑是集子中最为精彩的篇章。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并没有把关于萧军的一辑,放在最前面,而把抒情味比较重的一组放到了最显著的位置上。这也许是,他总以为散文总应该有一点抒情罢。可是他又对于自己的抒情总有些不满,因而就有开头所引的那段对于自己相当苛刻的话。
其实,他的这些散文才可以列入真正的散文之列。
不但他的抒情篇章,不如这类散文远甚,就是他放在下面的几辑,以议论为主的散文,比之这一辑,在艺术上显得逊色。这种逊色,是和张毓茂自己比的,不仅是和他最好的散文比,而且是和他自己的个性比。他是一个相当富有谐趣的人,大学时代,他和我谈笑,往往有东北歇后语,如形容某同学做事有条理:光屁股坐板凳——有板有眼的。又如,说到班上同学有谈恋爱的苗头了,就说是:乌龟看绿豆——对上眼啦。在一般怀旧的文章中,他有时还能把他的谐趣流露出来,到了一本正经发议论的时候,他动人的幽默,尤其是他那赵本山式的民间谐趣,就不翼而飞了。我时常有一种设想,如果张毓茂把他日常谈吐中的幽默和诙谐,表现出来一点点,哪怕像萧军所说的百分之一罢,他的散文,他的议论就可以让一些追求幽默的散文家望尘莫及了。
责任编辑 贾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