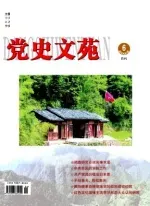书生领袖陈独秀与蒋介石的博弈
■张家康
陈独秀以其号角性的文章,集聚起一批知识界的精英分子,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共早期党首,实乃一介书生领袖;蒋介石早年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后由黄埔军校起家,以北伐胜利居功,进而掌握党政军大权。这样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竟被时势的惊涛骇浪推至历史的前台,作为代表各自政党和阶级利益的领导者,在云谲波诡的大革命舞台博弈。
陈陈独独秀秀::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
1923年4月,陈独秀因事来到孙中山的大元帅府,谈话间,传来刘震寰因未讨得军饷而将会计主任拘押的消息。孙中山大怒,立即将大本营参谋长蒋介石召来,让严惩此等不法军人,可这也只能是说说而已。正如陈独秀所说: “其实当时所谓孙大元帅、蒋总参谋长都是赤手空拳,此事终于隐忍而去。”这可能是陈独秀第一次与蒋介石相见。
孙中山有鉴于此,才下定决心要创办黄埔军校,以建立一支忠诚于国民革命的军队。1923年5月,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 (即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0月,蒋介石又受孙中山命,率领黄埔学生军迅速平定广州陈廉伯的商团叛乱。孙中山建立一支党军的愿望,正在成为事实。
1925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东征,蒋介石为东征军总司令,汪精卫为党代表,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剑锋直指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陈独秀于10月12日在《向导》发表文章说:
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得失地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为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中山先生及他手创的中国国民党,倘若没有这几个月国民政府一面肃清内部恶势力,一面反扑外部恶势力的坚决举动,几乎使人民怀疑什么三民主义、什么革命事业,都不过是欺骗人民的鬼话了!
蒋介石在受孙中山之命考察苏联时,就对苏联红军极感兴趣。据陪同的苏军将领回忆,蒋介石当着许多苏联红军指战员的面,“说了许多夸奖和感到惊讶的话”,称苏联红军“是世界上一支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他随后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的色彩就更呈“赤色”,说什么“我们的国民革命将具有国际性质”,中国国民党倡导的民主主义经济制度 “也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
蒋介石在筹办黄埔军校时,几乎都是承袭苏联的模式,其中最突出的是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他认为党代表是 “救济中国军校的唯一的制度”。他很看重苏联的援助和共产党的帮助,黄埔军校在此二者的倾力下,才建成和发展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单位。平定商团叛乱和东征讨伐陈炯明,使人们对黄埔学生军刮目相看,蒋介石的地位也因此节节攀升。
在国民革命的名义下,蒋介石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借助苏联和中共的帮助,在个人通向权力之巅的路上,迈出了最初的扎实步伐。他对此充满感激之情,时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们所要仿效的,是俄国的革命党”。“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在全力推行政治部和党代表制时,他限定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担任。
这一切使新老军阀视蒋介石为敌人,帝国主义列强也把他看做“赤军”领袖。而更令蒋介石气恼的是,党内的许多人也对他不满。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对国民党的 “左派”领袖尽力进行维护,陈独秀多次在 《向导》上发表文章,痛斥来自方方面面的攻击,他说: “国民党中又有一班新的右派分子,口头上自称是中山先生的信徒,实际上对于真能为中山主义在广州奋斗的左派,不但心憎腹诽,并且公然致函蒋介石阻其急进”。他批评国民党新老右派对“左派领袖汪精卫、蒋介石的攻击,竟无所不用其极,不惜罗织许多罪名,假造许多谣言”。
此时,共产国际对蒋介石也甚为瞩目。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说: “有40万党员的国民党,历史的 ‘明天’将使它在全中国掌权。而它却在思想上表示赞同我们,这已经是巨大的成就了。”为此,共产国际把筹砝押在国民党一边,并专门作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其中就说: “广州政府乃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先锋队,成了未来的国内革命民主建设的典范。”这次会议还批准国民党以 “同情党”的名义参加共产国际,蒋介石还进入共产国际主席团,成为名誉委员。
国民党一大前后,蒋介石确实赞成并维护联俄、联共,但这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的正统和核心,三民主义乃是唯一的理论基础。这些是他安身立命、施展抱负的基础。尽管国民党一大上,他在国民党的地位不如跨党的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和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可是,从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他作为专职的军事委员起,就明白枪杆子的重要性,终其一生都不忘整军经武,牢牢把握手中的枪杆子。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中央成立了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自此他跻身政治中枢。
蒋蒋介介石石::不要长篇大论的打起笔墨官司来
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随后又被国民政府特任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他距权力之巅仅一步之遥,可这短短的路途上却横亘着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一个是共产党,另一个是汪精卫。在经过一番精心的策划后,他一手制造了 “中山舰事件”,吓跑了汪精卫,也敲山震虎,给苏联顾问和中共以威慑。
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自知目前还离不开苏联和中共的帮助。所以,他一方面向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代表说,此次事件 “对人不对俄”,并希望国民党的苏俄顾问鲍罗廷尽快回来。另一方面,他说罪在李之龙, “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暗示他不是针对中共。可是事件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公开了身份的250名共产党员不得不退出国民革命军。
当时,苏联派出的布勃诺夫使团正在广州,布勃诺夫还真以为是“对人不对俄”,甚至还为蒋介石抱屈说: “中国将军脖子上戴着五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顾问。”他认为在华的外国军事专家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权”;中国共产党 “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
陈独秀根据这些信息,在 《向导》上发表 《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文章说,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势力 “还很强大”,“今后所有中国的革命势力非统一起来,不但不能得着胜利,并且各部分都很难存在。可是不幸最近广州的事变恰恰和这个 ‘革命势力统一政策’相反!”针对 “此次事变是由于共产党阴谋推倒蒋介石,改建工农政府”的谣言,陈独秀在文章中郑重回答:
第一,照全中国的政治环境,共产党若不是一个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第二,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第三,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程潜都不是疯子,共产党如果忽然发疯想建设工农政府,单单推倒蒋介石是不够的。
不过,陈独秀还是从中山舰事件中看到了蒋介石的本质。在陈延年详细报告事件经过,且请示共产国际无明确指示的情况下,4月中旬,彭述之受中央委托到广州组织特别委员会,以 “自己制定对蒋介石的政策”。这个对蒋政策就是“立刻准备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就在此时,鲍罗廷由莫斯科回到广州,带回了斯大林指示,中共仍然继续留在国民党内。
鲍罗廷秉承斯大林的意旨,一开始便对蒋介石容忍、让步,他向中共中央做工作说: “在现时的国民党里没有人像他 (指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 “我们不得不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 ‘党务整理案’,并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
在鲍罗廷的力挺下,尽管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共领导层 “不能接受”蒋的整理党务案,可那也只是消极的牢骚而已。最终 “整理党务案”获得通过,在国民党担任部长的中共党员不得不辞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蒋介石成了最大的赢家,他的地位扶摇直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
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又能做什么呢?6月4日,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针对其 《关于中山舰案对全体党员代表演辞》,以大量的事实予以驳斥。蒋介石说:中山舰事件, “我要讲也不能讲”, “太离奇太复杂了”, “决不能统统讲出来,且不忍讲的”。这种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语词,就是故设玄机,向人们提供错误的思维导向,即事件是由中共引起的,这种手法在某种意义上,比开门见山更具欺骗性。陈独秀驳斥道: “现在先生对全体代表训话中,虽未明说中国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全篇从头到尾,却充满了指责共产党同志的字句,使听者读者都很容易推论到中国共产党实此次事变之阴谋者”。况且, “第一军中实际撤退了许多共产分子及有共产分子嫌疑的党代表及军官”,这也就难怪上海报界说 “事变是中国共产党阴谋倒蒋改建工农政府之反响”。
陈独秀还说:“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我们知道我们的党并相信我们党中人,并没有这样的反革命阴谋”。可是,中共却“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至于你所说一个团体有两个主义,是“一定不会成功的”,这是戴季陶的理论,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中共产分子的话”。而在刚刚结束的国民党二大上,你“曾说共产分子都为三民主义工作,为什么现在又这样说?”
此时的陈独秀十分迷茫。蒋介石已经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可他还以 “左派”面貌出现,还是“赤军”领袖,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还对他颇有好感。面对这样的对手,批评起来就不能直截了当,而只能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他继续说道:
国民党既许共产分子跨党,并未曾主张加入国民党应脱离共产党,如何能一见他兼为共产党服务,便指责他是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呢?除这两样外,还有什么?并且先生自己也说:“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又说:“我认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共产主义”。如此说来,两主义并不冲突,他们兼做点共产主义的工作,也算做了三民主义的工作,说不上什么招牌的话,实际上,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
蒋介石看了陈独秀的信,自然是点到了他的要害之处,很不高兴地说:“不要噜噜苏苏,长篇大论地打起笔墨官司来”,“我讲的话,并不是对共产党讲的,故无答复之必要。……我可以再声明曰: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没有关系”。
陈陈独独秀秀::这些口气乃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
陈独秀所说 “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就含有多年积淀的愤愤不平的怨气。在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他已将蒋介石确定为“将来之敌人”,指出:“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这就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陈独秀的为难之处。
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忧,陈独秀才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中公开提出“革命北伐时期尚未成熟”,担心北伐会给野心家提供机会,他说:“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这些都是有所指的,那就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文章一发表,蒋介石的反应最为强烈,指责陈独秀作为中共领袖,“反对本党北伐,阻止国民革命”,“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影响重大”,“应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答复,免致误会。”陈独秀也没被吓倒,而是通过张静江等作了答复:“若政府当局拿神圣北伐的大帽子来压住民众,硬要牺牲他们利益,这便大大的失了北伐之真实的意义了”。又说:“中山先生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现时还在推翻的运动中,北伐总司令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几乎是无形取消了。”
陈独秀的这些话当然阻止不了北伐。1926年7月,北伐部队向湖南集中,9月7日攻克汉口;北进江西的北伐军一路横扫,进逼武昌。在北伐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陈独秀也改变了对北伐的消极态度。但是,他与党内多数同志对蒋介石因北伐而坐大形成独裁的事实,一直没有放松警觉。9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提出了应对的三种方案:“一、迎汪倒蒋;二、汪蒋合作;三、使蒋成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经过讨论决定“取第二办法”,即迎汪复职,汪蒋合作。
蒋介石得知迎汪复职的消息后,虽恨得“切齿”,但还是隐忍不发,让胡公冕来上海见陈独秀,表示:“请C﹒P﹒(中共的英文缩写——笔者注)勿赞成汪回……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蒋)捣乱,分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甚至扬言汪精卫回他将“决不能留”。陈独秀也明确回答,并给吃了这样的定心丸:“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不主张推翻党务整理案。”
蒋介石一面阻止汪精卫回国复职,一面在北伐途中怂恿、默许反共的暴力活动——赣州惨案、南昌事件、九江事件、安庆事件和杭州事件,枪杀共产党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捣毁省市党部、工会和农协,解散工人纠察队等。正如郭沫若所说,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
陈独秀知道处此乱世中国,有枪就是王,他一介书生,再怎么发作也是秀才遇到兵。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蒋介石的真实的本质。1927年1月25日,中共上海区委提出 “用口头不用文字”,让民众知道“蒋实为反革命”。陈独秀也在《向导》发表文章,指出这样一些现象:有人“经过日本帝国主义拉拢,而与北方军阀妥协,以葬送革命”;有人口头禅“我主张如何如何,反对如何如何,时常‘我’呀和‘我’的大喊,这在党便是表示‘我即党’,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国家’,这些口气乃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这些不指名的批评,稍有头脑的一看便知是蒋介石。
就在北伐军将进上海前,陈独秀与国民党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主席吴稚晖有过一番对话,吴稚晖问道:“那末据你判断,列宁的共产,行在中国要有若干年呢?”这位心直口快的中共领袖毫不设防地回答:“二十年足矣!”吴稚晖当场就急了眼:“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只有十九年,便要借尸还魂了呢?”3月22日,北伐军占领上海,吴稚晖等便于27日来到北伐军行营总部,以陈独秀的话为发难的借口,与蒋介石讨论与共产党分裂的办法。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迎来了北伐军进驻上海,这本是一件高兴的事,可陈独秀的情绪却怎么也振奋不起来。他在中共上海区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要准备继续斗争,我们要看清这个开始的序幕”,“每个党员要懂政治,懂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语焉不详中透露着忐忑踌躇的心理。恰在此时,汪精卫这个为各派政治势力所瞩目的人物,从法国途经苏联,于4月1日回到上海。早在去年10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就通过了 《请汪精卫销假案》。汪精卫此时回国可谓适逢其时,蒋介石、吴稚晖等很快将汪精卫包围,情绪极为愤急,再提“对共产党之弹劾”,并要“采断然之处置”。
在此之前,共产国际已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其中就要求中共千方百计避免与国民党的冲突,即便是蒋介石发动政变,也不得与之公开作战。当汪精卫向陈独秀转述蒋、吴等对中共的担心时,一直与共产国际疙疙瘩瘩的他又能说些什么呢?只能表示决无此事,并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进退维谷的陈独秀正无路可走,现有汪精卫前来转圜,在他看来以一纸宣言就可“解释谣传表明态度”。这正是书生领袖的天真迂腐之处。
可是蒋介石深藏不露,城府在胸。4月7日,他亲自将一面书有“共同奋斗”的锦旗送与工人纠察队,5天后便大开杀戒,开始血腥的清共,是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开列了197人的通缉名单,鲍罗廷列第一,陈独秀列第二。这种对共产党的通缉、追捕、杀戮,遍及全国各地,一直延续到卢沟桥事变。十年之痛,陈独秀失去了最为优秀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怀有党仇家恨的他在这一年写了一首诗 《国民党四字经》,其中有:“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清党反共,革命送终。”据云蒋介石读到这首诗,破口大骂,可见刺到了他的痛处。
陈陈布布雷雷::仲甫近况艰困经呈奉谕一次补助八千元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叛徒出卖而被捕。这对蒋介石当然是好消息,但是却引来许多人的说情,包括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这些他不得不顾及。况且,他们还是有过一段共事的经历,尽管这个过程不是十分愉快。蒋介石对被捕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从来没有慈悲之怀,比如对恽代英、瞿秋白等,劝降不成就立即下令枪杀。纵是劝降成功,在没有利用价值的前提下,也是格杀勿论,对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即是如此。而唯独对陈独秀是个例外。
军政部长何应钦奉蒋介石的旨意,在军政部会客室审讯陈独秀。审讯的气氛比较温和,陈独秀在给高语罕妻子的信中是这样记述的,“弟在军部受何应钦半谈话、半审问后,许多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之小纸条,情意殷殷(充满同情心,毫无敌视表示)令人欣慰,四面包围(长官不能禁止),弟真应接不暇,幸而墨尽,才能解围。”这哪里是什么囚犯,分明是大红大紫的明星大腕。
陈独秀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后又改为8年。自宣判之日起,他便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他一人独处,住在一个12平方米左右的单间,内有书桌、书架,室外就是一个小天井,可以读书报和写作,可以在会客室与前来探视的亲友聊天。伙食也比其他囚犯好,每餐都有两菜一汤。夫人潘兰珍也被允许前来探视并照料他的生活。这一切超出常规的囚禁,没有最高当局亦即蒋介石的“恩准”,恐怕谁也没胆量妄自决定。
陈独秀在狱中完成了《金粉泪》56首,这组长诗对许多国民党大员指名道姓地批评,其中就有批评蒋介石的诗句,例如:“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清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党中无派缘清党,阿斗先生双眼明”;“虏马临江却沉寂,天朝不战示怀柔”;“感恩党国诚宽大,并未焚书只禁书。民国也兴文字狱,共和一命早呜呼”;“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成为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陈独秀在狱中知道后特别高兴,他让人买了酒和菜,喊来同狱的濮清泉、罗世潘,共同庆祝。他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说着,他端着满满的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报了!”在端起第二杯酒时,陈独秀已明显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呜咽道:“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两酹此一杯!”说着就老泪纵横,痛哭失声。这给一直追随陈独秀的濮清泉留下长久的记忆,几十年后,他还说:“我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大怒,但从未见过他流泪。”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使陈独秀提前出狱。他与托派交往的经历,一直是个沉重的包袱,以至演变到由王明、康生栽赃陷害为托派汉奸,这使他十分恼怒。苏联还对蒋介石施加影响,要对中国的托派予以打击。蒋介石何等精明,怎能中了借刀杀人之计,他曾专门发了“委座电谕”说:“凡未实际参加伪组织者,不论谣传如何,均不得称逆。当电中央社及新闻监察所遵办。”蒋介石认为沸沸扬扬的陈独秀托派汉奸乃是 “谣传”,不能以汉奸相待。
陈独秀出狱后,完全舍弃了个人恩怨,积极奔走于全民抗战的大潮中。他对胡适和周佛海等人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他的这种做法却遭到中国托派的反对,他们向托洛茨基告状说:陈独秀 “拥护蒋介石与国民党在进行革命的反帝战争”,我们“与他决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就在陈独秀到江津不久,刚刚脱离中共而任职国民党军统的张国焘向蒋介石建议,可利用王明、康生制造的 “托派汉奸”案,去对陈独秀进行策反。蒋介石以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便派屯兵西北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军统局局长戴笠前往江津拜访陈独秀。
一见面,陈独秀便直截了当地相询,“你们可是奉蒋先生之命前来的”。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又缓缓地说:“自从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知两位先生来意如何?”他还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并让寄语:“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战时的大后方,人员密集,物价飞涨,本无经济来源的他过着捉襟见肘、寅吃卯粮的生活。他的生活主要是依靠微薄的稿酬,大多是朋友及北大同学会的资助,这个倔犟的老人是不甘心接受别人的馈赠,尤其是来自曾经对立的营垒。可生活是残酷的,在万般无奈的情景下,为了生存,他也只能有选择性地接受馈赠,比如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的三笔赠款。这是1940年7月至1942年1月的事情,是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二年。一次1000元,两次各8000元,三次赠款都经张国焘转交。一生傲骨的老人多少有些不情愿,在收到第二笔赠款时,给朱家骅致信说:
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赠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
这些颇大数额的赠款,决非是朱家骅个人所赠,这在陈布雷致朱家骅信中可以看出,信中说: “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难,经呈奉谕一次补助八千元,以吾兄名义转致。”这种馈赠,均是以医药费、困难补助费的名义,不附带任何条件,且都是以秘密的方式进行。之所以选择朱家骅,是因为朱家骅与陈独秀同在北大任事,且有一定的私交,对方易于接受,而让张国焘送去,则因为张既是陈的学生,同时又与陈一样曾是中共老人。毕竟是时过境迁的抗战时期,各方力量在统一的环境中,多少已经缓和多了,况且,此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又何必与老而多病的陈独秀较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