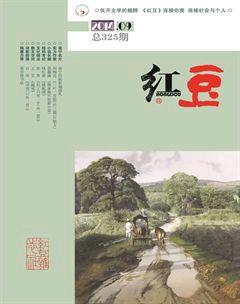小小说二题
梅寒,女,山东临沂人,现居桂林。2006年开始写作,已在全国各大期刊发表百万余字,出版亲子集《做孩子的天使妈妈》、散文集《当一棵小草有了梦想》、长篇人物传记《最好不相忘:张爱玲传》等作品近十部。2012年尝试小小说创作,被评为2012年小小说全国十大新秀之一,小小说作品载于《百花园》《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
【小说长廊·小小说研读】
名 伶
六岁那年,一张“关书”签下,他就成了师傅门下一名年纪最小的弟子。
他与师傅立下字据,八年为期,八年期间,师傅为他提供食宿,但演戏的所有收入归师傅所有。字据上还写着,满师后两年内所有戏份收入也要悉数孝敬师傅。
师傅是名师,名师的条件当然就要有些苛刻,家人还是一一替他答应下来。
学过戏的人都知道学戏的苦,那份苦却超出了他年幼的想象力。在师傅家里,一边学戏一边干活一边挨打。学戏从最基本的东西学起,唱念做打,一招一式,稍有一点不顺师傅的意,师傅手里的鞭子就落下来。不过,他学戏挨的打倒不如平日干活挨打多。劈柴生火,挑水做饭,给师傅端茶倒水,侍候师傅更衣,这些琐碎的事务占去了他大半时间。师傅面前,他低眉顺眼,战战兢兢,还是常常让师傅不满意。他出师以前,腿被师傅打得新伤叠旧伤。
师傅待他严苛,却还是极欣赏他的艺术天分,师傅看好他是梨园之内一棵好苗子。待他年龄稍长,师傅为他量身定做适合他的唱腔角色:这孩子性格比较抑郁,面常无欢容,不宜演花旦,可主攻青衣。
从此便主攻青衣。
眉清目秀的翩翩少年,穿了戏装,扮演的都是端庄正派的女性,或贤妻良母或贞节烈女,舞台上一站,便有遮不住的光华四散开来。当时有一大名士,初次看他登台就被台上的他倾倒,大笔一挥为他作了六首绝句,将他与舞台上风华绝代的梅兰芳相提并论……
却在那样的节骨眼上,他的嗓子出了问题,行话叫提前“倒仓”。提前“倒仓”搁一般戏子身上,就代表着他在那梨园行业的生命终结。他没有,他运气极好。几经周折,从前任师傅那里提前结业出师,再拜一师傅。此位师傅只听了他几段唱,就发现了他的与众不同:此生禀赋与众不同,不能以常情教之。师傅发现他清晨的嗓音不错,到了晚上八点以后反倒唱不出来,师傅还发现他平时的嗓音窄而涩,喝了酒以后反而宽且亮。师傅便根据自己的这一发现为他作了特殊的安排:早晨只喊嗓不准唱,一直到晚上十点以后再开始吊嗓子练唱。师傅如此要求有师傅的理由:角儿一般都是晚上九十点钟以后出场,晚上唱不出如何做角儿?师傅还一改平日不准弟子沾酒的规定,他就成了师傅门下唯一一个可以喝酒的弟子。
师傅因材施教,徒弟刻苦演练,他很快就成了名噪一时的角儿。
一出《玉堂春》,各路名家名派都曾唱过,到他那里,演得更是耐人寻味。因自己身形高大,他一改往日的着装形象,红色的罪衣罪裙;因自己的嗓音曾经出现过的问题,他的嗓子又显得格外柔和,行腔乍疾乍徐,一股细音,高处如天外行云,飘飘洒洒,低唱则如花下鸣泉,幽幽咽咽,再加上别具一格的着装,一高大倜傥的儒雅书生瞬间就成了满面憔悴、满腹哀怨的青楼女子,一出戏演下来,那唱腔那身段早已让台下的观众疯狂如痴。
那一段岁月,是他生命中最华丽的时光吧。一场接一场的演出,从北到南,场场爆满。他因家境贫寒而入梨园,十几年后梨园给了他最丰厚的回报。他因戏而贵,因戏而富。演出最盛的时候,他的手下人一次就给他存入几十根金条。
他一演,就是几十年。
及至他年纪渐老,便很少再上舞台,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扶掖后人上。改编戏曲,创办学校,每一项,他都勤勤恳恳去做,每一项,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他已是名伶,是梨园舞台上的大师。关于他的戏剧人生,也被搬上舞台,一演再演。戏中舞台上的他,爱戏爱得痴迷,演戏演得忘我。台下看戏的观众,一次又一次被舞台上的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名伶啊。
那时,他在哪?他正倚在医院的病床上,手上捧着有关他的大篇报道的报纸。
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在台上装模作样、扭扭捏捏演了一辈子小妇人?谁又愿意呢?实在演累了,该轻松轻松了……
一代名伶,离世前的心里话竟然是这些?谁信呢?
却是真的。
他离世前最大的遗憾,是不能穿上戏服再演一回《玉堂春》。
也是真的。
回 报
拿到那纸宣判书,他脑子里只轰鸣着一句话:为什么要这样待我?!
是的,命运真是太残酷了。他吃了那么多苦,经了那么多波折磨难,才跌跌撞撞挤进成功人士的行列,有了自己的上市公司,有了香车宝马活色生香的生活,可他在灯红酒绿觥筹交错间还没醒过神来,命运他老人家就要把这一切都给没收回去了,连老本儿也不给留。
肝癌中后期,字字如冰刀,每天都在切割着他的神经。他一夜一夜地睡不着,人迅速地消瘦下去。
用不了几天,我这盏灯就油尽灯枯喽。面对前来探望他的亲朋好友,他只有这一句话。众亲朋也不好说什么,陪着他长吁短叹安慰一会儿,红着眼睛就走了。再犟犟不过命啊。他继续昏睡。有几次,他甚至清晰地听到死神来叩门的声音。
有一天你死了,你记着,你一定不是病死的,而是被自己吓死的。这话,只有跟他共同生活了十几年的妻能说得出来。
他一下子被骂醒了:是啊,与其这样躺在家里被自己吓死,倒不如起来做点什么。
重回那个久违的小村看看,是他醒来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
小村很小,在重重叠叠的大山里头。尽管来前他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无论从物质上还是心理上,可当他拄着拐杖站在村头唯一一条进村的小路上,在暮色中向村子里张望时,眼泪还是刷的一下子流出来。二十年了,他从当年的毛头小子步入中年,从当年的一穷二白到今天腰缠万贯,村外的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小村竟然还是二十年前的样子,时光在这里似乎静止了。不,小村明显被光阴漂洗得更陈旧了。倚山而建的青石小屋,还是二十年前他初次来这里时的那些草屋,只是那些屋子已经比二十年前更加破烂不堪,还是那条进村的小路,小路看来也少有人走,几乎被路边的荒草吞没了。更让他痛心的是那些从他身边走过的孩子,他们衣衫不整,浑身上下脏兮兮,看他的眼神,像看外星来物。大概,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衣着光鲜的山外人。
二十年前,小村把温暖无私地送给他,却被世界遗忘在文明与进步之外。
“那年我高考落榜,家里又穷,再也复读不起啊。跟着村里人南下打工,不知怎么就迷迷糊糊跟人走散了,一路走到那深山里,最后连累带饿,就晕过去……那时,小村也这么小,这么穷。可当他们听说我的事,全村人集资凑了几百块钱,又派人把我送出山……那是什么?是恩情啊。如果没有当初他们的倾囊相助,哪会有我后来的飞黄腾达……”从小村回来,他的日子里多了一桩新的心事。他跟妻子忆当年,说着说着便常常泪流满面。
他体内的癌细胞应该肆虐得更凶了吧,阵阵疼痛的浪来得更加勤快凶猛。他的时间,也许真的不多了。
当他指挥着大批的人,将水泥砖头沙子运送到小村村口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被惊动了。他们倾巢而出,争相跑来观看。你看他,那穿着,一看就是大人物啊。是啊是啊,要是再胖一点就会更有派。看他面相就慈善……二十年过去,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他。他们只当他是上天给他们送来的活菩萨,是来度他们的。修桥铺路盖学校,盼了多少年才盼来。
进山进村的路都不好,工程进行得很缓慢。他在小村的日子也越来越多,慢慢的,小村竟成了他的第二个家。很多时候,他离开远在都市的家,也离开公司,在小村里陪着那里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同他们一起嚼着粗茶淡饭。筹措资金,备料招工,他在城市和小村之间来回奔波,很少有时间去医院,更少有时间痛苦难过。那时,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在支撑着他前行:他要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给曾经给予他再生之恩的小村以最好的回报。
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也没有人知道他来此处大兴土木的原因。他像一滴露珠,像一棵绿色植物,自然而然融进了那片茫茫的大山里。他们,已经将他视为自己身边的一位亲人,视为同他们一样的大山的儿女。
他如愿以偿。当那所漂亮的山村希望小学落成时,距离医学上他的死期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学校落成典礼上,他第一次在村民们面前流下了眼泪,他说:二十多年前,我差一点饿死在这里的大山里,是这里的乡亲们给了我再生的机会。这一次,我回来,只想能为乡亲们尽一点绵薄之力。可我想不到,我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再一次将我从死神那里抢回来了……
他去医院做检查,结果连医生们都不敢相信,他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