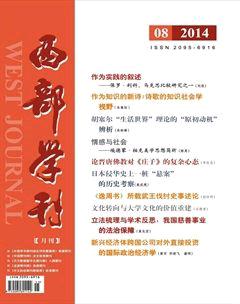从依附理论到世界体系理论
摘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依附和世界体系理论在关于后发国家的发展问题上,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是随着世界的发展与变化,这些理论的解释力却日益式微。比较而言,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诸如帕累托最优、资源禀赋等,在面对现实变化时,其解释力依旧十分强大。为什么不同理论解释力的可持续性有如此大的差别?通过分析发现,理论在形成和演绎的过程中,其分析单位与微观基础的匹配度决定了理论的解释力是否能够持续。
关键词: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分析单位;微观基础
中图分类号:F091
在解释后发国家(Late Developmental State)的贫穷以及如何实现赶超的问题上,从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再到发展型国家理论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我们依旧发现,伴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部分理论的解释力逐渐式微,甚至被新理论所取代。为什么这些理论在世界的变化面前无法实现持续?进一步,我们把视线再转移到经济学和物理学领域,发现经济学如资源禀赋、帕累托最优以及纳什均衡等理论,经典物理学的万有引力定律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依旧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这又是为什么?本文认为,理论在形成和演绎的过程中,其分析单位与微观基础的匹配度决定了理论的解释力是否能够持续。
一、什么是理论及理论解释力的来源
什么是理论?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理论是对现象系统的反映,旨在说明这些现象,并显示他们是如何相互密切联系的。[1]对于这种定义,华尔兹(Kenneth Waltz)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他将理论定义为人的头脑中关于某一领域的组织性及其内部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的一幅思想性图画(mental picture),是一种简化了的描述,其功能在于对某一限定的行为领域加以解释而非对现象规律的描述。[2]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更加简洁地将理论表述为一个所要解释的现象背后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一个简单逻辑体系。[3]总结来说,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是对现象的一种抽象,而非简单的对现象及其现象背后规律的描述。
依照上述对理论的定义,重新审视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当前热门的发展型国家理论,会发现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或是发展型国家理论都充斥着大量对现实世界的描述,而非对现象的解释。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在解释后发国家的落后问题时,给出了不同答案,依附论给出的解释是因为后发国家与发达工业国家的依附关系的存在,世界体系理论给出的解释是由于以单一经济体系、多元政治体系、多元文明体系为特征世界体系的存在,而发展型国家理论在解释东亚后发国家赶超奇迹时,给出的答案是这些国家拥有符合市场规律的有效的国家干预、良好的政商关系、强烈的发展意愿以及存在一定数量的领航机构。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理论给出的解释更多的是对现象的一种总结性或概括性的描述,而非对现象背后的逻辑关系的探讨。从这一层面来看,这些理论在被建构的过程中,还仅仅只是停留在归纳或者是演绎的实证层面,远远没有进入实证背后的因果逻辑推理层面,这也埋下了其解释力不可持续的病因。
进一步,被构建起来的理论为什么会有解释力,其解释力的来源又是什么?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对社会科学的逻辑进行阐述的时候,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所有社会科学无疑都是解释学,因为它们能够描述任何既定情景中‘某人正在做什么”。[4]吉登斯的表述标明一个理论的好坏在于其解释力的强弱,而解释力的强弱取决于:第一,其研究范式;第二,其逻辑推理;第三,其研究方法和工具。[5]
艾尔·芭比(Earl Babble)将范式定义为用以指导观察和理解的模型或框架。他指出,范式不仅形塑了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同时也对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些事物产生影响。[6]范式在科学研究中发挥了一个根本性的作用,范式所带来的革命效应也是巨大的,历史上,每一个科学理论的出现都蕴藏着科学研究范式的巨大变革。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范式不会像自然科学中那样出现革命性的更替,只有是否受到欢迎的变化,很少会被完全抛弃。面对同一现象,不同的社会科学范式提供了不同的观点,范式没有对错之分,作为一种观察和理解的方式,每一种范式都有自己独特的关于社会事实的假设,带来不同类型的理论,并且带来不同类型的研究。但是由于不同的范式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就不同。在多元范式混杂并存,特别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使得许多问题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往往一个解释力强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所坚持的范式。
理论的内部逻辑并不等同于通常的归纳和演绎,虽然归纳和演绎是理论建构的主要方法,但归纳和演绎只是理论建构的初级阶段,通过归纳和演绎得出来的结果只是停留在现象的规律层面。理论真正区别于通常所称的规律、定律,关键就在于其对规律产生的原因有一个逻辑上的推导过程,理论内部的逻辑告诉我们的不是“这个现象是什么样的”,而是告诉我们“这个现象为什么会是这样”。黑格尔(G.W.F Hegel)在《逻辑学》一书中曾说过:“这些心理的、教育的、生理的观察、规律和规则,无论是在逻辑里或在别的什么地方,一定大部分都显得索然无味。至于这样的内容为什么如此毫无精神,就在于这些规定牢固不变,相互间的规律性联系也仅仅是外在的”。[7]因此,理论内部的逻辑是否严谨精致就决定了该理论的解释力强弱。
理论所采用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归根到底都是服务于理论的内部逻辑,也就是对理论逻辑的检验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理论的“外洽”的过程。有学者认为理论不应该是简单的逻辑游戏,理论是要解释现象的,因此理论的逻辑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必须是一致的,也就是指理论的内部逻辑推论和经验现象的“外洽”。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理论是框架性的,是从现象中抽象发展出来的。无论是物理学还是经济学,都是通过远离对世界的直接经验,然后对其加以高度抽象的描述而获得发展的。这两种争论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即理论到底如何服务于现实?从这个角度去看,其实这种争论是可以统合的。理论的推论与经验现象是否一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论的推论是否与现象所产生的逻辑相一致,这才是理论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所要检验的东西,也是解释力的根本来源。
从上述分析来看,研究后发国家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发展型国家理论,每一个理论的解释力都与其研究范式、内部逻辑、分析工具和方法息息相关。依附论从国家出发,通过行为主义的范式考察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关系,从而来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世界体系理论继而以体系角度从结构主义的范式分析了世界体系的结构,进一步揭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内的具体位置、关系和运动规律。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范式带来了不同的逻辑,由此给出了对现象不同的解释。解释力的强弱随着范式的变化而变化。
二、分析单位与理论范式:理论的强化与削弱
针对后发展国家发展问题,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都给出了解释,结合上一部分的分析,每个理论都有自己的范式,都有自己的因果逻辑、分析方法和工具,但为什么这些理论的解释力依旧还是不能持续?
再来比较一下经济学和经典物理学,可以说经济学和经典物理学是两个完全不相关的学科,一个属于社会科学,一个属于自然科学,但为什么两者的解释力如此强大并可持续。经济学理论解释力的基础建立在理性人的基础假设之上,而理性人的假设则又是以人这种个体为分析单位,由人到理性人再到以此假设为基础前提的各种理论。经典物理学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质量集中于一点,这种简化的假设基础之上,而这种假设又是源自于普通的微观层面的物体远动,最后推演到宇宙。那么总结起来,经济学和经典物理学之所以能够拥有强大的解释力,可以说与其分析单位是密不可分的。
社会科学常见的分析单位从个体、群体、组织到各种社会人为事实,一个研究对象可以通过多个视角,选择不同的分析单位来进行研究,比如依附论就从国家的层次来研究国家间的依附关系,而世界体系理论则从世界体系的结构层面来探讨国家间的相互联系,同样是解释国家的发展问题,不同的分析单位带来的范式以及理论的逻辑都不一样,因而解释力就不一样,那么,分析单位是如何削弱理论解释力的呢?
分析单位的错误推理通常有两种情况,即区位谬误(ecological fallacy)和简化论(reductionism)。区位谬误通常是以对群体的观察来解释个体或者用个体的行为来解释群体,个体行为是否等同于集体行为,这之间的鸿沟如何跨越,往往导致了学者们的争论,也即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方法论的争论;而简化论则是将一个现象归结于某一方面的原因而忽视了另外一些解释,导致的结果就是单一的解释无法做到全面的解析,这也是单一性与多元化的分歧。因此研究问题的适用分析单位并不总是清楚的,但是对问题的研究往往尽可能减少方法论上的缺陷,才能提高理论的解释力。
依附理论从国家出发,把整个国家当作一个行为体,研究国家间互动及其关系的变化,这是明显的集体主义,这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缺陷,忽视了国家行为变化的根源,是什么导致了国家行为的变化这个问题就被依附理论所忽视,因而伴随着国家行为及国家间关系的变化,依附理论的解释力逐步变弱,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上分析,依附理论似乎就遭到了挑战,苏联和东欧的变革无疑更是对绝大多数依附论坚持者的一个动摇。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卡尔多索(Fernando Cardoso)的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也受到怀疑。总之,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国际关系的现实都对依附论提出了挑战和质疑。它无法解释的是同样存在依附关系,为什么日韩等国家实现了赶超,而拉美大部分国家却依旧落后。世界体系理论在解释后发国家的问题的时候,在依附论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指出了国家行为变化的外部结构性因素,即国家所处的世界体系结构的变化,但是依旧没有解释在同一外部体系结构下,为什么有的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能够上升到半边缘甚至是中心地带,而另外一些国家长期处于边缘地区?从另一方面说,对于现在所谓的不发达国家而言,不管是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还是与其隔离,这些都不能保证一国经济的发展,重要的是一国改造自己国家经济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战略、财政体系以及经济和政治领导人是至关重要的。世界体系理论只是一种外部维度的分析,只是从国际经济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行出发来说明国际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总体来说,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缺乏对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研究,没有打开国家这个黑箱。
三、找到微观基础:分析单位的匹配
到底什么样的分析单位才是合适的,有学者指出分析单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并没有限制,分析单位就是所要研究的对象,对象是什么,那么分析单位就是什么,分析单位需要和结论中的单位保持一致。也有学者指出分析单位的选择取决于并服务于研究假设。还有中国学者指出分析单位有时不一定是研究结论中所解释的单位,一项研究中可以有多个分析单位,只有从多个层次、不同角度去研究才能得到真实、完整的信息。在这种不同的争议之下,到底该如何去寻找合适的分析单位呢?
如上文所说,分析单位往往是和理论的微观基础相联系的,那么作为国际关系中分析国家行为的理论,到底其微观基础应该是什么,是国家,还是国家所处的体系或是组成国家的个人、组织?仔细观察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理论的分析单位的变化,会发现其路线是从国家上升到国际结构,是一个向外发展的路线;那反过来,为什么分析单位不从国家下降到国家内部结构,甚至到组织,到个人呢?再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来看,似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都避而不谈国内结构问题,而直接将所有国家作为行为主体,考察其国际行为。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曾指出民族国家的国内结构是一个关键的变量,没有它就不能理解国家相互依赖与国家行为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大量的文献无法给出关于石油危机的挑战使得不同国家有不同行为的原因的解释。而将国内结构分析引入国际关系,强调国内不同行为体的作用,打破了长久以来国际关系中对国家内部视而不见的现象,这也成为卡赞斯坦标志性的贡献。
如上文所述,依附理论在解释后发国家落后的原因时,仅仅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依附关系层面给出答案,一方面忽略了结构因素,另一方面更忽略了个体的能动因素。而世界体系理论尽管在依附论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从世界体系结构的层面进行了分析,指出后发国家的贫穷落后是由其所处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结构所导致的,但是也出现了分析单位完全上升到体系结构层面,脱离国家这一行为体基础,忽略个体的能动作用这一重大问题。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微观基础应该是国家内部结构,因此其分析单位应该着眼于国内结构层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在对发展问题的研究上重新找回了国家,在对国家内部的分析中找到了问题所在。
四、结论
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在其所编的《找回国家》中就曾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政治科学和社会学中主流的研究视角都是多元主义论和结构功能主义,忽视了对国家本身的研究。此阶段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通常喜欢寻求对所有国家共同拥有的特征和功能进行一般化,而且通常是以极端抽象的方式,比如用单一的生产模式、单一的资本积累的状态,或者用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来进行概括。这就难以为国家结构与行为的国别差异和短期变动等因素赋予英国变量的重要地位,从而削弱了一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力。这其中就包括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当我们在勘察理论、模型或制度形式在不同国家间的传播过程时,发现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国家行为或经济思想时,我们更需要的是领悟出这一充满矛盾的结果的真正含义,即将视角重新放回到国家本身上。
建立在国家是单一的、有目的的行为者这一假设之上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分析单位由国家上升到体系,由对国家行为的考察上升到对国家所处的体系的考察,远离了国家本身。找回国家,回到对国家内部的考察,才是正道。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M].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2](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3]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M].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岳彩申.理论的解释力来自哪里: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反思[J].政法论坛,2005,(11).
[6](美)艾尔·芭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7](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作者简介:曹飞(1989—),男,安徽淮北人,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国际中心学术研究室主管。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东北亚关系。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