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被捆绑在小说柱子上的浪漫诗人
李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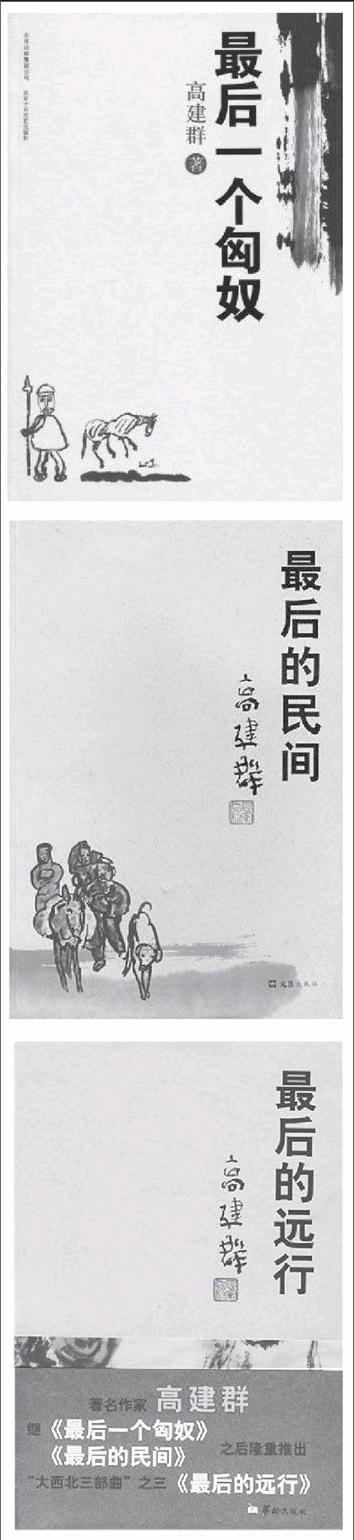

“陕军东征”曾引起文坛剧烈震动,并成为重要文化现象被载入史册。时至今日,“东征三驾马车”依然笔耕不辍,以旺盛的创作精力续写着陕西文学的辉煌。
作为“三驾马车”之一,高建群老师作品风格鲜明,被评论界誉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是当代文坛罕见的具有崇高感、古典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的重要作家。
因小说成名,但他却是一位极具诗人气质的作家。他的作品里随处可见诗歌元素,诗歌的语言,诗人的情怀。走近他,我们会发现,他就是“被捆绑在小说柱子上的浪漫诗人”。
建立文化中国制高点
李 东:高老师您好!去年您被聘为西安航空学院文学院院长,前不久又成立了高建群文学艺术馆,这是学校重视文科教育的新举措,对您个人也有特殊的意义吧?您对繁荣高校文艺有什么新的打算?
高建群:长沙湘江边上有个岳麓书院,是北宋时期朱洞创办的,被称为“千年学府”,王阳明曾在这里讲学,而他受当时国学大师张载影响颇深。张载是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历史上把他叫“横渠张载”,他最有名的四句话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南方的文化人都很推崇张载,像曾国藩、李鸿章都认为南方文化人不像北方文化人,不像张载那样把天下为己任,有一种担当精神,做人做事做学问,有大格局。
西安航空学院虽然不大,但是他们高抬我,请我去当文学院院长,并且建了高建群文学艺术馆,所以我也诚惶诚恐,觉得人家这么重视我,去了以后,就想把它作成岳麓书院、关中书院那样,文化人的聚集之地。上次西安市挂职副市长、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先生来文化馆看我,问我有啥打算,我说要把西安航空学院文学院,朝三个方向发展:第一个是成为文化的亮点,第二是成为文人聚集的热点,第三是成为文化中国的一个制高点。
西安这个地方养人,更养文化人。我就在那里穿一双老布鞋、带个二轱辘眼镜,一身布衣,把这个事情做下去。长安城深泽大潭,宜养千年老鳖,就在那里有年没月地活下去,看能不能做成气候。我给文学艺术馆的大门上写了一副对联:对联是“三间旧屋半亩园,落落乾坤大布衣”,横批是“人书俱老”,里边有书画间和写字、喝茶的地方。门口原来的草坪,现在种上了菜。今年5月2日,也就是唐僧去世1350周年纪念,我到兴教寺参加纪念活动,门口有老农卖菜苗,我就买了菜苗回来栽上,大家把那个地方叫“半亩园”,我还写了一首歪诗:“城中我有半亩园,锄头举处可耕田;不为菜蔬不为果,只为乡愁只为看。”现在西红柿红了,辣椒茄子都熟了,看了也舒服,就觉得和大地在一起,和平民百姓在一起,就是在那里寻找一份精神归属。
我感觉我的心态就像一条河流,开始起步,经过跌宕,最后归为大海;也就是那种很包容的感觉,平躺在沙滩上,海天一色,慢慢走完自己的角色,直到谢幕。
李 东:您的生活阅历相当丰富,有过苦难的童年、当兵的经历,也有做文学编辑、区县挂职经历,现在又被聘为大学文学院院长,哪一段经历对您的影响最深刻?
高建群:我相信命运。每个人来到世界上的那一刻,他的额头上已经被打上宿命的印戳,他的很多东西早已有上苍安排。我的童年很苦难、很贫穷,人们把那叫困难时候,人不值钱,像狗一样一个个死去。当兵时在一个荒凉的边防哨所待了五年,然后也有文学上的努力,也挂过职,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童年的经历。童年对我的影响最大。
人们问高尔基文学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高尔基说是苦难的童年。高尔基第一次拜访托尔斯泰时,托尔斯泰打开门一看,一个风尘仆仆的青年流浪者前来拜访,身上还有一种海洋的味道,因为做过水手,那就是青年时候的高尔基,那时候他还不叫高尔基。托尔斯泰听了他的苦难之后,说:“孩子,在拥有了这些经历之后,你完全有理由成为一个坏人。”托尔斯泰双手举过头顶:“圣母啊,你是一只无底的杯子,承受着世人心酸的眼泪。”高尔基告别托尔斯泰后,正式改名“高尔基”(也就是“苦难”),并开始文学创作,写出了《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
李 东:之前在一个会议上,听您谈到西安高新区挂职后,要创作新的三部曲:《三千个传奇》《三千具尸体》《太阳从西部升起》。您的作品给大家的印象是,关注视角总是纵深的历史,要转向现代化和高科技,我们充满期待。现在“三部曲”进展如何了?
高建群:在西安市高新区挂职是在2005年4月27日到2007年11月27日,整整2年零7个月。当时去的时候,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在欢送会上我有个发言,题目叫《艺术家,请向伟大的生活本身求救吧》。这个发言新华社发了通稿,在全国发出。在发言中我坚持一个观点,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应该到生活中去,到正在发展的时代中去,看看主流社会、主流人群在做些什么事情、思考些什么事情,把这个时代记录下来,而不是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顾影自怜、自怨自艾。当前我们的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一再被边缘化,这个边缘化的原因,有社会的原因,更有作者自己的原因,我们远离了生活,所描写的那些东西老百姓已经不关心了,他们更关心当下最迫切的生存状态。
《三千个传奇》就是高新区三千个创业成功者的故事,成功者都有成功的必然原因;《三千具尸体》就是三千个失败者,怎么在时代的大潮中做弄潮儿的时候失败的,虽然失败了,但他们也是悲剧英雄;再到《太阳从西部升起》。原来想写这些,但实际上已经写成了,挂职结束的那个中午举行了欢送会,下午回来后我就带着一支笔、一个本子、一个袋子、一杯茶和手机就到公园开始写作。写了一年零十多天,写成了长篇《大平原》,上面的这些素材成了《大平原》的后半部分。《大平原》就是写了农耕文明在今天面临的窘境,写一个村庄、一个家族、一群人他们的故事、传奇、命运,写到村庄变成了高新区的一部分,写到这片古老土地从后稷挖第一锨土开始,历经五千年春种秋收,一直到当代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被取代,最后写村口的老槐树被连根挖起,然后它将在城市的某个街心公园里成为风景树。《大平原》大概就是写这个故事的。当然《大平原》后来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长篇小说类名列第一。电影和电视剧目前还在前期的运作中。
文学必须向新媒体就范
李 东:《统万城》出版后,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是您的“封笔之作”。对于您这样不断抛出大部头作品的作家来讲,写作应该早已成为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您不会就此“罢手”,对吗?您个人对于艺术创作还有怎样的规划?
高建群:我在写完《大平原》以后,休息了一个礼拜,之后到汉中去了一趟,回来后有一天中午正吃饭的时候,旁边陪同的人说我脸发生了变化,叫中风还是叫面瘫,说我眼睛和嘴巴都成歪的了,很可怕的,后来住了二十多天医院才缓过来。出院后,我就说不敢写长篇了,每写一次就是和死神打一次交道。但是后来又遇到了《统万城》的题材,在我55岁生日的那天,受邀到草堂寺,草堂寺住持在那里给我讲鸠摩罗什的故事,给我念了四句偈语:“云远天高古道长,沙漠驼铃震四方。晶莹最是天山月,为尔遍照菩提光。”他希望我能写鸠摩罗什,他说鸠摩罗什等了一千六百多年,终于等来了能够写他的人,我就应允下来了。后来榆林那边又想让我把统万城写一写,这是个重要的题材,发生在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发展史重要的节点和拐点,一个是匈奴民族退出民族历史舞台,一个是汉传佛教在中国的确立。然后写这两个题材,又用了一年多时间,在榆林写了一部分,回到西安又写,把这个写完之后,确实身心疲惫,然后我热泪盈眶地说:我被文学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绑架了四十年了,我应该就此向长篇小说这个体裁告别了。
书出来以后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就有记者问我:“高老师,您能写这么好的小说,难道您忍心不再写吗?读者会答应吗?”我就觉得我那话说得太早,于是就这么回答道:“演员在谢幕以后,如果观众的掌声热烈,会将他重新召唤回舞台。”
《统万城》出版后这两年多,我也出版了一些书,文学的、绘画的。现在我正在写一部书,将近三十年前写过个中篇《遥远的白房子》,央视不舍不弃想要拍成电视剧,春节前把剧本已经写完了,我把剧本过了一遍,现在有我的中篇小说,有央视的三十集剧本,我打算用一两年时间把这个写成一个长篇,这就是我最近的计划吧。
李 东:《最后一个匈奴》曾被改编成电视剧《盘龙卧虎高山顶》在央视播出,而新作《统万城》和成名作之一的《遥远的白房子》等也将被搬上银幕,这再一次印证了您作品的艺术价值。筹拍工作进展怎样?您又是如何看待文学与影视“联姻”的?
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当时是央视派了电视剧频道制片人李功达找到我,在宴会上他说:“如果不把高老师的《最后一个匈奴》这部中国文学的红色经典拍成一部电视剧,那将是中国电视剧人的羞愧和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失职。”这话彻底把我打动了,我就授权说那就拍吧。后来拍出来还可以,但是他们说不如作品那么厚重。当然影视作品创作就是慌慌张张,四五个月拍出,完了再几个月剪辑、播出,有些粗糙,基本上还是能接受。我和他们也谈过,男一号潘粤明、女一号刘涛、女二号秦海璐、女三号李欣汝,他们钻到陕北山沟里面像鬼一样,见了人都不认识,他们的表演让我很感动。刘涛说她以前拍过很多影视作品,直到《盘龙卧虎高山顶》才回到人间,双脚踩在坚实的大地上。这个片子原来一直叫《最后一个匈奴》,在播出前广电总局打来电话,问还有没有其他名字,我就随口说那就叫《盘龙卧虎高山顶》,名字改变对收视率也有一定影响,但电视剧基本上让各方都满意,收视率还不错,投资方也回报颇丰,我也心安。
《统万城》的电影去年热了一阵子,也初步定下来,由香港导演张之亮担任导演,他拿出一个庞大的计划,可能要投资两个多亿,这也不是个小数目,投资方下不了决心,我也不愿给投资方施加压力,这已经进入商业运作模式,不能因为朋友的关系受影响。《统万城》的电视剧也在筹备,就是《遥远的白房子》的编剧老韩(韩庆敏)在做,电视剧可能比电影出来早一些,据说这个投资六千万就够了。
对于《大平原》,央视的思路还是《盘龙卧虎高山顶》的那帮人来做,后来他们找了个编剧拿出个大纲,我看了不太满意,因为那个编剧不了解关中农村,事情也就搁置了。
《遥远的白房子》的剧本,央视年前已经给我,根据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意见,我将剧本作了修改,编剧也作了修改,送审到广电总局也通过了。原来计划今年6月开拍,男一号是王力宏饰演马镰刀,女一号是刘亦菲饰演耶利亚,可能是演员现在到新疆有些担心吧,有些畏难情绪。新疆方面希望拍成继《冰山上的来客》之后的又一部西部经典之作,他们是这样计划的,可能已经行动了。在新疆霍城,就是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的地方,霍城有个老街,在那里修个影视城,明年5月建成,修好后会有部队警戒、演员进入,明年5月以那里为基地拍摄。可能到时我会去参加开机仪式,但是我不会干扰他们的工作,因为影视和小说还是两种文学形式。
对于文学与影视“联姻”,我们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承认,随着新兴媒体的出现,纸质印刷品日益边缘化,必须面对这个严酷现实。去年11月份,在省上组织的一个作家影视联姻会上,我曾说到:“面对影视网络等新兴传媒,文学必须低下高贵的头,向它们就范。”
李 东:在您几部重要作品中,插图都是您自己的书画,许多文字内容通过书画形象展示给读者。据我所知,您的书画作品也受到广泛赞誉并被收藏。您什么时间开始学习书画的?同样是艺术的表现形式,您如何理解书画创作和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
高建群:任何艺术都是相通的,小说艺术和书画艺术十分相像,应该怎么做,高度在哪里,用雨果的话说,就是“把艺术的某一个特征发展到极端,然后在极端的峰顶重造和谐。”
我参加过文革,当年刻毛主席像、写大字报,如果要追溯的话,那个时候就是我绘画的开始了,但真正对书画的认识还是在创作《最后一个匈奴》的时候。当时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案头就是两本参考书,一本是《印象派的绘画技法》,莫奈、德加、雷诺阿、塞尚、梵高……是他们指导我,把生活变成艺术的,另一本就是拜伦的《唐璜》。哦,伟大的拜伦。后来我也开始尝试给自己的书插一些画,尤其在省文联上班后,认识了很多书画家,也是向他们学习,很多书都是我插图,我的书画也有一定市场。但是对于书画艺术,我始终定位于自己就是个“票友”,写小说才是我的本职工作。
写文章时要目空天下
李 东:我在《最后一个匈奴》的创作谈中读到您创作的艰辛,但让我疑惑的是,在创作中您的两本指导书是《印象派的绘画技法》和长诗《唐璜》,为什么不是小说的大纲或者其他什么书籍呢?
高建群:你们不要听小说家、评论家告诉你小说应该怎么写,小说艺术具有无限可能性。你怎么写,都会写成好小说,不像某些人所说的,小说应该这么写应该那么写,那些都是一些技术性的东西。小说,谁都有可能教会你写。云南民歌唱到的“父母没有教会我们谈恋爱,是路边成双成对的蚂蚁教会我们的。”的确如此,大自然的各种法则各种规则,都会教你怎么写好小说。你只要想把肚子里的有些东西向读者倾诉,就把笔拿起来,真诚地倾诉给读者,读者说太好了,那就是小说。孙犁先生说过“人一拿架子,就先失败了一半。”有些人说,我要开始写小说了,就是这个道理。好小说怎么写出的,就是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雨,你各种感受,各种陈年旧事如果不把它倒出来,就像猫在挠你的心一样,像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行走一样,要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卸下来,就轻松了,把重负交给读者了。这就是小说。
我刚才谈到印象派的绘画技法,谈到拜伦的《唐璜》。拜伦是个伟大的诗人,他对欧美文学的影响,也许只有莎士比亚能够与之比肩,整个十八世纪的欧洲,因为拜伦而发了狂。我举个例子,俄罗斯在普希金之前,没有文学,只有小小的戏剧和寓言,普希金开始了俄罗斯文学,所以普希金被称为“一切开端的开端”。普希金的文学从哪里来的,就是学习拜伦的,他学习《唐璜》写出了《叶甫盖尼·奥涅金》。拜伦是很伟大的诗人,他为英国贵族社会所不容,于是在一个早晨,坐上一辆华丽马车,左手搂一个黑人美女,右手搂一个白人美女,拐杖一扬,说:“要么是我不够好,不配住在这个国家;要么是这个国家不够好,不配我来居住。”说完,马鞭子一扬,在欧罗巴大地游荡,写出了不朽之作《唐璜》。
李 东:在对您作品的相关评论文章里,我注意到一个关键词:史诗。作品被推崇到史诗的高度,这不是普通小说家能达到的,我们也知道您早年写诗,后来为什么转向小说了?您的小说作品里,时常流淌着诗意的语言,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是您诗人气质的体现?
高建群:我在很多场合说过,“陕军东征”的几部作品的出现,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概在1985年的秋天,当时路遥主持过一次重要的创作会议,路遥说那个会议不知道叫啥,后来就叫做长篇小说促进会。那个会的主题,就是“文学的最后的较量,是长篇小说的较量”,从而号召大家都来写长篇。这个会议一完,路遥就率先钻到陕北写他的《平凡的世界》,我写《最后一个匈奴》。先是《平凡的世界》出来了,接着《最后一个匈奴》,接着《八里情仇》出来,接着《白鹿原》、《废都》、《热爱命运》出来,所以跟这个会有很大的关系。
我感激诗歌,我的语言在小说家里面是独树一帜的,不敢说最好的,也是最好的之一。他们认为浪漫主义文学当代有两个代表:一个是张承志,一个就是我。这个跟我写诗歌有关系,诗歌对于语言的锻造,诗歌中提炼出来的那一种意境,在我的小说里面随处可见,我是用诗在写小说。前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说过:我是一个被捆绑在小说柱子上的浪漫诗人。实际上我也是的,尤其是我的《统万城》,有专家指出它是新五四以来,白话文创作上真正意义上的史诗作品。它完全按照希腊史诗的格式,它的人物出排,它的历史故事结构来写的,它的语言包括崇高感,都是史诗性的东西。我不喜欢寻常的东西,我喜欢天马行空式的,像一个中世纪的行吟诗人,这也许是我的气质吧,当然与我的阅历也有关。我在陕北长期生活、我在新疆草原生活,当我骑着马,在西域大地上,沿着额尔齐斯河,一路向西伯利亚走的时候,看着路两边的坟墓,我热泪盈眶,不管坟墓是哪个民族的,我都脱帽以礼,当作我祖先的坟墓,在那一刻我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
李 东:熟悉您的人都知道,生活中的您是非常谦逊和低调的,但对于写作就显得不那么“低调”了,有文章曾说,《最后一个匈奴》写完后您说中国文坛要发生大事了;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统万城》是应该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足以显示出您强大的自信,但这似乎和您的性格不相符,您是如何理解的?
高建群:陕西的经典前辈作家柳青说过,“搞文学只有别人动你的份,没有你动别人的份。”这就像农民担着鸡蛋进城一样,不敢碰任何人,你一旦碰了别人,鸡蛋打碎了你的家当就全没了。也是因为如此,我把别人都看得很高,我的工作室名字就叫“高看一眼工作室”。实际上就是让这个社会放过我,忽视我的存在,让我安心创作,看能不能写出一些有价值的、较为长久的东西。如果你整天盛气凌人、咄咄逼人地挑起事端,那就没有时间写作了。从我个人的秉性来说,尤其是到了60岁以后,我到了佛学所说的禅的境界,我追求一种更大的包容,我觉得人应该自我完善,更大的去包容世界,这是从做人的角度来说。从写文章来说,我是目空天下的,我敢说我写的长篇小说,应该是新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比如《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统万城》,包括之前的《六六镇》,尽管它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这不是我的错。我在一本书的后记里曾经写到,假如二百年后,当人们在尘封的书架上翻起我的书,比如《统万城》,他就会感叹,那个时代还是有那么几个思想深刻的作家的,千万不敢小觑那个时代!
之前我在太白山和常宁宫讲课时对年轻的作家说过,不要还没写就觉得自己不行,觉得只是来学习的,那不行。你们年轻作家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要有大格局意识,一张稿纸铺开,在我之前的文学史是一片空白,一切从零开始,从现在开始,从我开始,这样来写作,看自己能不能写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取乎其上,得乎其中。文学上必须这样,文学上如果是谦谦君子,你就不可能有大成就。
文学的崇高感已经丧失殆尽
李 东:您曾写过一篇题为《对中国文坛深深的失望——写给世纪告别》的文章,里面谈到“全盛的文学时代,须由三拨人构成,即一流的作家、一流的批评家和一流的读者,现在这三拨人都不怎么样。”十多年过去了,您的看法有改变吗?
高建群:没有任何改变,而且比起十多年前,文学更加走向堕落。文学被权贵绑架,被金钱绑架,被世俗文化绑架。文学的崇高感已经丧失殆尽了。
美国小说家海明威,当别人问他当时美国文坛谁是大师时,海明威长叹一口气,说,伟人们都已死去,我现在是和XX生活在一起。现在我们觉得文学还不错,关起门来自我陶醉,评个什么文学奖,但是文学的那种庄严感,那种恢弘气度,那种古典精神,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们不说和欧美文学比、和非洲比,就是和日本、印度、韩国这些我们近邻的国家比,也是输。我们的文学已经沦落到连中国足球都不如的境地了。
李 东:当时文章中您写到“我们没有好的评论家”,您如何看待文学批评?
高建群: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是一个火炬手,他能随时引导文学走向,当文学偏离为人生的主旨以后,他马上来矫正,向作家提出警告。典型的例子就是别林斯基,当果戈理写出《死灵魂》的第一部时,别林斯基在他的《现代人》杂志上宣告:俄罗斯一位天才作家诞生了,让我们做好接受他的思想准备。然后俄罗斯文学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巨匠果戈理诞生了。当许多年后,果戈理写出《死灵魂》第二部的时候,别林斯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我们的天才小说家,已经沦落为沙皇的一个帮凶、一个现行制度的帮凶,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他已经不是艺术家,而是成为艺术的敌人了。果戈理听到这话,哭了,他把他的《死魂灵》第二部付之一炬。
当然这一切都会改变。时代要发展,文学要发展,文学批评也必然会发生改变。
李 东:对于陕西文学的评论,众说纷纭,作为资深的省作协副主席,您如何评价当前陕西文学现状?又有什么建议或者期许?
高建群:我怀着满腔地期望,希望文坛新势力的崛起。我记得我在七八年前的那一次省作代会上,记者采访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么一段话:我们这一代人行将老去,这场宴席,将接待下一批食客。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希望年轻的一代能够成长起来。
我记得在太白山那个读书班上,当时在座的有很多有名的作家,年轻的作家四十多岁五十多岁,也很有成就的。但是我在会上不客气地说,比如有人采访问我,陕西作家在你们之后现在谁还有希望,我没有提到你们,你们有怨言。很多人我都话到嘴边了,我不敢提,为什么呢,我觉得你们身上还缺少点什么东西。缺少啥?后来我也在想,就是缺少一种大格局,一种文学的大格局,人生的大格局。如果有那一点,你们很快会就从卡的那个地方出来了。你们现在都是写个小说,写的还可以,可读性还不错,销量也不错,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样你就成功了?了不起了?不是的。大艺术家,他就像是狗熊从森林中一路踩过去,他就是不管哪个大树碰倒了,灌木碰倒了,他无所畏惧,他就一路走过去,像一个行吟诗人一路走过。你们缺少这种大气度。
咱们这些年轻作家的优点是,能够吃苦,特别能吃苦。有的人,就像那个寇挥,为了写作生活上省吃俭用,我听了很感动。在寇挥这样的作家面前,我说那些招摇撞骗的,招摇过市的那些人,他们应该脸红。寇挥这样的作家还不少,像高鸿这些都不错,包括杜文娟也在努力写作,一会儿跑到西藏,一会儿跑到高新区,这都是不错的。就说是,一定要像一个文化人那样活着,不要咱有点成绩了,给你一个小官员让你做着,你把你真的当做官了,不是的,官员根本不认可你,官员们只是把你们拿来当作点缀。他们根本不是,拿你来作同僚。总体来说,陕西作家还是很好的。陕西作家一个是能吃苦,再一个是有扎实的生活积累。我记得就是1991年5月23日,中国作协1991年的年会是在延安召开的,当时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山西作家马烽在会上说,我对山西的作家说过,你们要注意黄河这边的陕西作家,陕西作家比你们的生活底子更厚,更能够坐下来,所以大作品有可能在陕西出现,紧接着《最后一个匈奴》就出现了,接着《白鹿原》、《废都》、《八里情仇》、《热爱命运》都出现了。所以一定要有生活积累,这一点是陕西作家最可贵的东西,陕西的作家是很厚重的,很憨厚的,就是像牛一样耕耘。
柳青生前说过一句重要的话:有一天,写不出东西了,收起你的笔,做一个与世无害的好人,也算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柳青的这话,总是叫我时时警策,叫我永远夹着尾巴做人。
这两年我参加陕西省作协的活动多一些,主要原因是常常想到那些前辈作家对我的提携。柳青、胡采、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王丕祥等等。我常常想,前辈作家当年是怎么对待我的,我现在要以他们为榜样,对待后起的作家朋友。
我的文字有我的血在流淌
李 东:在“键盘写作”成为写作趋势的当下,“手稿写作”显得难能可贵。您还是一直坚持手稿写作吗?您对网络文学如何看待?
高建群:我有几次机会可以跟着老婆和儿子学习,可是当时忙于写作,就没有跟上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就是世界的另一半对我是漆黑的,我现在体会到这点。后来在儿子帮助下,他买了手写板,我用手来写,虽然慢一点,写长的不行,但可以用手写板来写短一点的。我可以发短信,我还有微博,我今早上就连发了两个微博,我早上一起来,我说:“古人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这意思就是说早晨我扛起锄头,扛起镢头上山劳动,晚上我回到家里,脱裤子睡觉,帝王的力量虽然强大,对我来说又有什么作用呢?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咱们各干各的事情。这一发,大家都说好,就是有这种感觉。
我的思维还是很活跃的,我的这种雄厚力量,这种知识积累,这种阅历,如果让我在网络上发起威来,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将来的话,大家可能在网络上发现一个力量出现,那么可能就是我。现在我还是手稿写作,就是写长篇,就是坐在那里,喝着茶,抽着烟,拿着笔就像在那里给人类写遗嘱那种感觉,那字写出来是我的字,不是新华字典的字,也不是时间上的字,也不是键盘上的字,我的字,每一个都有我的血在流淌。可能写短一点的东西我在网上,拿一个手写板。最好的是他们谁写的,我拿手写板在网上给他们改动。
最近咱们陕西做了一个“大美陕西”的专题片,我让他们传过来,在家里拿着手写板给改了一遍,那个出来反响是相当好的。省外宣办要出一个“丝绸之路”的书籍,我给他们写了一个前言,我觉得写的很棒,这个前言可以拿来放到课本里面当范文来读。
李 东:“键盘写作”的趋势化,让作家手稿显得尤为珍贵。近年来,网上不断爆出有人拍卖名家手稿的事情,引起轩然大波。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的手稿是如何保存和处理的?
高建群:我的手稿基本都还在我的家里。那一年,台湾来了一个拍卖商,想收走我的手稿,他想把“文学东征”几本书的手稿都收走,他来找我,谈价位谈得很高,想150万收走,我当时也没有给。后来现代文学馆,来了三次要我的手稿,我都没有给,我说我的写作是我的个人行为。后来他们要我的《大平原》的手稿,我说如果这个能获个什么奖的话,获奖结束后,颁完奖,我把我的手稿,还有我的四十幅《大平原》的插图举行个仪式,一块送给他们。后来我说你们也没有给我获什么奖,这也与你们无关,这是我个人写作,他们也没能拿走,现在还在我的文学馆展着。所以我的手稿基本上都在,我也不赞成拿去拍卖,如果你写小说想着手稿以后拿来拍卖,那样你的小说肯定是写不好的,而且别人会嘲笑你:你是没有吃的还是没有喝的?手稿对我来说就像老婆孩子一样珍贵,我不可能把自己老婆孩子拿到拍卖市场,头上插个草标去拍卖,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至于人死了以后,人们为了纪念你,办个什么慈善活动,把你手稿拿去拍卖,那是另外一回事。
李 东:前不久,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发微博,对某诗人“跑鲁奖”进行揭露,一时成为网上热门话题,您知道这件事吗?您如何看待当前文学评奖,又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获奖?
高建群: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很少获奖,好像有些人成了获奖专业户,只要有个奖,他就能获,我的话,很多奖我都不知道。我也不热衷评奖,而且我有一种担心,对评奖这件事本身的担心,每一次的评奖,都可能是对文学的一次深度伤害。评出来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然后说这就是当下中国文学的高度,这是值得怀疑的,真正的好作品被挤到圈外,又是一种伤害。
我和一个老作家谈过,他谈了一句重要的话,他在台上的时候不敢说,退下来后才给我说: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每况愈下,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评奖引起的。大家都是为评奖去的,然后就有成篇的作品,为时局服务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占了上风,大作品出不来。不光是文学评奖,还有其他艺术门类的,比如电影、戏剧等等各个方面。
方方我也算比较熟悉,但是她说“跑鲁奖”这事,我不太知道,也不关心,我不希望一些寻常小事来打搅我的清净世界,所以也没有必要去听。世界上所有发生的,都是应该发生的,有些人人家跑了,跑成了,一天招摇过市。他哄文学,文学也哄他,完了到最后,要不了十年八年,这个时代就把他遗忘了,他成为了笑柄。
这是一个愉快的下午。“高看一眼工作室”里,一壶茶、一支录音笔,聊文学、聊生活。
高老师以具有亲和力的陕西方言侃侃而谈,让我再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文学前辈对待生活的谦逊和对文学创作的大境界。
在陕西这片文学沃土,有一大批优秀文学创作者,更值得尊重的是,一些作家远离文坛浮华,“任凭外界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动”,静心创作,默默构筑着自己的文学殿堂。或许他们正在被发现,他们已经被发现。
责任编辑:阎 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