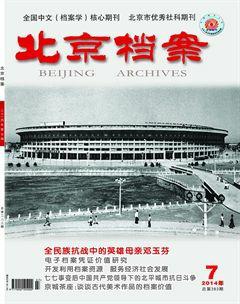我的“眷村”情
吉路
电视连续剧《原乡》的热播,让我想起那些曾经和仍然生活在“眷村”的台湾朋友们。
“一二三,到台湾,台湾有个阿里山,阿里山,有神木,我们一起回大陆。”这是在京投资台商说给我的一首儿歌,据说几十年间流传在台湾岛内。词作者无从考证,但其特征很明显:一是它的时代色彩很浓,估计当年初创是配合国民党的所谓“反攻大陆”而作。能流传日久,或因寄托了去台老兵的思乡之情;二是它的生命很长,伴随着那数以万计的“眷村子弟”长大成人。
所谓“眷村子弟”,泛指一九四九年前后随国民党去台军中眷属的第二三代,因为他们多生长在驻军的“眷村”而得名。当然,早期能成为“眷村子弟”的,一般是父亲位居军内中上层,因能携家眷随军而行的,必是有一定官阶的人。相反,这二十几年回北京探亲的去台“老兵”,因为离开家乡前多是十七八岁的农家子弟,不少当了所谓“十万青年十万兵”的“青年军”,四十年后归故里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台湾老兵”,有的孤身一人,有的在台娶妻,还有的“搭帮过日子”。
口述那首儿歌的台商也是一名“眷村子弟”,有这样出身的台商,其实不在少数。开放初期,他们主要是当台湾本土企业家的引路人或代表,来大陆考察投资环境,以后才办起自己的企业,逐渐发展成了“台商”。这位“眷村子弟”曾不无调侃地说:带头喊了几十年“反攻大陆”的那些大人物,明知道早已是不可能,却迟迟不肯面对现实、改变政策。没成想,我们这些子弟真是“一起回大陆”发展,陆续事业有成,不知道算不算“反攻大陆!”
“眷村”,原先是指一九四九年起至一九六〇年代台湾当局为安排被迫自大陆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眷属所辟建的房舍(包括接收日据时期的“眷村”)。岛内有统计,现今军列管公有眷村达五百三十座,若包含非军有及混住,则有八百七十九座,其中桃园县最多。
一九九八年夏天,我随演出团体到台湾交流时看到两处“眷村”。一处在台北市中心,比较早就被改造成新社区、建起小楼房。从外表看,和北京的多层居民楼没什么两样,每个单元也不大,基本上是两室一厅的规格,家居简朴,和北京市民的家居区别很小。我最欣赏的是,尽管楼不高却有电梯,还有地下汽车库,使得地面上干净利落。据说这个“眷村”改造时,正值一九九六年岛内“大选”。
也许是为了争取这部分国民党的“铁票”,原本回迁需交一笔高额费用的计划,改为免费回迁。不花钱的好事谁都乐意接受,但这些一心想回家、几代跟着蒋家父子的“眷村人”,是否真把票投给李登辉,可以想象得出。不过,听说一九九八年底选“台北市长”时,一些“眷村”老者走街串户,动员大家投马英九的票,不仅因为马英九代表国民党,而且因为马英九也是“眷村子弟”。我看到的另一处眷村在市区边缘,就是著名的“四四南村”,现在以“历史建筑”的方式被保留。
在“眷村”见到“眷村子弟”和他们的长辈。虽然人数不多,时间不长,但依然深深感受到他们所说的那种“两边不着地”的无名困惑。的确,他们在台湾被称为“外省人”,可是很多人“生于斯,长于斯”,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在大陆又被叫做“台湾同胞”,可是很多人几十年在“眷村”里生活,和当地老百姓往来有限,甚至连台湾方言只听得懂而讲不来。也许是这种半自闭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对台湾政治有很强冲击力的“眷村文化”,以及由此产生了独特的“眷村文学”。最具代表性的如:朱天心的小说《未了》,张大春的小说《牯岭街上的少年》,杨德昌导演的电影《牯岭街上的少年》,王伟忠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光阴的故事》,赖声川、王伟忠共同创作的舞台剧《宝岛一村》。
我还去了两户在“眷村”住过的殷实人家。他们经商多年,资产尚可,所居地段也不寻常,算得上“中产阶级”,但住房内的装修和布置,完全不同于台湾电视剧里的豪华场景,仅仅是典雅舒适而已。其中一个场景是我难以忘怀的。一对至今没有见过面的新婚小俩口,听长辈说打算让我到家里来,特意买了一只无色透明的玻璃花瓶,插进几支洁白美丽的百合,摆在客厅的茶几上,表示欢迎北京客人的到来。
此外,还有一家“眷村子弟”兄弟,本和我不相识。他们听朋友说我刚从北京来,拜托定要见上一面,因为北京是他的出生之地,所以我是他的尊贵客人。朋友对我说,你无论如何不能推,他们很有诚意的。说的也是,在台湾使我感受到这是不能用一般的“好客”解释清楚的。可能是他们身不由己、当时无法到大陆看一看、走一走,于是把接待大陆来的朋友作为情感寄托的所在。事前,朋友只告诉是和他的同学见见面、吃吃饭、聊聊天,结果聊起天让我非常惊讶——围桌而坐的十有六七互称“某将军”。我不便直接询问,但从年龄上推测,他们应多已退役。和他们坐在一起喝“金门高粱”,让我想起在“金门之战”中九死一生的表哥,是同胞弟兄用白酒擦遍他全身才救过来。表哥少年从军,待他来京看望老父亲时两鬓斑白。他和许多在台“外省人”一样,担心“台独”成气候,举家落户海外。与此同时,有些“眷村子弟”抱着不能让“台独”得逞的心态,从海外回到台湾、加入反“台独”的行列。
一晃多年没去台湾了,熟识的“眷村子弟”还和我保持着联系,经常在年节互道平安。最令人惊喜的是,二○一二年春节前,一位来京参加小儿子婚礼的“眷村子弟”,特意邀请我一同参加。
——以《台北人》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