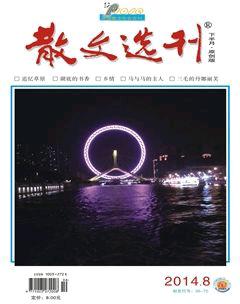椅子
2014-08-26 03:34吴昕孺
散文选刊·下半月 2014年8期
吴昕孺
椅子蹲在客厅墙角的阴影里,像一只落魄的鹰,忘记了天空。它忘记了自己消磨的岁月。年龄堆积在深厚的空虚里。那空虚宛如千年庭院高悬的匾额,给喧闹的客厅勾勒出一抹沧桑。上午九时,阳光从窗口跳进来,它板着面孔不予理会;中午十二时,暖风从门缝冲进来,它正襟危坐不予理会;下午五时,霞光从屋顶漏进来,它纹丝不动。岁月成功地雕塑了它,但它与流动的岁月无关。它只在晚上八点,月色不知从哪里渗入客厅时,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动,仿佛祖父临终前微弱的声息。
我收藏了它。它收藏了记忆。或者说,它被我和记忆同时收藏。
我牵着祖父的衣裾,奔跑在消亡的路上;而记忆举着时间的杯子,行走在复活途中。我和记忆谁是椅子真正的主人呢?
椅子蹲在客厅墙角的阴影里。阴影是它永恒的位置,它因此得以逃遁于其他表述之外,在语词之外,在牵挂之外,在谎言之外,在遗忘之外,也在地久天长之外。
它固执地,把那片阴影魔幻成时间的墙纸,魔幻成像天上云朵一样的东西。它固执地,在灰尘与蛛网的宏大叙事里,娶200年前一位女子的背影为妻。
责任编辑:黄艳秋
猜你喜欢
幼儿100(2023年35期)2023-09-22
作文小学中年级(2023年1期)2023-02-12
扬子江(2020年4期)2020-08-04
疯狂英语·新悦读(2019年12期)2020-01-06
汉语世界(The World of Chinese)(2019年2期)2019-04-19
作文与考试·小学低年级版(2017年24期)2017-12-14
时代青年(上半月)(2017年11期)2017-12-06
儿童与健康(幼儿教师参考)(2017年5期)2017-06-05
小学生导刊(2017年14期)2017-05-17
好孩子画报(2013年2期)2013-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