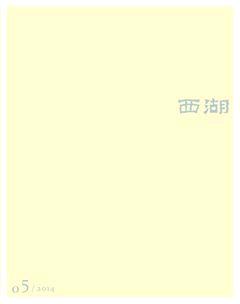医生手记
高众
中毒的婚姻
你想象不出一个人想了却自己的生命是需要多大的勇气。你我均不是当事者,无法体验这样选择让自己的生命提前终止是怎样的心理状态。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初春的时候,我在某驻军医院实习。北方的初春感觉不到那种春的气息,相反,甚至比隆冬还要让人感到寒冷。急诊科少有病人,带教老师将我一人放在门诊,自己窝在医生休息室。急诊科本来是不欢迎实习生的,因为实习生一般都笨手笨脚,帮不上实质性的忙,有时反而会帮倒忙;这与急诊那种紧张和风风火火的节奏自然格格不入。
我实习期在心肾内科待得久。心肾内科是抢救危重病人的一个重要科室,特别是心脏病的病人,抢救就是要快要急;在心肾内科待久了,我习惯急和快的工作环境,熟悉急重病人的抢救流程,所以我反而很受急诊科医生的欢迎。平时一旦有急诊病人出现,急诊科医生绝大多数情况也是找心肾内科的值班医生参与抢救,而我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值班医生的帮手。
那天晚上外面很冷,天上飘着雪花。我实习的这家医院位于北京北郊的农村,四周被庄稼地包围着,只有数条小路与外界连通;平时车就很少,这样的夜晚自然车就绝迹了,医院的院子里显得极其宁静。
没有病人,我坐在门诊室看书,因为实习考试临近了,这直接影响到我能否正常毕业。
晚上十点左右,也就是急诊科实习生的下班时间,我收拾好书本,就在脱白大衣时,外面汽车的马达声响起,由远及近。不一会,汽车临近急诊室,一个凄厉的男声在喊:“救我老婆……”我重新穿上白大衣,急速冲出去。一个男人背着一个女人冲入,护士们已打开急救室的门,带教老师也早已站在急救室。这一点,急救室的医生和护士总是让我佩服,平时没事时看起来似闲庭信步,一到这样的紧急时刻,动作快得让人吃惊。
患者躺在急救床上以后,护士飞快地给她扎上液体。这扎上液体在急诊中有个专用名词,叫“开通静脉通道”,是在第一时间将急救药物送入病人体内。带教老师简单地询问得知,这个女人因为和她丈夫吵架,一气之下喝下去半斤左右的“乐果”农药。当我们凑近病人时,一股浓烈的蒜臭味扑面而来,这种蒜臭味是典型的有机磷毒物的中毒表现。于是医生赶紧给她静脉注射解毒药物“阿托品”,但是似乎已经晚了,她的呼吸微弱到连听诊器都无法听见,只能看见她极尽所能张大的嘴唇在轻微地颤抖。瞳孔缩小本是有机磷农药中毒的重要体征,但是掀开她的眼皮发现她的瞳孔似乎在慢慢放大。之前心脏很有力地跳动,此时,心音慢慢变得遥远。
这样的情形,似乎病人很难从死亡线上挣扎复回,当时麻醉科、心肾内科、急诊科的所有值班医生似乎都无力回天了。
主持抢救的心肾内科主任一边指挥医生护士做心肺复苏抢救,一边安排高年资的医生出去和患者家属,也就是她的丈夫谈病情。在当时,说谈病情倒不如说是交代后事。因为象征着生命的四大体征呼吸、心率、脉搏、血压,病人已经失去或者即将失去。这样突如其来的死亡很显然她的爱人猝不及防,不一会,门外传来极其悲惨和绝望的哭声。说实话,这是我八年的从医生涯中所听过的最绝望最毛骨悚然的哭,常人很难想象此时这个男人是怎样的绝望和悲伤。哭声很快停止,哀求声悲伤地响起,求你了啊医生,怎么也得想办法……
真的是无力回天了,心肾内科主任说,小王你来做心肺复苏。此刻,我心里明白,这个病人在医生们极其小声的讨论声中要放弃被抢救了,不然不会让我这个实习生上手。我很清楚,据以往的经验,一旦让实习生上手,就意味着这位病人最后的价值只在于让实习生通过在真实的人体上找到实际的抢救感受,来增长实习生的临床经验。
不可多得的实习机会,我很珍惜。于是我根据书本上的提示,不厌其烦地做心脏按压,其他医生或是默默地看着我做,或是盯着心电监护的显示屏。
外面的哭声和哀求声交替着传入我的耳朵,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听这样的声音。当我累得筋疲力尽汗流浃背,就快放弃的时候,突然有个医生发现心电监护的屏幕显示出室性心律,于是大家又兴奋起来。虽然室性心律是一种无效心率,意思是这种心率是不能正常地泵出血液的,但是出现室性心律意味着还有使生命复回的希望,尽管这希望渺茫。
出现了室性心律,接下来就是电击,只有电击才可以实现有效逆转,让它从室性心律转变为可以让心脏正常工作的窦性心律。很显然,这一步在别人身上可能会轻而易举,但是对一位重度有机磷药物中毒的患者来说,在她身上何其艰难。因为有机磷中毒的发病机理就是使连通神经和肌肉的乙酰胆碱失能,换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掐断了两者之间的电话线,让它们的信号无法连通,这样,受着神经指挥的肌肉因为失去与上级的联系而接收不到指令,就会变成一坨死肉,一坨死肉显然不会再有生理功能。
七八次电击之后,依然没有反应,于是除颤器又交到我手中,意味着增长临床经验的时刻又到来了。我清楚记得当时除颤电击的次数,在我的手上,一共电击13次。13这个数字被西方人认为是最不吉祥最倒霉的数字,此时却成了这名病人的救命稻草;也就是在第十三次,病人的室性心律终于转变成窦性心律。
心脏的复跳无疑使所有人深受鼓舞,大家抢救的积极性明显高涨,刚才抢救室内漫不经心的气氛立即重回正轨、变得有条不紊。有医生出抢救室的门再次与其家属,也就是她丈夫交待病情,于是外面变得安静起来。
心脏的复跳固然是生命的希望所在,但这只是黎明前的一丝一缕曙光,离病人真正脱离生命危险还有很长的路走。因为呼吸还没有恢复,血压只是靠药物维持,此时的生命如此脆弱,如嫩豆腐一般一碰就碎。然而,毕竟是看到一点生的希望。
这样的危重病人必须依靠呼吸机帮助呼吸,必须在诸多生命监测的机器下维持最基本的生命体征,于是很快便转入重症监护病房。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得到最好的医疗仪器的保障。
病人转入重症监护病房时已是凌晨,大家都疲倦不堪。心肾内科主任说,小王还是你来吧,你最熟悉病情。于是我和另外三位护士就此住进重症监护病房,我也是平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生命的坚持和韧劲。
那几天的雪在北京北郊的农村出乎寻常地大,一天工夫,地上就积了厚厚的一层。外面的风在重症监护病房的窗户缝隙里一晃而过,发出凄厉的叫声,特别是在夜晚,这样的风声足以使人毛骨悚然。
重症病房出奇地安静,因为这里绝不允许家属探望;家属最多只是隔着玻璃向病房里匆匆看上两眼,便会很快被医生或护士劝退。这倒绝不是医务人员不近人情,只是因为外人的进入会带进细菌、病毒等各种微生物。正常的人体有免疫力,这些微生物不会产生不良后果,但是对重症患者来说,他们的免疫能力早已被自身的疾病所摧毁而变得弱不禁风,微生物漫不经心的侵入会造成严重的感染,这种感染将会危及病人的生命。
这样出奇的安静,外面的凄风,再加上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的病人,几下合成一种恐怖的气氛弥漫在重症监护病房。男人也许不会怕,但是这样的氛围让年轻的女护士感到了恐慌,恐慌到夜间不敢上厕所、不敢单独睡觉的程度。
有个护士结婚时间不长,那几天正好跟爱人闹别扭,所以她不想回家,于是不停地和别人换班。正因为此,在重症监护病房抢救这名患者的八天,我是和她待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人。
重症监护病房没有医生单独的房间,也就没有单独的床。现在的问题是这名病人时刻离不开医生的照看,这医生也就是我。因为在救治过程中,医嘱是根据病情随时更改的。那时我是实习生,没有处方权,按医疗技术常规,我没有单独给病人定医嘱的权力,我的所有医嘱都必须经过我的带教老师、也就是心肾内科主任的签字认可,护士才能执行;不然的话,我下的医嘱谁要执行,谁就承担一切医疗后果。但是在晚上,没有带教老师在场的话,敢坚决执行我的医嘱的,就是这位跟她爱人闹别扭的护士,她的理由只是“负责任的男人是可信的”。也许我所做的一切是负责任的男人的体现。这种赌气式的做法,严重违背了医疗护理技术的常规;对我来说,则是明显超越了实习医生职责的范畴。
男人是否负责任的观点严重影响到这位护士对其他男人的看法。她对患者的丈夫恨之入骨,在她看来,能将自己的女人逼到自尽的份上,这样的男人恶劣到什么程度?
患者病情稍微稳定一点时,也就是我休息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完全视病人的病情而定。我休息的地点在护士休息室,幸好休息室有两张床,于是我睡一张,另一张床用于几名护士值班时轮流休息。由于跟爱人闹别扭的护士经常值班,由于救治病人耗费大量的精力和体力,休息不可避免,我和她经常同处一室也就成了必然。
也许是我的敬业博得她的好感,即使同处一室,她也不对我过多防范。其实也没什么需要防范的,困倦的来临无法阻挡,经常恨不得站着就能睡着,不可能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心思,或者说根本不可能不怀好意。可就是在如此的困倦中,这位护士会和我唠叨她婚姻的不如意。说实话,当时关于婚姻这个话题,对我这个还没对象的学生来说,她简直就是对牛弹琴。
不过也有好处,好处在于女人之间的同病相怜,她对躺在病床上还没有自主呼吸的女人格外关照。这样的同病相怜说实话让我有点不寒而栗,心里老是在思考婚姻是否真的这样可怕,就像这个女人一样,中毒如此之深。
随后的相处中,我发现跟丈夫闹别扭的护士与躺在病床上女人跟其丈夫吵架的原因竟如此一致,皆因为丈夫和别的女人在一起谈笑风生而醋意大发,而区别就在于一个喝下农药、一个赌气不愿回家。
空暇时间,我和女病人的丈夫聊天,他显得很无辜:就是在一起聊天而已,真的没有实质性接触。他说完叹口气,以过来人的身份拍着我的肩膀说,唉,兄弟,你还年轻,你不懂女人。
女病人的丈夫显然希望我们更用心地为其女人救治,也就极尽奉承和溢美之词,我倒是很受用,但是这些却更引起心情不爽的护士反感,对他训斥是常事;就是在这样的厉声训斥中,他还是每天将重症监护病房的室外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任劳任怨。他的工作虽然减轻了护士们的工作强度,但是好像并没有人领情,但他脸上依然写满了献媚和卑微。有时我走过他的身边,轻轻拍拍他的背,作为同是男人的理解和安慰;他很感激。
重症监护病房就是在这样奇怪的气氛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终于在第八天的早晨,女患者恢复了自主呼吸,并很快清醒过来。当她抬起头四处找寻的时候,我知道,她在寻找他的爱人。我赶紧出门叫醒睡在楼道里的她丈夫,她丈夫得到她清醒的消息惊喜异常,赶紧起身,几乎扑向病床。夫妻俩紧紧相拥,谁也没说一句话,双双泪如雨下。那位闹别扭的护士同样在一旁泪雨滂沱。
许多年过去,我在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之后,与我现在的爱人牵手走在一起。时至今日,重症监护病房的场景我一直铭记心中。那八天难忘的生活,给我上了生动的婚姻一课,尽管那时我还在懵懂中,对婚姻一无所知。提前教育也许会让人更加印象深刻,我一直记得那服毒的女人和卑微的男子,虽然现在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生活如何,但我想那对劫后余生的年轻夫妻应该早就明白,婚姻的中毒并不可怕,理解和信任也许是最好的解药,无需更多语言。
血色的红
我有一天突然莫名其妙想到千刀万剐这个词语。不知道我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个词,我想它究竟是出自何人之口,又来自何方?我不知道将千刀万剐这个词安放在别人头上的时候,是怀着怎样的愤怒和仇恨?我实在想不出。但是当我想到这个词语的一刹那,有一种冰冷和阴森的情绪让我的后背发凉,同时我还想起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冰冷铁青的脸庞,和她脸上冰冷的黯然的表情。
十五年前的冬天,那时我作为京郊某医院的实习生,一个很冷的早晨,和另外两个同学去妇产科报到。妇产科位于住院部主楼右侧副楼的第三层;一道门将妇产科与公共走道隔绝,一块很郑重很严肃的牌子挂在门的左侧,上面写道:男士莫入。
北方的冬天冷极了,头天晚上下了一层厚厚的雪。早晨的太阳被白雪反射出刺眼的光,被刺骨的寒风裹挟,冰冷地照射到人身上,更显得寒意逼人。我们从寒冷中走过,推开原本“男士莫入”的门,很快被一股暖意包围;随暖意一起包围全身的是浓浓的消毒水刺鼻的气味,和一丝淡淡的血腥味。
在医生办公室,妇产科主任用冷冷的眼光打量着站在她面前的三个实习生,我们三个像是自由市场待价而沽的商品。良久,她说我,你跟朱主任吧。
妇产科主任站起来,走到门口,歪着头朝走廊里面的房间喊,朱啊朱啊,这高个子的学生就归你了。朱主任是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一位精瘦、风风火火、语速奇快的小老太太。她并不是什么行政主任,在医院,只要职称到了高级,也就是副主任医师这一级别,就和科主任称呼一样。不是别的,可能是医生这个称呼没有主任的称呼好听;主任的位置象征着权威,特别是医疗技术上的不容质疑。当然,也有可能是国人自古以来的官本位思想在作祟吧。
朱主任是一个性格特别直爽的小老太太,将大半生都奉献给了妇产科。也许是长期和女性生殖器官打交道的原因,她说话从来不避讳生殖器。比如说自己发烧,她会很自然地加上“连阴道都感到揪着痛”这样让别人听起来很难为情的话来形容自己身上的不适症状。不过这样的直爽,也显得这位小老太太很可爱。这是后话。
她说大个子你过来吧,声音尖利、沧桑、急速。我顺着声音沿着过道走过去,检查室的门虚掩着。我敲门,她说进来,同样语速极快,只是稍微有意压低了音量。
我确实慌乱,因为我从没见过女人真实的裸露的身体,而在妇产科,只要是进来的病人,都会露出私处让医生检查。起初到实习医院,医院为我们准备的实习计划一发下来,大家都争相传阅。异性相吸是千百年来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妇产科无疑最吸引男生的眼球。一群年轻的男学生很显然因为好奇而不自觉践踏了职业的神圣庄严,总是无数次猜想会在妇产科看到什么,每次猜想,内心如同初次约会那般慌张,虽然这仅仅是可以满足自己对异性身体私密部位的好奇心而已。
推开门,朱主任背对着门,也就是背对着我,配合护士在器械台前准备检查器具。她的背后,也就是我的眼前,横着一张检查床。整个房间也就是这样的陈设了,简单、明了,简单明了的陈设在白色的背景下更能显示出一种让人肃穆的森严。我一只脚踏入,便听见一声近似凄厉的喊,男医生出去,我不要男医生检查!是我左侧发出的声音,我侧过头一看,一个年轻的姑娘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俯着身子,仰着头瞪着我。
这样的尖叫声显然让我感到紧张和胆怯,虽然厚厚的口罩能遮掩我绝大部分的面孔、掩藏我不安的表情,但是脚还是不由自主收了回去,并随手将门带上。朱主任当然知道是我,说你进来。我只得又推门进去。朱主任看我一眼,透过镜片,眼睛眯了一下。她的面容被口罩遮挡得严严实实,这一眯,算是笑了一下。这一笑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紧张和胆怯。她对那个姑娘说,医生不分男女,他是我学生,也是我助手,你要是不让他进来,我也没法给你检查了,再说我一个人怎么给你检查?
我很感谢朱主任,就是因为她说我是她助手。这样说能彻底掩盖我医学知识的不足和临床经验的空白。作为实习生,我面对病人时,需要一些伪装的尊严。医学生和医生在医疗技术上存在天壤之别,不管是什么病人都不会放心到让连医生资格都没有的学生做检查治疗的程度。而助手不一样,能给一位有高级职称的医生做助手,很显然已拥有足够的医疗技术准备。
那位姑娘看着我,脸通红,这红色在白色为主色的检查室显得格外明显。我很明白,这样的红脸有羞涩的成分,更多的是恼怒和不满。也许是大大的口罩彻底遮住了我的面孔,也遮住了我的慌乱与尴尬,示人的只剩下两只眼睛;幸好眼睛不会变色,因此外人看来,我显得平静从容。
也许是检查室内格外温暖,也许是我内心备受煎熬,我承认,面对即将脱去衣服的年轻漂亮的女子,我的意志受到了极大的考验。朱主任抬头看了看我,随手递给我一块无菌纱布,朝我使了个眼色,说过来,看看窗户,擦擦脸;又低声说,不管是男病人还是女病人躺在手术台上只是人,没有性别之分。很显然,她完全洞穿了我的内心,脱去白色的口罩包裹,我一定无地自容。
女子开始脱衣,犹豫、缓慢并且不断看着我。她如此眼神看我,我显得比她还不安,于是我扭过头,背对着她,我的身后瑟瑟作响。
朱主任说我,你来站这边,指了指她身体的右侧;然后指挥女子躺下、将双脚抬起、放在妇科检查床尾特制的不锈钢托上,女子的生殖器便充分暴露。
朱主任检查完后,对我说,看样子不到六十天呢,你过来检查看看。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明知故问,很随意地对我说。这样的发问是让我动手检查最好的理由,目的并不是让我这个还没入门的学生对资深的副主任医师下的定论做肯定或否定的验证,而是为一个男学生给年轻女子做妇科检查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我戴好手套,她对我说“双合诊”。双合诊是妇科一个诊断手法的名称,指一只手的两个手指从阴道进入,顶住子宫颈后壁,另一只手压在脐下盆腔的位置,这样来探测子宫的大小。这完全是个经验检查,没有客观指标对应,对一个还没走出校门的医学生我来说,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因此茫然无知,但我又不得不装腔作势。我在检查的时候,朱主任故意和女子说,你再算算月经期。女子听她这么一说也很茫然,说我算确实是了。我知道她明知故问,是对让我学习双合诊检查所寻借口的进一步阐释。朱主任又说,可以用药物流产的。女子坚决说不,不愿让它多待一天。女子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黯然而坚定。朱主任说好吧,准备一下,通知你爱人,下午手术。
从女子黯然而坚定的眼神中,我敢确信她没有爱人,也就是没有结婚;虽然她看上去年龄很小,但我相信确实有个男人曾走进她的内心。
窗外的雪不再下,天气依旧寒冷,风吹得树枝上的雪胡乱飞舞,树木重新露出赤裸裸暗灰的老枝。我的身后依旧瑟瑟作响,女子在穿衣,而我的心却在窗外,我承认我是多愁善感的男人。
中午我坐在医生办公室,一缕光线透过窗户照在身边,让我感到一丝温暖。门外一角静悄悄站着一个中年男人,我招招手,说进来吧。他脱下大衣,挺着肚子站在我面前。我说你是×床的亲属?他说是,我说你签字吧。他看了看手术知情同意书,只瞄一眼,就飞快地签上他的名字,潦草得没法认清。我说能认真点么?至少让我知道这字是你签的吧。他说小医生事真多,很不耐烦地重新签上名字。
女子如上午那样姿势重新躺在妇科检查床上,护士在准备手术器械。冰冷的不锈钢器械在搬动时相互撞击,发出刺耳的声响。朱主任站在女子的身边,问:决定不要了?可要想好了,毕竟是一个生命。女子显然显得不耐烦,说坚决不要。朱主任又说不要害怕,不要怕疼,女人就是这样,这样的手术台大都上过。她轻描淡写的说话很显然安慰不了女子内心的悲壮与恐慌,她的泪无声无息地流。女人一旦流泪,浑身便软了,变得柔弱而让人爱怜。
多少事都是这样,以激情与幸福开始,而以黯然与悲伤结束?医生您轻点,女子一边啜泣一边央求,无助得如同一头失去抵抗任人宰割的羔羊。朱主任看了她一眼,说没事,没那么疼,忍着点就行了,然后带上手套,朝着女子的双腿之间坐下。
无影灯的光束直射在女子的生殖器上,男女交欢的器具变成冷冰冰的物体,窥阴器将阴道扩张成不设防的走廊,长长手柄的刮匙顺势而入,插进子宫,短暂地轻轻进出;女子便扭动着身躯,汗水便混着泪水沿着面颊而下。
血和混着血的物质在刮匙的作用下沿着窥阴器的缝隙往下流,女子身下的床单便出现一片血色,如盛开的牡丹,异常鲜艳。渐渐鲜血向周围扩展,牡丹不见了,一大片的红,血色的红。刮了一会,朱主任让我接上负压吸引器,吸引头一插入子宫,负压吸引器便轰然作响,连接的透明的橡皮管瞬间被血和血色的物质充满;血和血色的物质快速流动,最终流入玻璃瓶中。
朱主任看了一眼玻璃瓶,停止了吸引,说王医生你来——王医生就是我——又说你刮,感觉子宫壁不光滑就算是刮干净了。说刮,其实就是刮除子宫增生的用于孕育生命的黏膜;清除了生命赖以生存的土壤,生命也就不复存在,连残留的希望都不再有。
一个也许本身就不应该到来的生命,在孕育之初就被这样一点一点用千刀万剐的方式无情摧毁。在我的老师,这位副主任医师摧毁这个小生命的同时,我从女子满是汗水和泪水的脸上分明看到了掩饰不住的愤怒与悲哀。
曾经梦中美妙的异性身体,我却不是在美妙的意境中接触,因此沉重与血腥一直是我记忆中的主题。玻璃瓶中的血液和残破的组织确实刺痛了我。生命从开始到结束,这个过程本来充满亮色,而它在还没有真正显露出生命力量的时刻,就被它的同类人为中止;像本来是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因为指挥的原因,在乐器刚发出声响时就被叫停;还没有接受观众的鼓掌与欢呼,曲未奏响已终了,人未聚齐便散去。
女子脸色由红润变成蜡黄,手术停止时她的身体也停止扭动。我扶起她,她整个身子便靠在我身上。护士替她穿好衣服后,我搀着她走进病房,让她躺在床上;问了下亲属在哪,没有回应,再环顾四周,没有人影。我明白那个中年男子如悄无声息地来一样,早就悄无声息地消失。
术后两小时,接近傍晚时分,朱主任带着我查房,问女子恢复得怎样,可以住院再观察的。病人脸色铁青、冷淡,很自然排斥我们的存在,声音很低沉,说不了,我要回去;然后默默下床,穿好衣服,再套上她那件红色的羽绒服,出门,下楼。
窗外本来银装素裹的大地,被夕阳染成红色;远远地,分不清哪是道路哪是田野,两排树之间应该便是路。女子的红色羽绒服在医院大门外停车场的公共汽车站牌前格外耀眼,一个人在寒风中飘摇;与之相伴的是,被夕阳染成红色的雪。目光所及之处,全是冰冷的红、血色的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