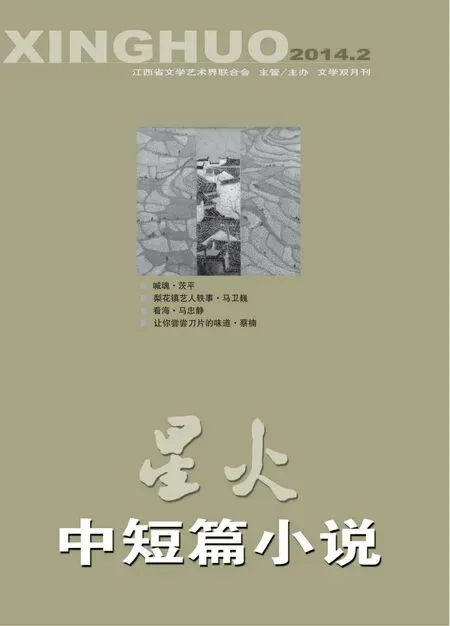园丁(短篇小说)
□王明明
文珍在阳台修剪那盆绿萝,那是最原始的一盆,跟远子一个年纪了。当初远子还在文珍肚子里孕育,也就是文珍和老公刚搬到新房的时候,她听说放几盆这种植物在新房里,能净化空气,还能去甲醛,于是在搬进新房的第二天,她就去花卉市场买了几盆。如今,只剩其中的一盆枝繁叶茂,其余的早已寿终正寝。可这枝繁叶茂的一盆竟能不断繁衍着,续接着生命。文珍上网查阅资料,请教了一些朋友后,决定将那些枝桠剪下、移植出来,有的被她栽进了花盆里,最近的一批她则干脆把它们培植在水中。她从网上选购了形形色色、晶莹剔透的玻璃杯,然后一个枝桠一个枝桠地小心将它们放进水杯里,在水面上用一块泡沫固定住,然后她把最原始的那盆和这些被移植出来的新生命统一摆在阳台左边那款她悉心选购的塑钢花架上。一片春意盎然。
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最先关照的就是这一片被浓绿堆满的墙。文珍拿着剪刀,边剪边数,整整十八盆。她心满意足。
远子从她身后闪了过去,抱着个篮球,头也不回地往房门口窜去。
站住!文珍喝止他,干什么去?
我约了同学打篮球。远子说。
文珍有些扫兴,厌恶之情顷刻浮现满整张脸。她心里嘀咕,又是篮球,他怎么会这么热衷于篮球?多么粗野的爱好,撕扯、拼抢、进攻……没一项是她喜欢的。况且,多么庸俗!对,是庸俗,因为喜欢篮球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几乎所有的男同事都喜欢,远子他爸也喜欢。他们不仅喜欢篮球,还喜欢抽烟喝酒,喜欢应酬。在文珍看来,喜欢篮球似乎和喜欢抽烟喝酒一个样,没点个性。她想不通,实在是想不通,她的儿子,怎么也会喜欢篮球呢?
钢琴练好了吗?文珍质问远子。
我刚练了一会儿,我下午,噢,不,下午要去培训班,我晚上,晚上回来补还不行吗?见文珍面露难色,远子干脆晃动着身子,撒娇哀求起她来,今天是星期六,妈——
她没办法赞同他,只能默许,她也知道今天是星期六,况且星期一就是远子的生日了,玩一会就玩一会吧。可她仍旧像是被什么东西推动着似的,停不下来,问,你刚才练了琴吗?我怎么没听到。
当然!远子肯定地说,我弹了《月光曲》还弹了《我和你》,你没听到?
文珍想了想,确乎没听到。
那你一定是走神了。远子说。
或许吧。从早饭过后,文珍就一直在摆弄这几盆绿萝,许是真没注意到吧!她心里却犯着嘀咕,那么大的钢琴声从书房传来,她会听不到?不过天天如此,那么被她忽略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她心烦的时候,不是也很烦他弹个没完嘛。有几次儿子弹得好好的,应该说弹得非常好,可她听着就是烦,可能因为她在单位里又受了领导的批评、受了同事的气,甚至仅仅是因为她在厨房里打碎了一只碗。她总是很容易心烦的。可每次她都得忍着,烦也不能打断他,她知道儿子远子正朝着她所期望的那条艺术人生之路迈进。远子马上要考初中了,他一定会考上全市最好的那所艺术初中的。那里不仅应试教育搞得好,艺术氛围也浓厚,只要进了那所学校,初中、高中一路读下来,考上顶尖的艺术高校,以后准能成为一名艺术人才,钢琴家?歌唱家?演员?导演?作家?编剧?一切都有可能。文珍这么一想,就如同看到了自己的那个梦,它就像鱼缸里的一条鱼,触手可及,可看上去总是影影绰绰的。
当然,也不能排除远子在撒谎。这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以前,他对她可是说一不二的,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对她总是劲儿劲儿的,她让他往东,他偏往西。就说这孩子打扮打扮多好,穿个休闲小西装、带个小眼睛、留个锅盖头最适合他了,就像哈利波特一样。可他现在整天就爱穿着脏兮兮的球衣球鞋,戴隐形眼镜,还把皮肤晒得黝黑。最让文珍受不了的是,他竟然愈发壮了,像他爸爸一样朝着五大三粗的方向发展,哪里像个文质彬彬的学生样儿?想到这些,文珍难免有些失落。特别是想到她生了他,他却有可能在欺骗她,文珍心里就不是个滋味。
远子出生时,文珍三十岁了。三十岁,是文珍向她的梦想奋力一搏的时候,这种搏多少有点垂死挣扎、回光返照的意思。可就在这个时候,远子来了。文珍开始不想要这个孩子,因为她觉得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在追梦,她渴望成为一名一线作家,所以这些年来,文珍坐在冷板凳上埋头苦写着,竟都忘了时间的存在。父母劝她,姑娘啊,你听句劝吧,你也不小了,三十,都是高龄产妇了。现在不要(孩子)?怕到你想要的时候都难了……
这一劝,着实让文珍心里一惊,自己怎么就三十了呢?爸妈说得也在理,她不是不喜欢孩子,她甚至挺喜欢孩子,她只是不想这么早要。可她又扪心自问,还早吗?她的梦想之路上似乎还有着层层迷雾,让她看不清路究竟还有多久多远,难道真的要等她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后再考虑孩子吗?文珍犹豫了。
犹豫过后,文珍决定生下远子。她想,孩子就是自己的动力,她完全可以跟孩子一起追梦嘛!老公她是指望不上了,她跟他就像两艘船上的人,老公不拉她后腿、不干涉她,她已经心满意足。那就干脆指望孩子,起码这样,她能不那么孤独。
远子就在她的同意下,出生了。第一次,她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文珍有点小小的骄傲。
远子出生在二○○一年九月九日,文珍知道九月九日是俄国伟大作家托尔斯泰的生日,又是新世纪的第一年,一定是有寓意的,寓意着远子很可能成为新世纪的一位伟大作家,享誉全球。这么一想,文珍就难掩心中的喜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她念大学那会儿读过,准确地说她并未真正将这本大书读进去,但是教授他们外国文学的老师多次强调读书的重要性,特别是阅读经典作品的重要性,那她怎么能不读呢?如果不读,等到课堂上同学们讨论的时候,她就只能哑口无言。所以,文珍利用了半个学期加一个暑假,终于把从图书馆借来的三卷本厚厚的 《战争与和平》啃完了。啃完后她发现,好像还是谈论不出什么,因为书里写的离她的生活实在是太遥远了,那么多字,她看着睡着了,醒了再看,看到后面就忘了前面。
她却忘不掉远子被老公从产房抱出来的样子。那时,她早已精疲力竭地被护士推回了病房,睡了过去。她是在睡了半小时后,被耳旁嘈杂的说话声吵醒的。
老公把孩子抱在怀里给她看,文珍,你看,这是我们的儿子,是你给我生的儿子,你太棒了。说着,老公不顾周围人,在她额头轻吻了一下。身旁的公公婆婆、孩子的舅舅舅妈和临床的产妇们都笑了。文珍看着丈夫怀中的婴儿,小脸红扑扑、皮肤皱巴巴的,湿漉漉的头发黏在头皮上结了一块脏兮兮的血疤,这样子实在不怎么好看,活像一个小老头。可他太大了,比她想象的大得多,医生说有八斤吶!文珍想,这么个大东西,是从她子宫里出来的?顺着阴道出来的?她怎么都不敢想。
身旁的人开始七嘴八舌,他们说孩子长得像老公,不像她。文珍心里听着老大不高兴,自己生的孩子怎么会不像她呢?婆婆说像,怎么不像,脸蛋像他妈。文珍伏起身看了看,脸蛋确实像自己,胖乎乎的圆脸向外鼓鼓着。婆婆本是好心,可文珍不领情,偏偏不像点好的。文珍在心里嘀咕着,若有所失。
从头到脚数下去,文珍最不满意的就是自己的胖脸。她不知哪来的观念,总觉得一位女作家、一个知性女子,就应该是骨感、瘦削的,具体到脸上,那就应该是瘦削的尖脸。这种脸,配上长发,才叫美,才叫好看,往阳光下一坐,端上一杯咖啡,那本身就是一段讲得出口的生活。
可自己偏偏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往这方面发展。瘦脸针老公不让她打,她就在头发上做文章,把头烫成了大波浪,蓬松着,两侧各遮去一半的脸,看上去效果立竿见影;远子刚出满月,她又开始减肥,保持身材。可就是再努力,她也回不到生孩子之前的模样,她对着镜子照,无论是肩膀还是腰腹,她的骨架仿佛被撑开了,回是回不去了。于是她就只好在着装上下文章。那段时间,文艺圈里的女人们都流行穿大裙摆的裙子,流行蝙蝠衫、灯笼裤,她也跟风买来一股脑往自己身上套。这一套不要紧,她发现自己还挺适合这种着装风格,就买了很多套换着穿,一穿就是十多年。
她不仅自己这么穿,还给远子搭配着。老公是个不讲究穿戴的粗人,儿子可不能像他。于是,自打远子能穿上衣服、帽子、鞋子时起,这一切都是文珍操办。她给远子剪和年画上捧着金鱼的那个胖娃娃一样的发型,剪过锅盖头,还扎过小辫子,她给远子穿过中山装,穿过长袍,还穿过跟她一样的裤裙。这一切,都被她的相机记录了下来。
现在,作为家庭主妇的文珍,时不时就会拿出以前的相册翻看,那里面不仅有远子从小到大的照片,还有文珍作为一个作家,起码是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的美好记忆。
三十五岁的时候,文珍发现自己的梦想破灭了。
究其原因,导火索无疑就是某次文学采风活动。只是文珍不知道梦想破灭究竟是一个循序渐进、质变到量变的过程,还是顷刻间的土崩瓦解。
那是文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文学活动。她清楚地记得,那个黄昏,她接到那个电话时,正在菜市场跟一个面目狰狞的小贩讨价还价。当她听到电话那头的邀请时,她急忙丢下钱,不用找了不用找了,然后第一时间逃离了那块脏乱之地。当时,激动和紧张的情绪在文珍身体的每一滴血液里游走,自己窝在这么个小县城写了十几年,写到儿子都上小学了,总算被领导发现了。文珍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酸楚。即便七年后的现在,每每想起,文珍都能把当时的心情体味得丝丝入扣。
为了那次会,文珍把自己最新完成的小说《园丁》改了又改,竭尽所能改到她心中的完美。但从踏上统一往采风地的汽车那刻起,她的心就宛如一片微风拂过的湖,总是颤颤巍巍的。
会议组织者刘秘书一上车,就开玩笑说,昨晚是哪个住我隔壁啊?好家伙,聊文学聊到凌晨三点,这把我困的。
车上众人你盯我我盯你笑成一团,文珍却谁也不敢看,聊文学能聊到半夜三点?有什么可聊的呢?文珍想都不敢想,她的心顿时有些凌乱。漫长的旅途,刘秘书给大家找到了打发时间的项目,先是轮番自我介绍,接着又是发挥各自特长的节目表演。无论哪一项,那都是考验人嘴皮子功夫的,这对文珍来说,实在是有难度,她就一个人窝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带上耳机,看着窗外。
看,一个七十年代末,比自己小了快十岁的小妹妹M走到了车前,拿起了话筒讲了起来。她才二十出头,竟然就已经上了两次文学界顶级的选刊,她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目前正跟着享誉国内外的一位作家从事影视剧本创作。
瞧,那个同样七五后的小伙子,身着一身中山装,米白色的长围巾从他的两肩倾泻下来,十足的民国诗人范儿,却把一首辛弃疾的词用颇具古曲的唱腔唱了出来,迷倒了车上众人。这个小弟高中就开始写诗,如今已经在国内一线诗歌刊物上发表了几千行诗,出了两本诗集,其中一本还获了一项诗歌奖。
……
文珍越听就越有些低落,在这群人里,自己年龄最大,却成绩平平,她就像角落里一堆不起眼的枯草,只能暗自悲伤。这也罢了,更重要的是,那些弟弟妹妹跟领导频频打着招呼,看得出人家早已熟识。文珍隐约觉察自己似乎就不该出来参加这么一个会议。她把自己的那种心情定义为忐忑。让她怎么形容呢?忐忑应该是心脏的节奏,这种情绪一定能在生理学上找出某种对应的解释,比如是心脏供血出现的一种什么情况之类的。她发现能用来形容忐忑这个词的都是些方言俚语,比如空落落,比如七上八下,真的就是那样,她整个心脏都提在半空中,落不了地了。
不正是这样吗?自己就是方言俚语、下里巴人,人家那才叫阳春白雪。文珍想到了自己伺候远子的这五年,她的定位就应该是个家庭主妇,是位母亲,压根不该梦想成为一个作家,不是吗?她这么想着,看着车窗外的植物,泪眼迷离。
改稿会请来了北京的几位专家,有她崇拜的N,可是N却并不知道她。不仅不知道她文珍,她文珍好像连崇拜N的资格都没有了。
等到次日晚上举办文学沙龙时,文珍的自卑变得无以复加。沙龙是从几个电影片段和音乐片段引出,谈的是“文学与人生”、“我为什么写作”这样的话题。那几个电影,文珍没看过;那几段音乐,文珍也没听过。对那几段音乐,她没有跟其他人一样感同身受。主持人介绍那些音乐时,几乎流出眼泪,文珍却一点感觉也没有,她只知道满大街放得叮当响的情啊爱啊的,对这些民族、古曲却没啥感觉。等到谈论文学与人生、谈论写作时,其他人上来都是引经据典,要么就是分享自己的文艺经历,譬如某女作家因与初恋男友闹分手,于是一个人拿了本散文跑到海边捡贝壳,从此走上了一条文学之路……
这些,文珍都没有。
她发觉自己很俗,只知道柴米油盐,只知道孩子尿布,只知道家长里短。她不会像他们那样把落地镜子摆在自己的写作桌前,对写作,她从来没有那种优越感;她也不像他们那样不屑于与陌生人交流,反倒她似乎还挺爱在旅途中与形形色色的庸常人聊家长里短。文珍想说,文学不就那么回事,喜欢,就写呗。可她不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她就干脆不说。那个文学沙龙对文珍来说,终于成了煎熬。然后在煎熬至尾声时,文珍突然下了决定:放弃写作。
是到该放弃的时候了。这个决定下得斩钉截铁。文珍这样逼迫着自己,竟真的一熬就熬过了整整七年。熬到远子都十二岁了。
七年来,文珍越来越文艺,这种文艺却是徒有其表,骨子里她早就不再是个作家了。她也渐渐习惯了按文艺的标准去打造远子。远子出生后,老公取名叫房远东,文珍怎么听都觉得俗,什么“刚”啊、“强”啊,当然也包括“东”啊这类字,都被用烂了,多么俗。他也就是占着个姓氏有点冷门,要不然简直俗不可耐。文珍就思谋着得给儿子取个笔名,老公瞪她一眼,你也想让儿子整天坐电脑前鼓捣文字?冷冰冰不懂生活?她就假意退让,那就取个小名总可以吧?文珍心想,作家有什么不好呢!坐在电脑前怎么就不懂生活了?还生活得诗情画意呢!
开始,文珍想叫儿子房子,老公说,你干脆叫车子,或者票子更好,房子咱有了。
文珍就叫他远子了。这名字好,远,代表着无限的可能,而且很文艺,她叫起来也挺顺耳。一岁过后,这个名字就一直伴随着儿子走到今天。
现在,文珍坐在阳台上,陪伴她的是眼前的绿萝和手里的相册。那本厚厚的相册翻下来,除了那次文学采风,剩下的几乎都是远子的照片了。远子才出生时,是每月一批相片,后来变成每年一批,背景是春夏秋冬的,室内室外的,本市的、外出旅游的,应有尽有。照片里远子不负她所望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发型、衣着,有捧着书的,有抱着吉他的,有弹着钢琴的,有夹着画板的,有挎着相机的……跟照片展一样,琳琅满目。这一切也主要在于远子争气,长得帅,这一点像老公,让文珍骄傲,但时不时也让文珍心里不是滋味,自己的儿子,竟然不像自己。
总得想办法让远子像自己才是,否则文珍总觉得不踏实,好像儿子随时都会背叛自己一样。她不光给他打扮,还左右他读书。远子刚上小学,文珍就把自己的书架抬到了远子的卧室。见他无动于衷,她就把她认为他那个年龄应该开始读的拿出来,偷偷摆在他的写字桌上。《希腊神话》《诗经》《论语》《红楼梦》《三国》……他不感兴趣觉得艰涩,她就给他买来带图带拼音的儿童版本。见他还是坐不住板凳,文珍干脆来硬的,给他布置功课,规定时间内必须读完哪一本,多长时间之内必须上交几篇作文给她看。
文珍总是在课堂之外,额外给远子布置作文。有一次,远子写了一篇作文,叫作《我的妈妈》,远子写道:
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妈妈,她是上帝的女儿,来到我身边陪伴我;
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博学的妈妈,她像一滴露珠,日夜滋润着我;
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爱我的妈妈,她给我买那么多漂亮的衣服,给我买那么多乐器,教我那么多技能,让我成为小伙伴中的骄傲,我感谢妈妈。
文珍读到此处,不知为何,她并没为儿子的懂事感到欣慰,相反,突然有点为自己羞愧起来。一直以来,她给予他的,都是她想要的样子,衣服是文珍自己喜欢的,书也是文珍自己喜欢的……她试图把远子变成她心目中的那个样子。这就是她的爱吗?文珍发现自己以前不像现在这样,自己以前也爱玩爱闹,也爱运动。可她现在是动不了了,身上有好几处潜在的毛病。文珍意识到,她对远子的爱,与其说她真的爱他,不如说她被他还有无限可能性、塑造性的人生所感动,甚至是艳羡。当她的暮气与他的朝气开始冲突时,她在用另一种方式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她在爱自己。
远子在最末尾写道:
妈妈,可是我总觉得自己没那么优秀;妈妈,我好怕有一天会让你失望……
文珍看着这么一篇作文,百感交集,那时远子才上三年级。
文珍有时也会想,她做的这些,真的是对远子的爱吗?她不知道。但她知道,自己不这么做,别人却都在这么做。一旦有一天,远子长大后,发现他比身边别的朋友落下了一大截,他会不会怨自己呢?
远子打电话回来说他中午不回来了,跟小伙伴一起在外面吃点快餐,然后直接去上下午的表演课。文珍挂了电话,有些无聊。老公在南昌包工程,平时也很少回家。家里又剩她一个人了。
一种莫名的难过浮上文珍心头,她想有一天儿子会离开这座小城,到大城市去奋斗、安家,这里剩下的就只有她和老公。这么一想,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开始挥之不去。文珍又想到,有一天,她和老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到那时,在这个世界上跟远子有血缘关系的人就一个都没有了。她觉得远子的成长和远子的童年都装在她的肚子里,那么到那时,他的成长和他的童年不都没有了嘛!
这真是可怜的一代人。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又像没来过似的。不像远子和老公,他们各自都有兄弟或姐妹,有陪他们长大的那个能见证他们存在的那个人。而远子的世界,只有他的父母。
文珍不能再这么想下去了,她快透不过气了,她赶紧穿戴整齐,锁上门,在微风中散着步。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新华书店。
周末的新华书店热闹非凡,看书的远比买书的多。文珍随意翻动着书架上的书打发时间,不经意,作家M的一套童话集就出现在了她的眼前。那次采风会之后没两年,这个叫M的小妹妹着实火了一把,文珍记得那段时间她频频在各大小说类选刊的目录上看到M的名字,她还在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栏目上看到她本人,她那时被省作协推荐至鲁迅文学院学习,因为那一届鲁迅文学院有好几位国内当红的七零后年轻作家,所以艺术人生邀请他们去做了一期节目。可是后来,M又销声匿迹了。不成想,怎么改行写起童话来了?
文珍想不通,可这一切现在又跟她有什么关系呢?文珍想想,只觉可笑。翻看着花花绿绿的童话集,绝对难逃出版公司包装骗钱的感觉。文珍百无聊赖时,听见书架的另一侧两个学生在耳语:
亲爱的,晚上去哪吃?声音稚稚嫩嫩的。
文珍撇过头去,一个小姑娘正坐在一个小伙子的腿上,他们各自手里捧着一本书,最多十四五岁的样子。文珍“啧”了一声,现在的孩子可真是……她再抬头看书店里,这里似乎成了中学生的天堂,前后左右都是坐在地上、靠在书架上、勾肩搭背看书的学生,自己身处其中,就像一片葱地里长了一株百合,实在别扭。文珍赶紧扭头,朝外走去。
就是在刚出书店门口时,文珍的手机响了,是远子表演课的老师打来的,请问是远子妈妈吗?远子下午怎么没来上表演课?
文珍立在那,他和他同学去了呀。说完,文珍明白了什么,愣在那。她气得肺都炸了,这孩子果然学会骗人了。她真想把手机举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可就在她举起手机的一刹那,文珍惊呆了:一个小男孩正在天空飞翔呢,就在路口的另一侧。文珍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她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个孩子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接着一辆公交车将他的身体盖住……
啊!文珍叫了一声,闭上了双眼。接着她看见路口那边一个妇女从倒地的电动车上爬起来,冲到公交车前,开始嚎啕大哭,妇女身后跟着一个看上去跟远子年龄相仿的姑娘,姑娘站在公交车前伏在母亲身前嚎啕大哭着。公交车的轮子底下,分明有血在汩汩地流出……
那时,事故现场已经围了一大群人。文珍还未从刚才的气愤中缓过来,这会又被眼前的一幕着实惊着了。心都快跳到了嗓子眼,堵得她喉咙难受。不敢看,也不敢停留,更不愿上前。文珍最不爱凑这种热闹了,赶紧打了一辆的士朝家里开去。
晚饭之前,老公也回来了。这段时间工程不忙,刚好远子要过生日了,就回来待几天。老公说。
文珍做了几道菜,边做菜她边跟老公说,你这儿子你可得好好管管了,学会骗人了。下午的课又没去上,不知道去哪鬼混了。老公不以为然,小孩子嘛,爱玩就让他玩玩。文珍瞪了一眼,老公赶紧改口,好,管,我一定管。
晚饭就吃得有些尴尬。
老公问远子,儿子,下午去哪了?
去上表演课了。远子埋头吃饭。
咳!文珍啪地把筷子摔到了饭桌上。远子抬眼看了看文珍,心虚地低下了头。
你到底去干嘛了?文珍吼道。
别这样,让我来。老公打断了他。
最终这顿饭以远子提前下桌而收场,他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再也不出来了。
本来团团圆圆的一顿饭,吃得文珍一肚子火。
好好吃饭,好好吃饭。老公说。文珍却一下想起了白天的那场车祸,刚要开口说,看着一桌子菜,又觉得不合适,干脆把话咽了回去。
第二天黎明,文珍是被一场噩梦吓醒的。醒来之后,文珍能清楚地回忆起梦中的每一处情节,这是从未有过的,让她害怕。梦里有东西在追她,一直不停地追,然后她疯了一样地跑,接着就撞到了一辆大卡车上。梦的最后一幕,她竟然又成了一个旁观者,而躺在血泊里的竟然是远子。文珍看着血从远子的身体里流淌出来,一圈圈扩散开来。接着,竟发生了回流。不过那些血不是回流到儿子的身体,而是变成了一条线一点点地顺着她的脚趾流到了她的身体里,远子则被吸干了一般,脸越来越白,接着变了形状……
文珍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跑到儿子房间看远子。远子发出微微的鼾声,他正睡得香甜。
文珍想到了昨日目睹的那场车祸,她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他看了看钟,也五点多了,晨报差不多也该送来了,她就干脆穿上衣服去楼下查看信箱。这么一场事故,在这所小城里,一定能上一上报纸的。
文珍到楼下时,投递员还没来。她合了合衣服,就在门口等着投递员把报纸送来。一觉过后,文珍对关于那场事故的前因后果的报道突然变得很期待。在这期待着的清早,文珍想到那个梦,心有余悸。她又想到远子的生日,该给他选一件什么礼物呢?是一套书呢?还是送他一把新吉他,或者一件休闲西装?文珍绞尽脑汁。
报纸如实刊登了文珍期待已久的那场车祸:一个妇女骑电动车带着女儿和儿子去火车站,结果在路上小一点的儿子被一辆摩托车撞飞出去,摩托车无牌照,撞飞男孩的同时逃逸,而男孩在摔落在地的一瞬间刚好被一辆来不及刹车的公交车碾压致死,男孩的姐姐当场就疯了……
文珍颤抖着,拿稳报纸,盯着新闻图片上的车祸现场,胃里翻江倒海,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然后,她在报纸上比划着,顺着照片找着自己当时大概所在的位置,一阵后悔,后悔昨天出去那一趟。
老公和远子起来得晚,起床时,上午已过半。文珍仍坐在客厅里发着呆,饭也没做。老公有点不满意,问她怎么不做饭?她也不吱声,只是盯着阳台的绿萝发呆。远子则看都没看她一眼,显然,远子还在生气。
她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坐了一上午。这一上午她都想了些什么,她自己也没记住。她强颜欢笑地说,不做饭了,我们去吃肯德基。
远子愣了一下,她一向最反对他吃那些玩意儿了。老公也愣了一下,他看了儿子一眼,他也觉察到了儿子尚在持续着的不高兴,就故意提高嗓门叫,还在等什么呢?你妈发慈悲了,赶快洗漱走人了。
远子“噢”了一声。
吃完早饭,文珍对远子说,儿子你想要什么礼物?今天是你生日,妈买给你。
你看着办吧。远子说。
文珍想了想说,要不咱买一套新球服吧?
远子愣在那不敢相信他所听到的,他想了想,终于露出了笑容,你说真的?
当然。
那我要曼联的。
没问题。
老公摸着儿子脑袋,看你妈对你多好,以后要想着孝敬你妈妈哈!
不用。文珍突然严肃着蹲下来,你带给我的快乐早就够了。
妈——远子叫了文珍一声,吞吞吐吐地说,我也有东西要送你。
噢?
算了,还没拿到。明天我生日就能拿到了。远子说。
远子生日那晚,当远子把生日蛋糕上的蜡烛统统吹灭,灯光亮起的那一刻,一个盒子出现在了文珍眼前。远子说,妈,前天下午我没去上课,就去干这个了,都说儿子的生日母亲的受难日,这是我送你的,打开看看。
文珍要伸手,又停住了。她不敢,她知道里面一定是一样不平凡的东西,她生怕打开的是一缕稍纵即逝的幸福,她宁愿慢点。她咬咬嘴唇,颤颤巍巍地打开了盒盖,里面是一本包装精美的书,这本书不是正规出版的书,但却是世界上最美的书。
书的封皮上写着:小说集《园丁》,作者文珍。文珍一下就想起了自己多年前写的这篇同名小说。她小心翼翼地拿起这本书,一滴泪滴在了封皮上,像一颗珍珠落地,清脆响亮,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