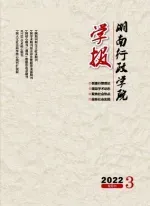合同诈骗罪的相关问题分析
王伟娜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昌平区 102200)
一、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
合同诈骗与诈骗罪属于法条竞合的关系。一个行为在外表上可以认为相当于数个构成要件,但是实际上只适用其中某一个构成要件,其他的构成要件当然应该被排除的场合,称为法条竞合。[1]张明楷教授从形成原因上将普通法条与特殊法条的表现形式分为六种。[2]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属于因犯罪手段的特殊性而设立特殊法条,属于普通法与特别法的竞合。合同诈骗罪既属于诈骗罪的特殊法条,也应当满足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所谓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欺诈手段,骗取对方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在德、日刑法中,仅规定诈骗罪。所谓诈骗罪,是指欺骗他人使之产生错误,并基于这一错误所产生的有瑕疵的意思而交付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对于诈骗罪,张明楷教授认为,即使行为人提供反对给付但受骗者的交换目的基本未能实现时,宜认定为诈骗罪。反之,如果受骗者的交换目的得以实现,则没有必要认定为诈骗罪。[3]在诈骗罪中,就财产性利益也成立本罪,这一点不同于盗窃罪;基于对方意思而转移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这一点又与盗窃罪、抢盗罪相区别。[4]P131日本学者大谷实认为,诈骗罪的本质是用违反诚实信用的手段取得他人财产,由于诈骗罪保护的法益是财产,所以用欺骗手段获取财产以外的利益的时候,如用欺骗的手段与他人结婚的行为,都不构成诈骗罪。[5]论者下述所及是关于诈骗行为的几个争议点。
(一)关于财产性利益
日本论者认为财产性利益属于诈骗罪的客体,所谓财产性利益是指财物以外的其他一切财产性利益,除了取得债权或担保权、使人提供劳务、服务这些积极性利益之外,还包括免除债务或暂缓支付等消极性利益。
德国关于财产的概念有三种对立的意见,分别是:纯法律的财产概念、纯经济的财产概念、法律经济的中介财产概念。纯经济的财产概念是目前德国的通说,台湾也接受此种观点,凡一个人所应得的财产总数就是财产。[4]P132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被害人发生下列三种困境时,即有财产损害:一、所得的给付,与缔约目的不合。二、因为承担义务,必须采取减损财产的措施,例如:支付高利息向银行贷款,或以不经济的价格让售物品。三、由于承担义务,再也不能善加利用自己的资金。[6]
我国理论界通常对此采取以经济的财产说为基础的折中说。[7]P840原则上,只要造成了他人经济损失,就可以认定为财产损失,但是如果造成他人经济损失的行为挽回了更大或者同等的法益,或者单纯使他人免除非法债务的,不应认定为财产损失。
张明楷教授认为,我国《刑法》第24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货物、货款、预付款都是财物,但担保财产则不限于狭义财物,而是包括了债权等财产性利益。可见,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可以是财产性利益。[8]
(二)处分行为
要成立此两种诈骗行为,要求因欺骗使对方陷入错误,并进而做出瑕疵的意思表示。陷入错误如果处分财产不是基于自由决定,行为有可能构成别的犯罪。有无处分行为是诈骗与盗窃区分的重要标准,若是行为人利用被害人不注意等情况下实施,被害人无处分行为,此时,因为无转移财产的意思表示,因此仅属于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诈骗行为的模式可以简化为:欺骗行为——错误——处分行为——取得财产。近期接触一起案例,A与B是男女朋友,A以自己的名义为B贷款,现B拒绝偿还贷款,在此情形下可否认为B构成诈骗呢?论者认为若当初A贷款的时候,B就没有偿还的意愿属于诈骗,若A履行一段时间之后不想再偿还则属于普通的民事纠纷。需要有欺骗行为,并基于错误处分了财产,才可够成诈骗。
二、合同诈骗罪的相关问题分析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属于普通法条与特殊法条的关系,因此若想构成合同诈骗罪,也同样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可是,生活中的相关案例,是否只要出现了合同这种形式的诈骗都可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呢?对于合同的要求,非法占有的目的要求,数额较大的标准该如何界定呢?
(一)合同诈骗罪的相关概念界析
1.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合同诈骗罪规定在刑法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一章,扰乱市场秩序罪一节。因为计划经济弊端的显现,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同作为经济运行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在经济社会中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1997年新刑法修订中我国新设合同诈骗罪,以保护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和诚信交易。
在理论界,关于合同的范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合同不应限于经济合同,另一种观点认为应限于经济合同。
第一种观点认为合同不应限于经济合同。王作富教授认为对于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大多数论者主张是财物,也有少数论者认为是经济合同。[9]支持财物论点的学者从合同性质划分将其归为两类,一类是双务有偿的民事合同,另一类是劳务合同。[10]这种观点认为虽不具有合同形式,但是扰乱了市场秩序的协议也应纳入“合同”范畴。
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应限于经济合同。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发布了《关于当前处理经济类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以及1996年12月16日发布了《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中第2条曾规定:“根据《刑法》第151和152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11]在解释之中使用了“经济合同”一词,因此有观点认为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应仅限于经济合同。
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规定我国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扰乱市场秩序罪一节,侵害的法益应是良好的市场秩序。对利用劳务合同,利用不符合合同形式的协议进行诈骗的行为与经济合同的诈骗侵害的法益具有相同性,硬将二者人为分开,与市场经济运行之中人们的通常理解相违背。当然目前在实务中还应以司法解释的范围为限,将其限制于经济合同的范围。曲新久教授认为,日本法国对于骗逃劳务有类似的规定,但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定,因此劳务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的对象。[12]
既然将利用合同的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规定为合同诈骗,就其与普通的民事欺诈相区分的角度来讲,其区别体现在,就合同诈骗罪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其司法解释将其界定为经济合同,所以,只有利用经济合同这一类特殊的行为方式实施的诈骗行为,才能符合合同诈骗的合同要件。对于民众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劳务欺诈,不符合合同形式的诈骗行为,不能界定为合同诈骗罪。
2.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的目的
关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张明楷教授认为,合同诈骗罪的责任要素除故意外,还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非法占有的目的既可以存在于签订合同时,也可以存在于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产生非法占有的目的后并未实施诈骗行为的,不能成立合同诈骗。[7]P745由于日本刑法未规定合同诈骗罪,对于诈骗罪的主观要件,日本学者大谷实认为,在诈骗罪之中,除了故意之外,还需要有非法占有的目的[5]P247。山口厚则认为,违法性的实质是法益侵害、危险的引起,由于有无法益的侵害和行为人的意思无关,故而基本上不能认可主观的违法要素。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需要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通说。[13]
我国《刑法》第224条明确规定要求非法占有的目的,《刑法》第224条规定:(1)以虚构的单位或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产权证明作担保的;(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而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的。前四种行为都与“非法占有目的”有联系,凡是适用刑法所规定的欺诈手段的,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原则上均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4]从其行为本身已经体现出行为人对于合同诈骗行为的非法占有的目的。
合同诈骗罪需要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合同诈骗罪的法条列举的几种行为方式,其已经体现出了合同诈骗罪所要求的非法占有的目的。合同诈骗与普通的民事欺诈行为相比,区别的关键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由上文知,张明楷教授认为非法占有的目的既可以存在于签订合同时,也可以存在于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但产生非法占有的目的后并未实施诈骗行为的,不能成立合同诈骗。笔者认为,刑法的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要求非法占有目的与危害行为的实施具有一致性,签订合同之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签订合同之后产生的,因不能履行合同要求的债权等权利而产生非法占有的目的,则属于普通的民事欺诈,不属于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的目的。同样的,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若仅产生了非法占有的目的,并未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也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适用规则
实务中有这样一则案例:2011年4月,赵某租住郭某的房屋,到期后因无力支付租金,便告知郭某7月份以后不再续租,郭某到房屋中介登记出租信息。2011年7月9日,郝某欲租房屋,到郭某家看房,此时赵某尚未搬离出租屋。赵某遂生骗取房租的想法,谎称自己系郭某的女儿,与郝某签订租房合同,骗取租赁费8400元。关于本案的定性和处理存在争议。
根据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溯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七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溯。在本案中,赵某的行为因不满足数额要求,在处理中存在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因赵某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而合同诈骗与诈骗罪属法条竞合,因此只能适用特殊条款即合同诈骗,最终认定赵某不构成犯罪。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案中犯罪数额不符合合同诈骗“数额较大”的要求,但是达到诈骗罪的追诉标准,应按诈骗罪处罚。
关于“本法另有规定”的解释,有观点认为只有在包括数额在内的所有构成要素均符合特殊条款的规定时才可适用特殊条款,否则仍应适用一般条款。[15]对于此问题,黎宏教授有不同的观点。黎宏教授认为,其一,在这种情况下,以普通法条论罪,有违罪刑法定主义之嫌。其二,以普通法论处会存在罪行失衡的问题。黎宏教授在文中举例说,个人集资构成诈骗的起点为10万元,行为人集资诈骗8万元的,若以普通法论处,应构成诈骗罪;集资诈骗10万元的,构成集资诈骗罪。前者可能属于诈骗中的“数额巨大”,法定刑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后者法定刑则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结果是,以同样的行为方式诈骗的,数额较小的反而处罚更重。[16]
对于上述二者观点之争,刑法149条第1款规定:“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不构成该各条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本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处罚。”张明楷教授认为这是一条注意规定。[7](p656)笔者同意此观点。由此,其一,对刑法的解释应当符合体系解释的要求,在解释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等特别法条时,刑法认为不符合特殊条款规定时应当补充适用普通条款,为维护刑法解释的统一性,除非有特别规定,否则刑法的解释应当符合体系解释的标准。其二,当行为完全符合本法另有的特别规定时,应按照特别规定处理;而当行为不完全符合另有的特别规定时,应适用普通法条的规定。对于黎宏教授在其文中所指出的可能会出现的量刑不均衡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集资诈骗本身金额较大的特殊性,因此刑法中对于集资诈骗涉及的金额规定了较高的数额标准,而处理具体的案件中法官需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自由裁量权,以做到罪刑均衡,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
结语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在笔者实习期间有所接触,便以此展开论述。法律条文的简洁性使得法律条文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性,需要系统的分析理解法律条文。本文先从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比较分析角度进行探析,探析了二者的相通之处,后分析了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适用规则。以期更好地区分二者,并运用于司法实践中。
[1][日]大塚仁.刑法概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张明楷.论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J].中国法学,2005,(5).
[4][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M].王昭武,刘明祥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5][日]大谷实.刑法各论[M].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6][台]林东茂.刑法综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7]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8]张明楷.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3).
[9]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10]姜晓燕.简析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性质之界定[J].法制与社会,2003,(1).
[11]郭大磊.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标准[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11,(4).
[12]张建生,王作富,曲新久,周常治.骗逃铁路运费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J].人民检察,2005(,5)
[13][日]山口厚.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4]李明.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规则[J].法学杂志,2013,(10).
[15]鞠佳佳.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双层界分[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6).
[16]黎宏.论法条竞合的成立范围、类型与处罚规则[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