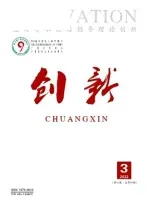中国新型公共产品的缺失与供给研究
白彦锋 王 凯
规范的“公共产品”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于1955年左右提出的,[1]指的是兼具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主要由政府等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很快就成为现代财政学理论的基石之一。“十一五”以来,我国教育、就业、社会保险等传统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性的公共产品”和“制度性的公共产品”等新型公共产品的消费和供给都出现了不少亟须关注的新问题。
一、资源性公共产品与公地悲剧
空气、水、土壤等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自然资源,是财政学视角中最典型的“公共产品”。然而,在人们过分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冲动之下,这些基本的公共产品正在遭受无情的破坏,现实版的“公地悲剧”在我国反复上演。草场退化、水体污染、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都可以看作是“公共悲剧”的真实写照。以水资源为例,环保部、国土资源部与水利部发布的《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显示,全国地下水超采区域300多个,面积达19万平方公里,严重超采面积达7.2万平方公里。对于浅层地下水超采的地区而言,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但深层地下水超采的地区必然会造成地质沉降问题,深层的地下水补充非常困难。地下水超采引发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地表沉降是最为突出的威胁。
二、制度性公共产品:食品监管与交通可持续发展
与自然资源的“公共产品”的危机类似,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等制度性的公共产品也已告急。2008年中国奶粉三聚氰胺污染事件出现之后,国内消费者对以奶粉,特别是婴幼儿奶粉为代表的高端奶粉、食品出现了空前的信任危机。为此,不少消费者将目光投向了香港等地,因为这些地方的相关产品价廉物美,而且产品质量有保证。然而,香港市场毕竟十分有限,内地消费者蜂拥而至,必然会导致香港奶粉市场的崩盘。在当地民众购买奶粉难度加大的压力之下,香港政府以违背自由市场经济准则和信条为代价,推出了奶粉限购令。无独有偶,荷兰、新西兰等其他西方奶粉生产国家也推出了类似举措。应当来讲,迅速富裕起来的消费者为奶粉等很多商品打开了巨大的市场,然而,食品监管等外部准则的缺位却使这一商机迅速化为乌有。“劣币驱逐良币”的巨大作用,让政府、市场、消费者、商家没有任何一方是最终的“赢家”。造成这种“多输”局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制度化“公共产品”的缺失,而制度化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利又迅速导致了空气等资源性公共产品的过度消费,二者之间的共同作用进一步加剧了“公共产品”的新危机。
除了奶粉等食品监管领域之外,制度性公共产品的缺失还表现在交通等其他领域。在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不管是大都市还是小城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交通拥堵以及由此衍生的空气污染问题。为此,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纷纷出台了限购、限堵、限行等政策。这些政策一方面削弱了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根基,证明了我国既往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也在拷问我国相关“制度性公共产品”的有效性。
三、破解新型公共产品危机的治理之道
第一,对于资源性公共产品的保护,应该转变观念,通过鼓励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来替代高投入、高污染,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即由更多地依靠物质资本转向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以医疗器械市场为例,它关系我国社保、政府采购等多个领域。我国医疗器械总产值在2011年就已经突破千亿。但其中,核磁、CT等高附加值大型设备市场,几乎被GE、西门子、飞利浦等外资公司垄断。在不少医院,甚至连螺丝钉、手术缝合线、各种试剂等小型耗材,也都采用价格高昂的进口产品。过度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或外资品牌,导致患者检查费用攀升。据《中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器械检查费用已经成为继药费之后病人的第二大负担。医疗器械、特别是高端医疗器械的生产周期长、技术投入高,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亟须政府在政府采购、社保报销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扶持政策,帮助国产品牌树立良好形象。这样既为国产企业打开了市场,也减轻了我国传统产业的环境资源压力。
第二,对于制度性的公共产品,可以借鉴我国香港地区打击“奶粉水客”的办法。为限制抢购奶粉,适当预留婴儿奶粉给本地居民,香港特区于2013年3月1日起实施《2013年进出口(一般)(修订)规例》,根据该法例,离开香港的16岁以上人士每人每天不得携带总净重超过1.8公斤的婴儿配方奶粉,这相当于普通的两罐900克奶粉,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万港元及监禁两年。此项政策出台之后,香港地区的奶粉水客几乎绝迹,政策效力可见一斑。相比大陆地区,在食品监管、环境质量等不少方面都存在违法成本过低的问题,结果使罚款限令成为了很多地方政府的生财新路,甚至使罚款这种本来应该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措施异化成了“乱罚款”,为人们广为诟病。
总之,面临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性和制度性的新型公共产品的缺失,我们确需及时反思,创新公共产品的供应方式,引导民众形成对资源性公共产品健康有序的消费模式,全面提升我国公共服务的管理水平。
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公共产品的适度供给
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面双刃剑,因为它势必会增加财政支出的压力和负担,因此,“分阶段适度供给”就显得尤为重要,下面结合新型城镇化问题进行分析。
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一度成为了城乡之间的“候鸟”,非城非乡,但是这可能是我国现阶段城镇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因为大中城市目前虽有就业机会,但是一下子将农民工全部市民化,必然使公共财政背上医疗、教育等很多公共服务的巨大包袱。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城市经济减速,农民工还可以返回农村,不至于酿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城乡之间的两栖生活成为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减震器。所以,应该看到,我国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是现阶段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有其制度优势的。换句话说,农民工确实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应当给予其一样的市民待遇,但是一蹴而就是不符合现实发展规律和要求的。有学者在分析我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所设计的“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三元结构,也是一种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的务实之谈。[2]在农民工融入城镇的过程中,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弱势群体是否获得了养老、医疗、失业等基本社会保障。在这方面,既需要政府的制度跟进,更需要企业主给予农民工同等待遇。
其实,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内部至今也存在二元结构,尤为突出的就是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养老社会保障的双轨制。2008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市先期开展试点,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配套推进。《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无论是养老还是医疗,很多事业单位包括机关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其人员与企业职工一样逐步参加了各类社会保险。随着社保标准的提高和改革的不断推进,“双轨制”终将合并统一。[3]
当然,农民的市民化、养老保险“双轨制”的最终统一必须要分阶段小步快跑来实现,因为其受到我国财力、人口老龄化等很多客观条件的约束和限制。类似的社会保障都有“刚性(Rigidity)、只能上不能下”的鲜明特征。不顾国情和财力的超前社会保障,必将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切实际地提高社保水平,一方面未来削减起来难度很大;另一方面只会使政府财政招致更多的负债,而这些政府债务相当一部分最终要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化解,将会使得低收入群体生活成本进一步上升,从而陷入无法自拔的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为此,从财政收支的客观状况出发,把握好民生财政或者公共产品的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救助穷人而不养懒人,实现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1]Samuelson P.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s[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36).
[2]李克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J].中国社会科学,1991,(3).
[3]徐博.人社部:社保“双轨制”终将合并统一[EB/0L].[2013-06-16].http://www.chinesenew.com/gn/2013/06-17/493219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