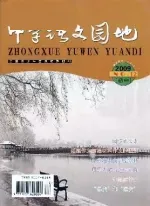痴 草
寇胜茂/文 邹永进/评
对于草,我总有挥之不去的情结——那是自小就得下的“病”,至今治愈不了。
少时家贫,不得不养一只羊、一头猪、几只鸡,割草便成了我最大的“营生”与乐趣。从3岁起,连路都走不稳的我,就知道挎笼磨镰了。稍长,便与一群穷伙伴上南塬、下河滩,往水丰草美的地方赶。有时,找着一块好草地,还要“封锁消息”,怕别人知道了偷着割去,也有为圈地占草与伙伴吵架甚至打闹的时候,但心里都不搁事,今天恼了明天又好上。傍晚回家,只要背上一笼满满当当的草,再看着妈妈微笑的脸,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割草就这样成了生活里重要的场景。
那时的渭河,水还比较充沛,滩上的树高大而挺拔,虽然只是普通的杨、柳、槐等,但那场面与气势却是我至今最壮阔的回忆。遇到好年景,河边的草茂密又庞杂,真有点碧草连天绿无涯的味道。到了夏秋时节,花儿紫黄,蜂蝶嗡嗡,漫过我们脖子的草地简直成了乐园。乏了,就势躺在柔软的草上,像投进妈妈的怀抱,听鸟叫蝉鸣,看云走霞飞。
也有割不到草的时候。饥馑的年代,好像什么都缺。将不多的草蓬了又蓬,让它虚虚地罩在笼里,或者干脆在笼底放些树枝,上面盖上薄薄一层草,迟磨到天黑,进村后先闪进羊圈猪舍,胡乱地撒上几根,才敢进屋。到了冬天,草更难找,只能在向阳的坡头、崖下、河边,遇上一些耐寒的植物,干枯的枝干下还有那么一小丛绿。
割草还有讲究,对于枝干粗大韧硬的,比如“狼尾巴”,应用钝镰,带有砍削的劲头才能奏效。柔软或贴地长的,比如“趴地龙”,要用快镰,刃越利越好,一镰撸下去、偎着进、转几圈、不歇气,就能放倒一大片。有些草,比如“猫耳草”,根须很浅,实在不宜用镰,只要用手一拔、再向后一甩,泥土就全掉了。姿势上要得法,拔草应先弯后直,割草宜微屈前倾,大多时候要右腿盘坐在地上,左腿半屈,膝盖向上,以掌握前进的方向并平衡肢体。镰刀要用长把的,开镰时先用左手攥紧草的上部,再翻转着一缠绕,右手快速地使用“连刀法”,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割草也让我知道,无论干什么事只要认真,就能把握特点和规律。有时生了气,也去割草,一看到绿色的海洋,闻着浅淡的草香,就把啥都忘了。
后来上了大学,离开了草和割草的伙伴,但对草的钟爱不减而甚。每看见它,总有一股莫名的冲动。妻笑我:“人家是花痴,而你却爱草,怪……”女儿说:“我爸的驼背,是从小割草背笼落下的病根。”我至今仍记得《汉语词典》里“艹”部的字有530多个,从简单的“艺”、“艾”到笔画在17个以上的“蘸”、“蘼”……没事总翻一遍,看都是什么意思。唐诗宋词中,有关草的我能背上30多首,从简单的“离离原上草”到比较哀伤的“一身乌色更招馋”……草就这样,况味一言难尽,却滋养了我的人生和思想。
有时候也想,水是草的泪,不然它们为何都扎根地下;树是草之最,因为它们都向往蓝天白云。读书时看惠特曼的《草叶集》,欣赏“我要到林畔的河岸,脱去伪装,吮吸草的真味”;看鲁迅写“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我就血往上涌、脊背汗热……几十年前,我第一次听到《小草之歌》,是在一个风雨之夜,我走出门去,跑了古城的几十条大街小巷,彻夜不归地寻草。我知道,从那一刻起,我这一生就是草命了,光水哺育、装扮大地,随遇而安、无名来去,又不惧风雨……
[感悟]本文表现了作者对草的喜爱之情。文章开篇用“病”形容“我”挥之不去的“草”情结,表明作者对“草”的感情之深。割草是“我”童年最大“营生”与乐趣,伴随着“我”的成长。从割草的过程中,“我”不仅总结出一些经验规律,而且还认识到人生的哲理。“我”爱草成痴,不仅喜欢真正的草,而且与草有关的汉字、诗词都爱屋及乌,喜爱有加。普普通通的草,滋养了“我”的人生和思想,草“光水哺育、装扮大地,随遇而安、无名来去,又不惧风雨”的精神成了“我”人生的精神追求。“我”喜爱草,不仅是因为草是“我”童年记忆的主要意象,更因为“我”喜爱草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