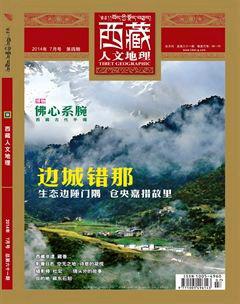杜宏



在这片苍茫亘古的荒原上,杜宏已行走三十余载。自1997年起,专注于西藏天、地、人三部曲专题摄影。以其对西藏历史、文化、民俗、宗教的深入研究和理解,用镜头记载历史,用视觉讲述变化,用角度感动心灵。独特的展现西藏“天者,神也;地者,境也;人者,魂也”的历史文化民俗及宗教景观全景图画。
摄影家是用镜头说故事的人,但有些故事,即便摄影家也无能为力。
杜宏所说的故事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那位一百岁的女修行人,她曾经走过喜马拉雅山南北的山山水水,就好像在自己后院溜达一样。
杜宏问她是否也有过爱情。老人狡猾地笑,说没有过。但是她又说,爱情啊,就像是天上的老鹰,趁你不注意,就会冲下来咬你的肉吃,如果你赶它,它就会飞走,要是你不赶它,它就咬你的肉吃,一块又一块。
这位老修行人已经过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她会像摘下一朵花那样愉快地抛下当世,还是会有些不舍和忧伤呢?这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
杜宏的作品中有一幅《神鹰望月》,我觉得隐约和这个故事有相关之处。这幅作品只有两个色调:蓝与白,像是一扇屏风的两面,鹰在半空中盘旋,月亮隐约露出沧桑的弧度,一切都静止着。
杜宏自己这样写:它是生命的使者,也是灵魂的翅膀。在太阳升起的时分,它飞向浩瀚天宇的深处,凝望那新月的光芒,把它哲人般的身影投影在广袤的大地上。岁月,因此归于沉寂。
老修行人就像那只鹰,向永恒而冰冷的月飞去;又或者老修行人是月,经过沉寂而古老的岁月之后,看着鹰向她飞来。这鹰是爱情,或是死亡,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她等待着两者重合的那一刻。
杜宏的风光摄影,如《暮色中的雪山》或《风雪南伊沟》,都在表达一种与自然沟通的努力:雪山与暮色的对峙与对话,森林和风雪之间关于永恒的动与静的对话。这并非是以人类的角度来诠释自然,尤其是西藏。西藏过于广袤,有超越人理解力的宏大;然而将自然完全留给自然,不加以展现和诠释,扭头而过,摄影也就失去了意义。
可以说镜头的两端,架构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并通过无言的构图来得到展现。在《沐浴节》中,这种对话得到了完满的展现女人丰腴的,柔软如水的裸体如同跳跃一般呈现在同样柔软的流水中,波浪的弧线和女人的弧线相互交错、融合。如此无言的对话,只有通过摄影才能呈现。
当然并非所有作品都需要做如此的解读,有些作品如《暮色中的雪山之二》则可以认为是妙手偶得的轻松之作,夕阳下的雪山被加以柠檬黄色之后,便如同一块即将来开的幕布,或者是现代主义金属雕塑品,呈现出极为有趣的质感。可见未必雪山就一定要呈现出宏大、神圣的意义,其美感可以来自众多层次。
关于人物摄影,杜宏也有不少精彩之作,有些故事是可以说得出来的,例如《戴着耳钉的小央珍》。这幅作品是偶得之作,杜宏说自己下乡采风时停车路边,突然发现这位堪称衣衫陈旧的农村小姑娘耳垂上阳光闪烁,他在自己的摄影集中如此写道这一幕:“一下子,她就从一群小孩中吸引了我的目光。她的耳朵上戴着一个小小的耳钉,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闪射出灿灿光芒。我被深深感动,为她心中那柔美的希望追求。”
有些故事则未必能轻易说得出来,在《远方》这幅作品中,看到的是一对孩子的背影,男孩是传统的厚皮袍,女孩也是一身牧装,携手而行,脚下是无边的,已经有些枯黄的草原,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有趣的是这幅作品简直可以当作黑白摄影来看,全片中基本只有黄、黑、白三色,男孩肥大的皮袍有着草原一样起伏的苍老的褶皱。远方是哪里?他们究竟往何处去?这一画面让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西藏著名作家扎西达娃的名作《西藏,系在牛皮绳扣上的魂》,故事里同样有一对前往远方寻找香巴拉的男女塔贝和琼,受到莫名的躁动驱使,一直向地平线走去。
作家和摄影家都聚焦在人物身上,但更深远的焦点则有羡慕,有焦虑地投射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深远的,无限延伸的地平线决定了扎西达娃的塔贝和琼,或者杜宏镜头中这两个孩子的去向,决定了他们与世界的关系。有位诗人说“地平线是宇宙中的最后一根弦”,的确如此,这是一根时时拨动的弦。
对藏传佛教僧人的摄影一直是西藏摄影的主要内容之一:僧人的红袍如同古典雕塑,有力、饱满的裸臂,还有神秘的,仿佛走在云上的微笑都让僧人的人像成为西藏的标志性摄影之一。杜宏对僧人的摄影多呈现出僧人本来的生活面目,如老僧人之间亲密的交谈等等。虽然是人间烟火,但诗意从没有缺席过。
杜宏说他与一位老僧人是忘年交的好友,他始终记得这样的一个场面:他沿着石头台阶走进老僧人的小院,花开满院,老僧人站在台阶最高处的花枝下微笑相迎。在摄影作品中,他展现了相似的意境,虽然不是在那位已经过世的老僧人的小院。
《扎西陀卡寺》,同样是一座白色小院,院里的桃树笼罩整个小院,桃花触及人头。没有老僧人,却有一位年轻的僧人守在门前,他所迎候的来者也不是摄影师,而是另一位僧人,两者隔着三四米距离微笑不语。似乎他们正要开始一场充满禅机的对话,或者这场对话已经在无声中开始了,就像是西藏版的寒山、拾得。
这未尝不是杜宏对自己和那位老僧之间邂逅的描述,尽管一切都可物是人非,摄影所留下的也只有回忆的残影,但那一刻的会心和禅机却始终生机勃勃,未曾远去。在这个时空里,我们又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