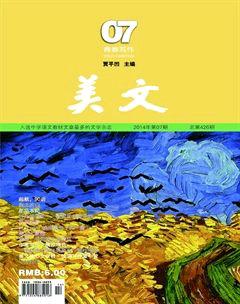未知
吴百川
城市的边缘,高楼在古屋摧枯拉朽的气势面前迅速坍塌。
我看见一高一低,突兀地对比着。视野的边缘多出了一片苍白的开阔,是天空变质了的色彩。视野的开阔,让人感觉天空的重量增加,向地面压迫而来。人与人站立的地面,显得那样低矮。
一切还只是开始。华丽淡后,还有什么能应接不暇。人类滋长缓慢的文明在面前重复着单调的节奏与旋律。灰色、灰色、灰色,视线开阔却因此更容得下浑浊,低压压毫无起伏的平房在城市的郊外谱写着喑哑的诗篇。
车轮的声音伴我前行。甩开了那些不修边幅的村郭,尘气莽莽然扑向双眼。城市的主动脉扎在眼前,扎进那水泥地融为血肉,载着烟尘和车辆,输进城市日益疲乏的心脏。
这样会得心脏病的。
跨过了主动脉,尘气耗散。同样是不修边幅的,却长了个子的平房在这里盘虬成弯曲的巷陌。这是另一个聚落,有着弯曲回环的泥泞小径,铺着一路颠簸的碎石。像余光中说的“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我忽觉这里的巷陌也与他说的有几分相似。过了这成团的迷宫,江南水乡的密集水系出现在眼前。我看见水网包裹着村庄,温柔地静止着。那些或宽或窄的河道,是江海的灵魂,沿着土地龟裂的血脉侵入而来。
像是最原始的村庄,生长着宁静的中午。那些并不算窄的长巷短巷里,行过几里地也见不到人影。村落在这里以最安详的姿态与水相处。它们没有河堤,与水相处得那么近。岸高出河面不到一尺,像是回应村庄的信任,河水永远安静不起一丝波澜。它们弯曲成最曼妙的姿态,从各个角落把土地缠绕,蔓延出或宽或窄的河面。已经成了最随性的搭配,却找不出每一隅取景的瑕疵。
河水侵入村庄则被老榕树诱俘,老榕树包裹住河水的退路,把它酿成碧绿的潭。径自流淌的河水,在它那矮矮的湿润的岸上,树木也沿河自然地生长成林。树木以最原始的姿态向我招手,稻谷在岸边低头,我感觉时光倒退了几十年。
沿河有石梯直达河床,河水生长到第二阶,将它漫过,留下潮湿的苔藓在时光的漏影里蠢蠢而蠕。我看见水乡原来也可以这么美好,只要村庄愿意放下身段这样靠近水网相处。瓦缝剥蚀,树林浅浅而立,一切安静到没有声音。
只要水是清的就很好。
一路向南就到了江边
江海总是被拿来相提并论,其实二者差别很大。海是鲜活的,有呼吸的,只要你站在沙滩上,你就能清晰地听到她温柔的酣声,似乎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潮水的涨落很明显,海面的一收一绽,潮水的来退会十分明显。站得近点,会觉得自己马上要被海水带走。而江则不同。江是流动的,它不喜欢拍打自己的沿岸,它只专心流入海洋。已经站到了江的最外沿,它也不愿意起来拍打我的脚。
其实也不愿意被它拍打的。江是很浑浊的,浑浊得让你想不到被它涌入的大海怎么会是湛蓝的。浑黄的江水很没吸引力,只是向东眺,发现水色在那里变得干净而碧蓝。
那里是东海了吧。
于是改道向东。一路过去看到的都是一些破败的造船厂。高高的机器停止了运转,没有一点声音,在这个寂静的中午,颓坏得让人觉得有些可怕。路况很差,黄沙厚厚地堆积,道路坑坑洼洼。路的一侧是废停了的造船厂,另一侧是一些矮矮的平房,活动的人家,告诉别人这不是一座死城。

路很快穷尽。平凡的旅程在一座废弃的造船厂宣告结束。此时可以看到沿岸的江水正在渗出清澈。穿过这座工厂,应该会抵达所谓的东海。进入死去的船厂,一片寂静,厂房没有一点工作的声音,成片的机器在沉默。这里的生命力被抽去,它已经空了,却占了大片的土地。几只散养的鸡在这里穿行,告诉别人这里的一切还没有死尽。
终于连机器也看不见了。我知道我在穿越泥泞,穿越芜杂,穿越废石冈。我知道我一侧头就能看到越来越宽的江,焕发出海的色彩的江。而我却在荒凉中行走,行走在不毛之地。我深知这不是海,因为它没有潮水。
山深深地凹陷,地面全是碎石。我知道我已经进入无人区。我感觉自己已置身荒凉的海岛,孤立在无人的海中央。远处是一座白塔嵌入遥远的海,我却无法向前。身后是深陷的山,面前是延伸的海,它们在把我拉扯,我却无法向前。
脚踩着荒凉的土地,我知道海还在呼唤我。
我走过的,有多少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