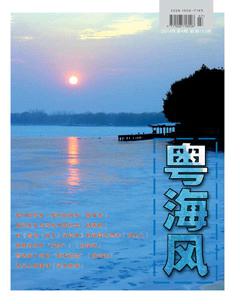“文革”之文学不可视而不见
周思明
报载:人民文学出版社近年出版了一套《新中国60年中短篇小说典藏》,这套丛书一共9本,按时间顺序编排。但吊诡的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居然没有作品编入。有资深人士告知,那十年(指“文革”时期)的确没有什么值得载入史册的小说,并非出版社故意遗漏(文见《张艺谋的隐秘“归来”》2014年5月21日《南方日报》)。由是,生发了笔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的一些联想。在可见到的一些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或图书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文革”十年间的文学内容阙如、作家作品隐身的怪现象。正如有的读者感叹:这十年仿佛是文学史失踪的十年。对于我这样曾经经历了十年“文革”且也曾经阅读过不少“文革”期间发表在各种报刊的文学作品的“50后”读者来说,尤其觉得惘然:那十年好像被谁偷走了一样。然而这种人为造成的文学黑洞中却又似乎藏着极为深邃的内容,因为当今许多青年人不曾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
“文革”(1966—1976)时期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文革”结束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家茅盾曾评价“文革”时期的文学艺术是“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这句话在当时影响很大,今天回过头来看,此言差矣。茅盾应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但现在看来,茅盾先生在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文学艺术这个问题上,也未能做到实事求是。事实上,“文革”时期的文学艺术,也并不是这样贫乏,只是“文革”时期的文学艺术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强烈,因而显得有些公式化,但在一代文艺工作者辛勤努力下,仍不乏值得载入史册的作家作品。
客观地说,小说创作在“文革”前期基本一片空白,以1972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牛田洋》为发端,到1976年整个“文革”后期出版的长篇小说一百余部。而中短篇小说创作在1971年以后随着各地文学杂志的陆续复刊,可说进入了一个高潮, 数量极为庞大。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从情节构思、人物设置到叙事方式,都表现了明显的公式化倾向,“三突出原则”与主要人物的“高、大、全”形象设计是主要的时代特征。其中《艳阳天》《金光大道》《万年青》《大刀记》《分界线》《万山红遍》等是“文革”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中国当代文学史册以及类似《新中国60年中短篇小说典藏》之类的图书中,“文革”文学研究领域的空白,使我们的文学发展链条和文学研究链条出现了人为的断裂,这种断裂很容易造成中国当代文学地图的模糊空间,这种模糊空间的存在又使得我们的文学变得越来越虚无化、主观化,并破坏了我们对于文学神圣的自信,混淆了后人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视听。正如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将洗澡水与婴儿同时抛弃一样,我以为文学研究界有必要把“‘文革文学”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的考察视野,去探寻一下谁在支撑起这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作者杨健曾经罗列文学史对于“‘文革文学”的描述,不妨公布如下:吉林省5院校1983年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称之为“一个没有诗歌、没有小说、没有散文、没有文学批评”的黑暗萧条时期。河南12院校1988年合编的《1949—1988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评选》序中说:“‘文革十年,文艺领域变成了一片白地,当然没有什么可选。”《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主编,1987年出版)引言称:“‘文化大革命十年可以说没有文学思潮,只有打着文学旗号的反动的政治喧嚣。”199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词典》中,“文革”期间的作品大陆仅收录了《艳阳天》一部作品,台湾作家的作品倒有19个条目予以介绍,仿佛当时文学的盛典应是在台湾。
其实,“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文学”有着割不断、理不乱的联系。比如,新时期写出《腊月,正月》《满月儿》的贾平凹、写出《班主任》的刘心武、写出《人到中年》的谌容、写出《乔厂长上任记》的蒋子龙等当代著名作家,“文革”时期都有小说发表或出版。《万年青》是谌容第一部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据该书文末所列,小说1973年写出初稿,1975年定稿。小说故事发生在1962年,相隔浩然《艳阳天》故事发生的时间1957年,迟延了5年,因而主题也发生了变化。这部长达34万字的长篇小说,后来谌容所有的单部头作品也没有在篇幅和数量上超过它。从这部小说的失败和阅读的痛苦可以看出,作者谌容未能达到浩然的文学水准,因此她不可能享有“一个作家”的巨大殊荣。在小说写作上,浩然和谌容一样,对主题思想是没有话语权的,真正显示出功力的,只是在狭小的别无选择的主题内在人物塑造中进行个性化的填充。因此,这也正是“文革”期间小说不可谓不少,但真正能使人读出味道、读出文学气息来的不多的原因。
此外,据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记载,刘心武曾于1976年6月发表小说《睁大你的眼睛》,“小说描写北京街道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开展社会主义大院活动的故事。”徐州师院编辑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中的作者自传中则称该小说“反映北京胡同大院一群孩子同反动教唆犯斗争”的故事,而在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刘心武小说精选》附录中的作者文学活动年表则有些模糊地介绍说这篇小说“写一个大院里孩子们同坏蛋斗争”。这种变色龙般的简介,个中潜伏的隐讳意味不言自明。以小说创作蜚声新时期文学的女作家张抗抗在“文革”中也有长篇小说问世。张抗抗这部小说名为《分界线》,1975年7月写毕,1975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有人把它命名为一部政治图解幻想小说,从题材上看应属于知青小说,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相似处,主要围绕改造土地,兴修水利,书到一半时,已一切顺利,下半部只好写抗洪。这构成了非常俗套的劳动主线,思想线索则围绕政治挂帅还是利润挂帅展开冲突,小说强调了开垦荒地不是为了利润,而反对势力即修正主义的代表认为是劳民伤财。这样就构成了这种小说的最大路化的矛盾。概念化的人物、乏味的描写、虚假的生活细节、忍不住要跳出来的通讯报道般的抒情,使之成为一部除了图解外没有任何价值的小说。
以小说《内当家》出名的王润滋1976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使命》,反映“文革”期间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歌颂贫农的儿子、共产党员、青年教师杨青志“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见《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梁晓声1976年9月出版小说《小柱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描写红卫兵小柱子和他的小伙伴们同放火烧山的地主作斗争的故事(见《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在被习惯性地称为“江青集团操纵的重要舆论工具”的《朝霞》丛刊《碧波万里》中,古华描写水利工地上革命派、保守派的俗套冲突的小说《仰天湖传奇》也赫然在册,其语言清丽流畅,人物对话生动,隐见不凡的潜力。后来以《桑那高地的太阳》《苍天在上》闻名的陆天明,在《朝霞》丛刊《青春颂》《珍泉》中也接连推出话剧剧本《樟树泉》《扬帆万里》。
有研究者试问:那些在“文革”期间没发表作品的作家,是否有迎合当时文学思潮的行为呢?比如王蒙,“文革”期间似乎无所作为,但《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中收有王蒙写于1979年的自传,介绍他于1973年开始动笔写长篇小说《这边风景》,1978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帮助下已完成初稿60万字,赶上半部《艳阳天》的长度。这部皇皇巨著没能赶在“文革”期间出版,反而在长达40年后的2013年4月高调推出,虽然王蒙自己坦承该作有所局限,但主流评论界却是一片叫好喝彩声,个中况味,颇耐人寻味。
其实,“文革”中除了浩然,也有一些至今没有争议的作家作品值得说道。比如,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长篇小说《沸腾的群山》(李云德著)、《海岛女民兵》(黎汝清著)、《雁鸣湖畔》(张笑天著)、《青春》(张长弓著)。此外,出版的长篇小说还有郭先红的《征途》,郑直的《激战无名川》,姜树茂的《渔岛怒潮》,前涉的《桐柏英雄》,杨啸的《红雨》,郭澄清的《大刀记》,克非的《春潮急》,木青的《山村枪声》,等等,也都反响不错,达到一定的文学水准。尤其是李心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几与浩然的《金光大道》齐名,也是1972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反响同样热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了这部小说,后被译成英、日、法、越等国文字,还由著名作家王愿坚、陆柱国改编为同名电影,其中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至今传唱不衰。
综上所述,所谓“文革”时期“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说法,是站不住的;所谓“文革”时期没有文学,“文革”时期的作家作品不值得入史也是不真实、不客观、不公正的。如果按上述结论,《闪闪的红星》《大刀记》《沸腾的群山》《探宝记》《红雨》《万山红遍》《海岛女民兵》《小号手》《桐柏英雄》《渤海渔歌》《燕岭风云》《粮食采购队》《青春》《边城雪》《带响的弓箭》《新来的小石柱》《响水湾》《山村枪声》《红石口》《山川呼啸》《使命》《小兵闯大山》《钢铁巨人》《洪雁》《春潮》《丹凤朝阳》《红缨歌》《战地春秋》《高高的苗岭》等一大批文学佳作就应该被打入冷宫,成为永世不得与读者见面的废纸、泥浆。
为了把历史的记忆正常化,学者林贤治主编了声讨“文革”期间盛行的“血统论”的书籍《烙印》。该书从无到有历经12年,其中6年间是在不同的出版社之间流传,因为题材特殊,众多出版社选择了放弃。林贤治在书的序言中说,历史不可能为沉默的人们作证,说还是不说,就成了问题。林贤治举了德国的例子,他说:战后无论是纳粹子女还是犹太人幸存者,在一段时间内都选择了沉默。但在沉默之后,德国能够正视以前纳粹大屠杀的问题,正视那段历史。从那开始,他认为是一个民族灵魂的重生。但非常可悲的是,在中国,人们至今仍是回避历史的。德国通过不断的记忆追溯、保存,把个人的记忆变成社会和集体的记忆的时候,已经把这段记忆正常化,保持了他的记忆的有效性。历史也通过这种记忆呈现出一种稳定性。但是我们还是选择回避和掩盖历史上最为不堪的那一页。无独有偶,学者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与“文革”记忆》一文中也指出:应该说,“文革”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也是一个极为丰富的矿藏。因此,似乎笔者也可以说,“文革”时期的作家作品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也是一个极有研究价值的内容板块。
由于文学表现“文革”这个主题、“‘文革文学”研究这个板块还存在着各种禁忌,以致作家们、学者们在技术层面的表达与探索有着太多的束缚和羁绊,这多少影响了他们对历史伤痛的深入的思考和贴切的表达,也人为地造成文学上的历史虚无主义。随着作家和学者的年龄层次的下降,他们面对“文革”的个人经验越来越稀薄,记忆也成了越来越空洞的形式。人类面对历史的苦难本来就缺乏再现的能力,如果在文学史的层面上再这样刻意地回避和涂抹本该占有一席之地的“文革”文学的存在,我担心再过20年我们的后人将不知“文革”为何物,也不知“文革”文学为何物,这是非常可悲的,也是极其危险的。陈思和说他曾经怀着急切的心情阅读过一部德国学者著作的《纳粹德国文学史》,读完以后仍然感到失望,伟大的德国文学对于这样一场历史灾难,似乎也没有为世界文学贡献出可与文艺复兴时期相媲美的伟大文学,像布莱希特的戏剧和托马斯·曼的小说,基本上也是用变形的手法来铭刻对这个恐怖时代的记忆。那么我们呢,我们难道还要走得比德国文学、布莱希特的戏剧和托马斯·曼的小说更远吗?
(作者单位:深圳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