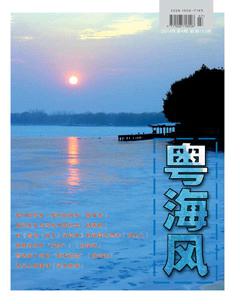《现代评论》如何面对“三一八”
刘希云
现在总是有人感慨北洋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地位高,那时的胡适在北大一个月能拿300大洋,毛泽东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挣8个大洋,而普通工人的工资才2个大洋,差距那么大。但是,我们也看一看那些知识分子在社会有大事发生的时候,做了什么?《现代评论》是1924年创刊于北京的一个集合了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舆论阵地,其中胡适是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三一八”惨案发生于1926年3月18日,《现代评论》给予了及时的报道和评论,正是由于舆论界的声音,才迫使段祺瑞执政府集体辞职。那时的言论界,真正发挥了批评时政的作用。在书生议政和政府的对峙中,北洋政府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并引咎辞职,自由知识分子凭借舆论的力量,用笔打败了一届政府,谱写了现代知识分子言论史上的辉煌篇章。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有骨气有担当,值那么多大洋。
《现代评论》在惨案发生后不久,就在第三卷的68期、69期和70期上进行了集中报道和评论。在68期上,发表的关于“三一八”惨案的文章有王世杰的《论三月十八日惨剧》,陈翰笙的《三月十八日的惨案目击记》,陈西滢的《闲话》,杨振声的小说《阿兰的母亲》,及泉的《三月十八日》,许仕廉的《首都流血与军学阶级冲突》;在69期上有唐有壬的《漆黑一团的时局》;70期上有王世杰的《京师地检厅与三一八惨案》,陈西滢的《闲话》和《杨德群女士事件》,凌叔华的小说《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方面对“三一八”惨案进行了书写。
关于“三一八”惨案,我们有必要追问一下它的前因后果。1926年3月初,奉系毕庶澄率军舰从青岛出发,进攻冯玉祥国民军所占领的天津港大沽口。3月9日,国民军为防奉舰进攻,在大沽口水道铺设水雷,并同时通告领港人,一切商船不得进入。3月10日,英、美、法、意、日等十二国由荷兰公使欧登科为领袖照会北京执政府,抗议国民军铺设水雷、封锁天津海口,认为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保留外国船只的出入自由。大沽口守军鹿钟麟对各国领事进行了解释,并提出外轮入口的三个办法。3月11日晚,日本驻津总领事与钟接洽,提出次日上午将有一艘“藤”字号驱逐舰入口,要求免检放行。双方约定的时间为上午10点,双方的旗号为“C”,入口时须先停泊某地,进港后须缓行。3月12日,日本舰只入港时间不对,舰数也不符。日舰未遵前约,强行闯关,炮台守军令其停进检查,不听,遂施放空枪警告。谁知日舰视为攻击,旋用机关枪扫射,炮台守军猝不及防,伤者十数。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军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7国公使,于16日以公使团名义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京政府。1926年3月16日,北洋政府外务部接到列强外交团之最后通牒后,经紧急磋商并与当日午夜答复,称“最后通牒”内容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所以“认为不能适当”。
3月18日上午10时,北京市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集合80多所学校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抗议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广场请愿,群众派出代表和卫队长交涉,要求开门放游行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双方起了冲突,卫队长下令向游行学生和群众开枪,当场死亡47人,伤200余人,死者有大家熟悉的北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人。后来军警清理现场,竟将死者的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扒光。3月18日当日,段祺瑞及北京国务院通电谓本日惨案乃国民党人徐谦等鼓动所致,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朱家骅、蒋梦麟、鲁迅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李大钊、徐谦、鲁迅等人被迫转移。3月19日各地舆论纷纷谴责国务院门口屠杀。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和道德勇气,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纷纷撰文谴责段祺瑞政府。《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加入谴责暴行的行列。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道惨案真相,《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3月20日,贾德耀内阁因三一八惨案引咎辞职,段祺瑞亦下令抚恤。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可怜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乱如麻”唱遍京城。[1]
王世杰的《论三月十八日的惨案》中,主要论证了这么几点:首先,枪杀为预定计划。在卫队长命令开枪时,实际上绝无开枪之必要;群众逃奔时,卫队尚有长时间的枪杀行为与劫掠行为;此次残杀,是一种预定计划,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实。然后指出元首犯罪的问题,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下,元首犯罪也要同普通百姓一样受法律与法庭的制裁。要认定这些犯罪事实,要紧的是收集证据。最后指出,在通缉令的颁发中,元首和内阁径自颁发,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就是颁布通缉令,也应该是由检厅颁发。现代文明国家没有元首或内阁颁布通缉令的。作为一个法律专家,王世杰主要从司法的角度对惨案进行了认定,并指出执政府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地方。陈翰笙的《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记述了惨案的整个过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听见一位穿便衣的人指挥,说队伍应当退入铁门,‘学生若攻击铁门,那么,我们就要老实不客气了。——我以为若果推出国务院或可免去危险。思索未完,忽闻笛声。笛声未完,卫兵举枪。正在举枪,群众已逃。逃未十步,枪声砰磅。我闻枪声,立即伏地。枪声甫毕,我即见血溅满地。我听见的枪声,都是排枪声,计共两次。我于是急向西滚,滚入停车场。向东窥,见卫队退入铁门内,从栏杆后任意射击。照壁下有女子中弹仰卧。西南操坪的丘八出来用关刀刺入女身,向空中高举再猛力抛掷!于是该女尸落在一丈远的地方。”[2]文中用事实,记录了执政府卫队令人发指的行凶过程。
在陈西滢的《闲话》中,他再次阐明了惨案的真相,“在群众方面,那天参与的人都完全是为了对外,并不是一党一系的运动。群众到执政府,不过是和平的请愿。他们最激烈的行动,也不过是叫几声口号。——在卫队方面,他们在事前已经向新闻记者等吐露口气,表示他们有干一干的决心。他们的行动也可以证明他们的开枪,不是为了仅仅要驱散民众。他们非但在民众四散逃避的时候,在后面追击,并且东西两铁门外,都驻有兵士,向在门口往外拥挤挣扎的人民,迎头开枪,所以死伤在门口的人特别多。”[3]后面陈西滢谈了一点感想,这次死伤者之中,妇女小孩占了一部分。他希望未成年的男女孩童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虽说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他们目下还算不上匹夫,等你们成了匹夫,再来担当吧。这里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
陈翰笙的小说《阿兰的母亲》,用文学性的语言和手法表达了“三一八”惨案给遇害人家庭带来的无法弥补的创伤。阿兰是母亲唯一的女儿,她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成了母亲活下去的希望。她是母亲生活的重心,前几天阿兰发烧,母亲守着阿兰,三晚没睡觉。阿兰的先生在惨案发生后逃出来,看见阿兰的尸首,她想跑去告诉阿兰的母亲,她母亲正在给阿兰作夹衣,同先生谈着这件衣服的颜色阿兰穿上一定秀气,母亲的心里全是阿兰,死里逃生的先生终于没有忍心说出阿兰遇害的事。许仕廉的《首都流血与军学阶级冲突》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谈了他所听闻的不同阶层的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军人的看法是学生仗着父兄的金钱和势力,来进学堂。自己不肯用功读书,寻事胡闹。一开大会,动辄千人。路上交通屡为断绝。对于洋车夫阶级,尤为欺凌,不管三七二十一,口口声声的喊打。商人的意见是国运同家运一样,老官僚和军阀本不足道,但是中国的希望在学生。而他们把书本丢下,今天要放假,明天要起冲突,打倒校长教员。他们老死不愿意读书,当教员的也混蛋,对于学生一点不管。再过十年恐怕中国人都不免要变成男盗女娼好吃懒做。中国不亡,未有天理。政客的看法是学生运动,背后有人主使。利用群众,推翻政府,借某国的金钱和枪械,在国内到处胡闹。天天讲革命,杀人放火,扰乱治安。若稍姑息,愈闹愈凶,我看杀几个人,也许会稍镇定一点。这样看,军政商各界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有很深的积恨。那为什么有这种仇视呢?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在北洋派和旧官僚的眼光中,无所谓社会国家。他们有私人之忠,无救国之义。他们伦理观念极重,忽听说革命平等自由的话,就产生怀疑,因怀疑则生偏见。二是一般青年,虽崇拜自由平等革命的学说,然未深加研究。少青意气极重,常有少数人越出常规以外行动。因少数人的不能自持,学界全体同受冤骂。三是我国人对于公民训练,向来不注重。中国俨然分两大阶级:一官吏,一人民。今忽产出一种所谓学生运动者,一面要指导人民,一面来干涉政府,所以引起双方的怨恨。文章最后说,虽然学生运动遭人忌恨,爱国的学生们还是要一致地奋斗下去。中国的唯一希望在知识阶级。
《现代评论》第69期的“时事短评”栏目,发表了高一涵的短评《惨案的前途黑暗》,指出这种暗无天日的惨案,绝不会在文明国家或法治国家之下发生;既已发生,那么,就可以证明中国绝不是文明国家或法治国家。现政府一日不倒,起诉便是一日无效;杀人犯一日不下政治舞台,在事实上便一日不受法律的制裁。大家不可只记得法律问题而忘记了政治问题,更不可只记得私仇而忘了公敌。
《现代评论》第70期发表王世杰的《京师地检厅与三一八惨案》先是赞扬了京师地检厅能大胆无畏地举发惨案事实,然后督促京师地检厅应继续追究肇事者的法律责任,把现在的元首诉诸法庭,该拘传的拘传,该起诉的起诉,该定罪的定罪。凌叔华的小说《等》写的是“三一八”遇害的学生。作为出身上层的大家闺秀,我们知道凌叔华善写“高门巨族”内的精魂和风波,但是这次作者担起了知识者的责任。文风依然保持着优雅的姿态,作者没有正面写流血的冲突,而是从侧面写出了死亡给爱人带来的伤痛。作品用了反衬的手法,三奶奶和女儿阿秋正为爱人上门做准备,少女害羞而甜蜜的心情下精心准备爱人的来访,三奶奶不顾病体在厨房忙碌。母亲在人逢喜事精神爽的作用下,很是兴奋。女儿也怀想着未来美好的生活。但是时间早过了约定钟点,男主人公还是没来。三奶奶出门打探,作品只用两句话就交代了悲剧的发生,“今早学生们上执政府请愿,街上人说卫队开枪打死了许多学生。——他们学校里死了三个人,有一个是他。”母亲眼都直了,回到家里,不知该怎么对女儿说。前面大量的铺垫、渲染,到后来的等待落空,悲剧发生,然后小说戛然而止。小说在结构上有明显的头重脚轻之感,正像小说给人的整体阅读感受:让人晕眩,猝不及防。结尾留下了大段的空白,让读者去想象。此外还有一篇陈西滢的《杨德群女士事件》的来信,因为他在《闲话》里说了一句“杨女士不大愿意去”,学生们认为这是侮辱了杨德群的爱国热情,陈西滢给予了说明。
这就是“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现代评论》对于这个事件的报道、评述和描写。有头版头条的大篇幅的社论,有短评,有文艺作品,有书信。可以说,“现代评论派”的知识分子在惨案发生后,站在道义立场上发出了及时而有力的声音,为“三一八惨案”的披露营造了摆事实、讲道理的舆论氛围,给当时的执政府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为惨案的政治定性打下了基调,才促使执政府承认过失,及时善后抚恤,发挥了自由知识分子舆论干政的集团力量。
但是惨案的发生却导致了自由知识分子心态的变化。本来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对时局多有批评,但是从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北洋统治时期宪法规定了民众有言论和集会自由,这是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但是自从“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知识分子的心态却发生了变化,一些人觉得虽然执政府在《宪法草案》中规定了民众的言论结社自由,但是他们的卫兵却未必能遵守这一点,对于一个能枪杀学生的政权,他们失望了。这造成了“三一八”之后,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大批知识分子“孔雀东南飞”,纷纷离开北京去南方。这造成了中国思想文化中心的南移。
(作者单位:德州学院)
[1]《京师地方监察厅公函》,转引自《“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2]陈翰笙:《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现代评论》2卷68期。
[3]陈西滢:《闲话》,《现代评论》2卷6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