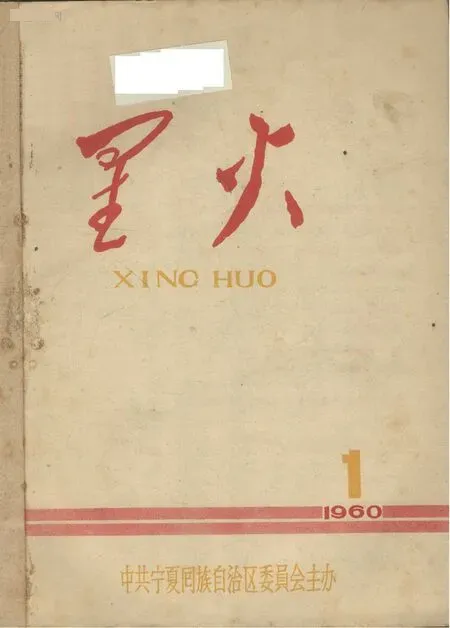钱二连说媳妇
□胡树彬
一
钱家庄钱二连的老妈钱寡妇最近身子不利朗,看了好多医生都不好,找刘家湾的刘阴阳算了一卦,说要冲喜,于是就上街砍来两斤猪肉,打了三斤土酒,拿一斤用输盐水剩下的玻璃瓶装了,叫钱二连提去杨家营的民办教师杨红青家,把他请了过来。
杨红青虽然当过钱二连的几年老师,却从未进过钱寡妇的门。见钱二连亲自来请,才甩着衣裳尾巴跟来了。到家时,钱寡妇已将饭菜做好,请杨红青坐席。杨红青也不客气,坐下就喝酒吃肉,吃饱喝足后才问:“钱二婶,请我来有啥事?”钱寡妇指着钱二连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刘阴阳说,我要冲喜才会好,想请你帮个忙。”杨红青哈哈一笑,说:“我以为是做啥子呢,这点小忙肯定是要帮的。”说着转向钱二连:“钱二哥,你看中了谁?哪村哪寨的?”
这地方没有专业媒人,替人说媒的都是和男女两家有着一定关系的亲戚朋友或寨伍邻居,很多时候只是起个中间人或见证人的作用。“张家沟的,双花。”钱二连说完,杨红青就一愣一愣的,愣了半天又问:“你们,平时说得有话没有?”钱寡妇替儿子说:“有,当然有,我们家请人套过口气的。”
气氛随即沉闷下来。钱寡妇虽然是个寡妇,但人却精明得很,她找杨红青做媒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因为他是双花的大姨爹;而且她还知道,杨红青的亲侄儿杨桥发也去张家套过口气,但还没正式上门去说。果然,杨红青沉默了几分钟才说:“好吧,哪天有空,我就带钱二哥去看看。”杨寡妇连忙说:“杨老师,刘阴阳说这事宜早不宜晚,我想请你今天就去好不?”
钱二连的名字中虽然有个“二”字,但钱寡妇却只有这么个儿子,他排行第二,是把堂哥钱运龙算上的。钱二连的爷爷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又只生下钱运龙一个男孩,于是,这对叔伯兄弟的关系就更近了一层,跟亲兄弟没多大区别。杨红青可以看不起钱寡妇母子,但钱运龙的面子却不得不看,于是沉默了两分钟,说:“明天,明天去行不行?”
钱寡妇笑眯眯的,一边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杨红青,一边漫不经心地说:“我家幺龙说,你家杨桥关的手艺好得很,想把乡里的篮球场包给他去做。”杨红青突然精神一振,眼里放出光来,脸上也露出难以掩饰的喜气,说:“钱二婶,还有我……我家关保是学厨师的……”钱寡妇知道他要说什么,于是接过去说:“双花是你姨侄女,我家幺连要是娶了来,我们不就成了亲戚嘛!古谚说是亲三分顾,这一亲二戚的,乡里的那个食堂,我家幺龙还会给别人?”
杨红青假装犹豫了一下,站起身看看快要落山的太阳,说:“好吧,那就这样吧,我回家换件衣服,钱二哥赶紧收拾好来叫我。”说完就匆匆地走了。
二
杨红青走后,钱寡妇对儿子说:“穿上你哥给的那套灰西装,提着那两瓶五粮液当礼信。呵呵,那两瓶酒还是杨桥关提来送你哥的,想讨篮球场的活干。”钱二连不说话,放下碗就去换衣服。换衣服出来,钱寡妇又对他说:“儿子,你要跟娘长点志气,媳妇说不成不要紧,不要让人瞧不起,更不要吊儿郎当的煮熟的鸭子让它飞!”
可是这些话钱二连一句都不爱听,心想不就是个村姑嘛,又不是大官小爷的千金,有啥吆不起台的?于是漫不经心地提着礼信走了。钱寡妇又跟出来扎咐:“你要记住头回不打狗二回不装烟的老规矩,去了就要赖着脸皮在她家歇,不要看见人家冷屁楸烟的就跑回来了。”钱二连头也不回,钱寡妇气得大骂:“你个卡树桠巴的,连你哥的小脚丫巴都捡不到!”骂够了才抖抖索索地回屋去。
将要落山的太阳懒懒地照着,钱二连穿上那套西装,看上去还真有点人样,走在路上引来大姑娘小媳妇亮闪闪的目光一圈一圈地绕着他旋转。钱二连假装没看见,踢脚甩手地走他的路。路边有群男人在大树底下打牌,也争着跟他打招呼:“钱二哥,要到哪里相亲去?”钱二连站住,说:“到杨家营找杨老师吹牛去。”大家当然知道他是说着玩的,心想这狗日的不就是想去耍杨家姑娘嘛,于是无不哈哈大笑,笑完后有人说:“听说乡里要修篮球场,请跟你哥说一声,让我们去背两背泥巴找两个盐巴钱嘛。”堂哥扎咐过他,叫他不要答应给任何人办任何事,但乡里乡亲的,不好拒绝,于是说:“我家的事情是我妈做主,你们去找她。”众人尴尬地笑笑,说:“算了算了,我们到月亮岩脚挖煤去。”
人们都不愿跟钱寡妇打交道。
摆脱纠缠,钱二连迈开大步,继续朝杨家营走去。钱家庄到杨家营有二里多路,钱二连走到杨红青家的时候,他家正在堆包谷草,两个彭家寨的小伙凹起腰子扛草垛,杨桥关围着一棵椿菜树将包谷草一层一层地往上叠,穿着健美裤白网鞋的杨春花却笑眯眯的,站在院门口看热闹,动也懒得动。
看见身穿灰西装黑皮鞋还扎着花领带的钱二连,杨春花眼里放着光,上上下下地将他打量了三四遍,咂着嘴皮说:“钱二哥,你今天帅得很嘛。”钱二连有些不好意思地别过头,说:“哪里帅?还不是跟平时一个样。”杨春花平时有点看不起钱二连,此时见他还真变了样,于是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不怕脏的话,就帮我家扛草嘛。”钱二连的出现已经引起了那两个小伙的注意,他们看见杨春花的眼睛闪闪发光,对着那身西装释放电流,年纪稍大的那个把草垛一扔,招呼年纪稍小的说:“老幺,扛球不起,走球!”那叫老幺的看看杨春花和钱二连,又看看自己的同伴,也把包谷草扔在地上,说:“走就走,我看干多少活都是白干。”
那俩家伙也真有个性,说走就走,连招呼也不打,直到走出二三十米了杨春花才发觉,于是撇下钱二连,追出去大喊:“彭光学!彭光学!”那叫老幺的还回头看了一眼,那叫彭光学的理也不理,一直往前走。钱二连忍不住笑了,在心里赞道:“嘿嘿,这狗家伙真他妈有志气!”
杨春花回过头来,看见钱二连一脸坏笑,生气地说:“钱老二,都怪你!”钱二连笑得更厉害,但不说话。杨春花只好抱起地上的包谷草,狠狠地鼓了钱二连一眼,说:“不得好死的,还笑!”正在此时,杨红青也换上那套不轻易穿的藏青色中山装走了出来,叫道:“二连,我们走。”
钱二连跟着杨红青走远了,杨春花还在一边拉包谷草一边叽里咕噜地骂,同时又忍不住拿眼去瞟那身西装的背影。
三
张家沟离杨家营还有十里路。由于山太夹,四点多钟就没太阳了。夕阳缓缓地爬山坡,他们不疾不徐地赶山路,杨红青边走边问:“钱二哥,你以前有没有上门去说过媳妇?”钱二连说:“没有,这次是开张生意。”杨红青说:“没有的话我告诉你,去到女方家要懂三(故意把‘四’减去‘一’),还要勤快,看到人家干活就抢着干。在家是皇帝,去到老丈人家就是奴隶。”钱二连却说:“我才不当奴隶呢,我妈说要我长点志气,不要让人瞧不起。呵呵,今天来你家的那俩小子,真他妈有志气,扔下包谷草就走,你家春花怎么喊都不应。”
走在前面的杨红青回头剜了他一眼,见这家伙穿上这身皮还比较顺眼,于是叹息一声,边走边问:“你哥有没有说要给你整个工作?”钱二连说:“没有啊,他没有说过啊。哦,好像是说过,要我去参加抓计划生育,半脱产,但我不想去。”杨红青说:“不去?你为啥不去?”钱二连说:“干那工作逗人恨得很。”杨红青说:“再逗人恨也比挖包谷桩桩强,按我说你不但要去,而且还要把那工作干好,干成全脱产,干成乡干部。”
钱二连不再搭话,杨红青也懒得说。两人沿着山路走了个把多小时,直到夕阳已经爬到山顶了,才来到张家沟。他们走进双花家院子时,双花正坐在晒壁前的屋檐下拉鞋垫,她妈在圈门口喂猪,她爹在一根梨树下逗画眉。另外还有两个小伙子在煤坑边杵煤,已经杵了好大一堆,还在继续杵。钱二连看得出,这两个蛮杵杵的家伙好像不团结,双方都在较着劲。
常言说小姨子有一半是姐夫的,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但还真有几分理,首先发现他们到来的,就是双花的老妈王雀妹。但这次让王雀妹眼睛发亮的不是杨红青,而是钱二连,准确地说,是钱二连的那套灰西装。的确,这方圆十几里除了乡长钱运龙,还没谁穿过这么高档的衣服。王雀妹左手提着猪食桶,右手握着猪食瓢,嘴唇哆嗦地喊:“唉,大姨爹,你们来得畅早?”
“嘿嘿嘿。”钱二连忍不住笑了起来,正要答小姨子话的杨红青回过头来,鼓着眼睛问:“你笑啥子球?”钱二连说:“那女的说话真幽默,我们黑都黑了才来,她还说‘来得畅早’。”杨红青早就听说钱家这个儿子有点吊,但还没想到有这么吊,于是脸一沉,说:“我在路上跟你说过的话记住没?你是来说媳妇的知道不?”钱二连连忙收住笑容,假装正经,杨红青这才打个干咳,哈哈一笑,说:“早吗不早了,但是没摸黑。”
王雀妹连忙喊她闺女:“双花,我手不得闲,赶紧招呼大姨爹他们坐。”其实这时双花已经注意到这两个不速之客了,但她关注的对象却不是自己的大姨爹,而是钱二连。钱二连一贯做事都是大大咧咧的,但在姑娘火辣辣目光的注视下,也不由变得拘谨起来,小脸红得就像西边天上的火烧云。姑娘愣了至少二十秒才反应过来,连忙拉来两张破木椅放在堂屋前面的厅口里,招呼道:“哥,大姨爹,你们请坐。”
正在逗画眉的双花爹听到杨红青的声音,心里一沉,暗道:“这个私儿又来了。”因为他早就听说过,他老婆婚前就跟这个狗家伙有一腿,还怀过孕打过胎,于是对他防范很严格,搞得连襟关系有点僵。但心里再不爽,亲戚来了也得应酬下,于是回过头来,本想跟杨红青打打招呼的,但首先看到的却是钱二连的那套灰西装,心里暗想:“估计又是来说我家双花的。”于是还没当过丈人的他心里惶惶的,转过身子离开画眉笼,朝这边慢慢地走来。
钱二连坐下后,随手把袋子放在地上,从里边拿出两瓶酒递给姑娘。双花见这酒的包装比平时见到的要豪华和怪异得多,连忙小心翼翼地接过来,说:“哥,就这样来算了嘛,还提东西做啥子?”钱二连心里有点小紧张,不敢开口说话,杨红青看见那两瓶酒有点眼熟,心里不由刺痛:“这不是我家前天提去孝敬钱乡长的么?怎么到这里来了?便宜了张金六这狗日的!”
此时已是傍晚,双花抱着小坛子一样的酒瓶走向大房侧面的小平房。钱二连抬起头来,只看见一个娇俏的背影,心里不由怦然一动,暗道:“这妞长得还不错,简直跟杨春花有一拼。”杨春花是他们村里最漂亮的女孩,最近两年来她家“摆寨”和提亲的人差点踏破门槛,为此杨红青轻而易举地收受了不少瓶子酒(但那两瓶五粮液却是他大儿子自个掏钱买的)。本来钱寡妇是打算给钱二连说杨春花的,但她“闺蜜”李伞儿说,她娘家村子里的张双花,比杨春花抻抖多了,人又勤快贤惠,保证是个好媳妇。钱寡妇来劲了,立马央求“闺蜜”:“妹子,那你带我去看看好不?”于是李伞儿就跟老公请了两天假,带着钱寡妇回了趟娘家,对双花进行实地考察。两天考察下来,钱寡妇非常满意,于是请“闺蜜”套套口气,姑娘说只要人家户对头,嫁哪都无所谓。有个乡长侄儿撑门面,钱寡妇心想:“像我这样的人家户,还不算对头?”于是又央“闺蜜”:“你帮我把她扳来,好不?”李伞儿却说:“我打打边鼓可以,做媒却不行。”钱寡妇连忙问谁做媒合适,李伞儿说:“杨家营的杨红青是她大姨爹,此人说媒一定成。”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故事。
等双花走了出来,钱二连再一看,只见她长着一张白净的瓜子脸,五官端正,明目皓齿,果然跟杨春花一般靓丽,在欢喜的同时又有些担忧:这么漂亮的妹子,会看上我吗?突然想起老娘的话,暗道:“生意不成仁义在,不要输了志气让人家瞧不起。”于是坐正身子,昂首挺胸,尽量做出无所谓的样子。谁知他这样一来,姑娘心里更是喜欢,以为这样周屋正房、器宇轩昂的,才是真正的男人,相比之下,那些低三下四地来干活的,就只能是下三滥了。
钱二连此时的表现,连老教书匠杨红青也震惊不已。那两个杵煤的家伙看出苗头不对,于是把杵煤槌一扔,气耸耸地理起褡褡就走,同样连招呼也不打。双花才不稀罕,但还是客气地招呼:“杨哥、陈哥,你们吃了晚饭再走嘛!”那两个家伙却懒得理睬,也不相互说话,出了村口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各回各家去了。对他们来说,不但断了这份心,而且也断了这条路。
杨红青毕竟是过来人,此时也只有叹气的份,心道:“真是人穷气短,这套西装的杀伤力,比那两身蛮力强多了!”
四
此时张家夫妇即使再笨,也知道杨红青和钱二连此行的目的了,两口子都在心里起了不小的波澜。钱二连和杨红青规规矩矩地坐在堂屋厅口欣赏张家沟黄昏时分的美好风景,张家三口却全都走进了大房。点燃煤油灯后,王雀妹吩咐双花:“去楼上下块腊肉来烧,我淘米。”张金六制止说:“饭都快蒸熟了,有啥子就吃啥子,又不是什么高人贵客。”王雀妹心里很不爽,但又不敢擅自做主,只是恨恨地瞥了张金六一眼。双花也看见了,心里有点悲凉,心想找到好人家,就早点嫁出去算了。
张金六懒得理睬她们娘儿俩,旋到屋角落扯出几张老皮烟,提着根竹烟杆走出来,把烟递给杨红青和钱二连。钱二连连忙摆手,说:“谢谢叔,我不会。”杨红青是不抽皮烟的,于是也摆摆手,一边说“我幺姨爹也是,又不是不知道我脾气”,一边摸出带过滤嘴的草海牌香烟,递给张金六一支,自己也点燃一支,心道:“钱二连这个狗日的,不会抽烟就不会买烟?这说媳妇不给人装烟怎么行?”
张金六也不客气,点燃杨红青递来的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烟子说:“我们抽惯老皮烟的,抽纸烟不止瘾。”此时的钱二连已经不再拘谨,接话道:“皮烟还是少抽点的好,抽多了容易得肺癌。”张金六本来就是垮着脸的,听了钱二连的话,脸拉得更长。杨红青连忙伸腿踢了钱二连一脚,示意他不要乱说话,否则这门亲事就说不下去了,同时替他解围说:“是的是的,他爹就是烟瘾太大,年纪轻轻的就得肺癌死了。”
谁知这句话又说漏了汤,张金六的马脸终于垮到地上了,气愤地抬起头来,扭过脸问大房里:“饭做好了没有?”双花答道:“快好了,可以进来了。”于是张金六充满敌意地瞥了眼身边的两个客人,说:“我们家穷,吃的一样不像样,请你们多多担待。”说着就起身往大房里走。
杨红青似乎已经受够了这个连襟的气,有点不以为然,钱二连却傻愣愣地坐着,心想村里人都说老子怪,这个老家伙比老子还怪。杨红青瞥了钱二连一眼,低声嘟哝道:“还说媳妇呢,一点眼色都没有,真是穿坏那身皮。”心里却说:“你连你哥的小脚丫巴都捡不到。”张金六在桌子边坐好了,还不见客人进来,双花连忙出来请:“哥,姨爹,请你们上桌子吃饭。”
夜幕开始降临,对面寨子暗沉沉的,只有几扇窗口发出微弱的灯光。进到屋里,杨红青挨着张金六坐了,钱二连只好挨着双花坐下来,因为气氛有点不和谐,于是看着那盏挂在桌子上方的煤油灯发呆。双花看见了,说:“哥,我们这里是老高山,点不起电,你肯定不习惯。”钱二连回过神来,淡然一笑,说:“没什么不习惯的,五年前我们村里还不是同样点煤油。”杨红青见机会来了,连忙插话道:“钱二哥,等过几天去了乡政府,请帮我弄几颗节能灯来,我家用电量大得很。”
一直垮着脸的张金六不由一愣,抬眼望望钱二连,阴阳怪气地问:“这位哥,是乡——政府的?”钱二连的脸立马就红了,热辣辣的,杨红青连忙向他使眼色。但钱二连不想骗人,说:“我——我不是乡里的干部。”张金六回脸看了眼杨红青,鄙夷地笑了下,说:“大姨爹,你们教书匠靠的就是耍嘴皮,但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招,我已经不再是小学生。”此时王雀妹已经开始上菜。当然不是什么好菜,只是两缸钵洋芋片,不过看上去油汪汪的,香气扑鼻。钱二连接话说:“我虽然不是干部,但我哥在乡政府上班,我经常去他那里玩。”
张金六又一愣,问:“真的?”钱二连说:“怎么不真?我这套西装还是他穿过的呢!”“哈哈!”张金六忍不住笑了出来,连双花和刚刚端着酸菜锅走过来的王雀妹也忍不住笑了。杨红青一边尴尬地跟着笑,一边在心里骂:“小狗日的,老子没想到你居然笨到这个地步!”
不过钱二连的反应也还算比较快,接着又说:“他只是帮我试了试,他比我长得高,穿上去怪怪的。”说着还站了起来,左摆摆,右弄弄,说:“你们看合不合身?一百八十多块钱买的呢!”
这下,张金六一家和杨红青却怎么也笑不起来了,他们的笑容全都僵在脸上,就像拿石头雕成的一样,因为一百八十多块钱,差不多是杨红青半年的工资,张金六家则要卖头小牯牛或两只半槽猪。这还不算,钱二连又蹬蹬脚说:“我这双擦油皮鞋,七十多块钱,哎,贵是有点贵,但穿起舒服。”
七十多块钱?那已经是一个公办教师半个多月的工资了,杨红青的月薪才三十五块呢,他一直想买双皮鞋,可整整十年过去了,这个梦想一直没法实现,心里嫉妒得不行,白了钱二连一眼,怪腔怪调地说:“不要显摆了,我们是来走亲戚,不是来表演,吃饭吃饭。”于是大家便端起碗就吃。
张金六虽然被钱二连的西装皮鞋和嚣张邪乎的性格镇住了,但由于心里对杨红青存有芥蒂,脸色依然有些冷漠。王雀妹想招呼杨红青多吃点又不敢,心里虽然明白姐夫是带这个小伙来相亲的,对钱二连的印象也还过得去,但见自家男人不感冒,也不敢多言。倒是双花,最近两年见惯了形形色色的男人,却没见过像钱二连这样有个性的,不由怦然心动,对他有了好感,觉得没拿酒肉大米来招待有点过意不去,于是有些怨恨地看了张金六一眼。
张金六也看见了双花看他的眼神,当然也明白她的心思,于是重重地把半碗包谷面饭放在面前的桌子上,招呼也不打,起身拂袖而去,搞得杨红青、钱二连及双花母女愣眼愣眼的。张金六摔门走了,杨红青才说:“我幺姨爹的脾气是越来越怪了。”王雀妹气愤地说:“这个砍脑壳的,就是长了个脏脾气,也不管有没有客人来,都是这个尿包样。”双花更觉得不好意思,笑了笑,对钱二连说:“哥,我爹就这个脾气,你心里不要有想法。”
钱二连能有什么想法?人家姑娘还不一定愿意嫁给你呢,过了今天,也许以后再也不会来了,于是也没往心上去,只是替双花母女感到不值,心想这么好的姑娘,偏偏碰到了这么个爹;这么好的女人,偏偏摊上了这么个男人,真够倒霉!然后看看王雀妹,再看看双花,突然生出一个想法:“难道这家人没有男孩?如果——如果只有一个独生女,就算她愿跟我好,我也不敢跟她好呢。以后天天跟这么个老头打交道,不被气死也要被烦死!”于是试探性地说:“说到哪里去了嘛,幺妹,人人都有脾气的,只是有的人脾气比较怪而已。哦,你家哥哥呢?他们怎么不来吃饭?”
双花见他并不介意,于是放宽了心,说:“我大哥二哥读不了书,都出门打工去了,在昆明做冷库发蔬菜。”哦,原来如此!钱二连心里释然了,脸上露出笑容,于是把碗放在桌子上,从西装口袋里摸出一包硬壳壳的驰牌烟和一只气体打火机,掏出一支递给杨红青,自己也点燃一支叼在嘴上。杨红青一般只抽三毛钱一包的小草海,出门做客才抽八毛钱一包的大草海(带过滤嘴的),而驰牌,要三块五一包,他不要说抽,连见都很少见到,此时一见,眼睛瞪得又大又圆,把烟接过来后,翻过来翻过去地看了好几遍,还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钱二连其实也会抽烟的,只是没烟瘾。他将烟子吸进嘴里,又慢慢地朝着天上吐出来,做出很惬意的样子,说:“饭后一根烟,强如是神仙。”
杨红青很舍不得抽那支驰牌烟,于是问:“有这么好的烟刚才怎么不掏出来?”钱二连笑笑,伸手入怀,又摸出一包,递向杨红青说:“杨老师,这包没开过,原是给你准备的,路上忘了给你了。”杨红青不好意思接,手伸了出去又缩回来。钱二连劝道:“哎呀,老师,你就不要嫌弃嘛,虽然只是三块多钱一包。”杨红青还是不好意思,手再次伸出去又缩回来。钱二连假装说:“杨老师不要肯定是嫌不好。”说着就把烟收了回去,放回衣袋里。杨红青心里一凉,肠子一疼,气得嘴青脸干,眼睛恨不得钻进钱二连的西装口袋里。
双花对钱二连的第一印象本来就好,现在见他抽的居然是三块多钱一包的香烟,更是觉得了不起,心差点跳了出来,两眼放着光芒,在钱二连与杨红青之间移来移去。王雀妹心里同样喜滋滋的,暗想:“这下我家双花有出路了。”
五
吃好饭后,寨上有两个姑娘来玩,双花就邀请她们和钱二连一起来到自己的闺房打双升。由于张金六躲开了,杨红青又不能跟年轻人一起玩,就默默地坐着抽烟,看王雀妹刷锅洗碗。沉默了几分钟,杨红青忍不住开口说:“这么大年纪了,我幺姨爹的脾气硬是改不了。”王雀妹叹了口气,说:“要说他是个猪虚泡,他又吹不胀。大虫二虫就是看不惯他的脏脾气,才早早就出门打工了,三年了,都没回来过,连信也懒得写一封。”说着说着,王雀妹就哽咽起来。
杨红青叹息一声,安慰她说:“万般都是命,由命不由人,等双花找到好人家,你就搬去跟她住吧,受了半辈子气,也该消停消停了。”王雀妹的眼泪又出来了,想说什么,但犹豫了一下,又不说了,擦了擦眼睛,问:“跟你来的这个哥,家里怎么样?”杨红青冷笑一声,说:“他呀,外面耍牌子,家里搅糨子。”王雀妹心里一凉,叹了口气,说:“儿子娶不进来是家门不行,姑娘嫁不出去是亲戚不行,来提亲的倒也多,只是都不咋样,大姨爹,你要费费心帮双花介绍一个。”杨红青说:“有好的还用说?”王雀妹忍不住又说:“这个穿西装的哥,看上去还算周正的哦。”杨红青又是冷笑:“你是看他那身皮罢了,不知道他的家底。”王雀妹追问:“他家里怎么样嘛?你说我听听。”杨红青说:“那我跟你说,他爹早死了,两个姐姐也出嫁了,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娃长大,家底能好么?”
这句话说得王雀妹的心里更凉,她也叹息了一声,说:“他不是有个哥在乡政府工作么?”杨红青说:“有是有一个,但不是亲哥,是堂哥。”王雀妹不再伤心了,把头一昂,说:“是这样的话,你还带他来干啥呢?我家双花长得周周正正的,不说找个干部嘛,好歹也要找个教师,至少也要找个干部子女,怎么连寡妇的儿子你也带来了?”杨红青此时还在恼恨钱二连耍他,于是尴尬地笑笑,说:“我哪里想带他来?是那钱寡妇三天两头的死缠,我摆脱不得,今天是星期六下午不上课,心里想看看你,就顺便把他带来了。情况就是这情况,你们看着办吧。”
不料他刚说完,张金六就一脚踢开门进来了,吓得王雀妹和杨红青都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还好,他们一个规规矩矩地抽烟,一个正在抹桌子,相隔有四五尺。张金六提着烟杆,铁青着脸,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就转身出去了。张金六走到平房门口,悄悄地从半扇开着的窗户往里看,见几个年轻人正玩得欢。本想进去喊他们各自回房休息的,但犹豫了半天,还是摇摇头,叹息一声,回自己的房间去了。躺在那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张金六一边抽老皮烟一边想:“这个小伙子看上去还算周正,人也对我脾气,就是不知家底怎么样,过两天托个人打探打探,那狗日的教书匠靠不住。”
正自想着,王雀妹进来了。张金六问:“你们说够了?”王雀妹一边解围腰脱袖套一边说:“说够了,他说这小伙是外面耍牌子家里搅糨子,还是个独儿,孤儿寡母长大的,没啥家底,死缠着要他带来,明天给他个断心话,叫他以后不要再来了。”张金六却不这样想,但又不愿将真实的想法告诉王雀妹,于是说:“断啥子心啊?你说!那教书匠的话你也信?反正我是不信的!你相信他就跟他去吧,反正他又是个寡公汉,你们正好麻绳断了草绳接。”
王雀妹本想骂他几句的,但又怕搞打起来影响不好,于是忍住了,说:“都这么大年纪了,半身都钻泥巴了,儿大女成人的,你还是这副脾气。”王雀妹嫌钱二连家底不好,张金六倒是想把双花放给他了,心里也不想把场火闹大,于是压住火气说:“放姑娘的事情我做主,一个妇道人家不要跟老子啰嗦,把我惹毛了烟巴斗扯起火闪来不认人。”王雀妹也猜透了他的小心思,想忍却怎么也忍不住,说:“我只有这么个闺女,你那脾气又脏,我不能让你误了她终身,像老娘这样一辈子暗无天日。”张金六脾气本来就不好,她这样一说,终于爆发了,跳起来吼道:“你是说老子误了你终身喽?唵!当初你一进老子家门,老子不是说过不惯就滚,你怎么不滚?是不是你野汉子来跟你长威风要收拾起老子来了?”
这句话正戳中王雀妹的痛处,恼羞成怒的她也跳了起来,撒泼骂道:“张金六你个屁私儿,你终于说出来了啊?今天当着我姐夫的面你要跟我说清楚,我们到底怎么了?”骂着骂着就扑了上来,和张金六撕扯在一起。关于王雀妹和杨红青的风流韵事,张金六也只是猜测和听说,并没有真凭实据,况且还是在他们结婚前发生的,上不了台面。只是这股窝囊气在心里窝了二十几年,一旦爆发也不容小觑,于是挣脱撕抓后,抡起烟杆狂风暴雨般地朝王雀妹砸去。
杨红青、双花和钱二连等听到王雀妹的喊叫声,都一齐跑了过来。杨红青大吼一声扑向张金六,一把扯过他手里的烟杆,抓住两头使劲一折,“嗒”的一声断了,然后向着张金六一甩,里面的烟油全都洒在张金六的脸和衣服上,呛人的臭味弥漫着整个房间。双花也哭叫着扶起躺在地上打滚的王雀妹,把她拉进自己的房间,母女俩抱头痛哭。张金六有点清醒了,觉得在未来的女婿面前闹这么一谱有点丢人,于是拉衣服擦擦脸,转身摔门而去,留下杨红青和钱二连竖耳竖耳地干站着,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六
事情闹到这一步,钱二连说媳妇的事情已经没戏可唱了,那两个姑娘走后,双花安慰下母亲,就打来热水,叫杨红青和钱二连洗脚。当晚两人被安排在另一间平房里睡。两人同床异梦,辗转反侧。钱二连虽然看样子有点吊二,其实还算个孝子,心想老妈也太迷信了,非要冲什么喜,这个姑娘看上去还行,只是这个家庭也太那个了。不过又想,我要娶的是姑娘,她爹娘谁管得了那么多?他们是有儿子的,又不要你跟他住。整整一个晚上,钱二连都在娶与不娶双花的事情上矛盾着,交锋着,直到老天要亮了,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这一晚,杨红青心里同样不好受,一方面张金六二十几年了还很在乎他和王雀妹曾经的“恋情”,让他很没安全感;二是钱二连这个狗日的,居然敢耍他。他也想过大儿子想承包篮球场和小儿子想承包乡食堂的事,但想来想去,心里的这口恶气还是难以除去,于是打定主意:别让这小狗日的好事得逞!整整折腾了两三个小时,杨红青才沉沉睡去,一觉睡到太阳出山,等他醒来时,张金六和王雀妹早就下地干活去了,钱二连却睡得像死猪一样。
家里只剩下双花。双花原本对钱二连是有好感的,也曾经在心里幻想过和他结婚后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家庭她实在无法待下去了。可是,太阳都照平了他还不起,她心里越来越凉,于是也断了心肠,懒得理睬他们,挎着花篮打猪草去了。直到双花打了一篮猪草回来,钱二连才睡醒。这时张金六已经走在回家的半路了。钱二连连忙穿上衣服,开门出来,双花正在水管边洗猪草,抬头看看他,本不想说话的,想想过意不去,于是干咳了一声,问:“哥,怎么不多睡一会?”钱二连不明情况,依旧大大咧咧地说:“睡不着了。杨老师呢?他哪里去了?”双花说:“他呀,回家去了,你现在撵他,估计还撵得上。”
听姑娘的口气不对头,钱二连摸着后脑勺傻傻地站着,半天挪不动脚。姑娘突然想起什么,连忙返回房间,提出那两瓶五粮液,说:“哥,我家没人会喝酒,麻烦你拎回去。”钱二连再傻也明白了,他们的事情已经泡汤了,心里一凉,暗道:“老子比那两个杵煤的还不如!”但为了风度,还是摆摆手说:“算了,生意不成仁义在嘛,才七八十块钱一瓶,就留给你爹喝了吧。哦,这种酒一般人是喝不起的,你留下吧,以后需要找人办大事的时候,也好做个礼信。”说到这里,钱二连想起老妈的话,媳妇说得成说不成都要有点志气。对,志气!人活着,就要有点志气!于是钱二连看了看花朵般的双花一眼,就转身走了,反正那两瓶酒又不是自己掏钱买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必要心疼。
双花听他说这酒要七八十块钱一瓶,当时人就呆了!天哪,七八十块钱是啥概念呀!差不多要卖一头半槽猪了!听说幺姨爹教一个月书也才三十五块钱呢!双花傻傻地站着,一动不动,直到钱二连走远了,才回过神来,追上去边跑边喊:“哥!哥哥!钱哥哥!”钱二连听到了,但心里的那个声音却比双花的喊声更大更有力:“人要有志气!一定要有志气!不要连个杵煤的都不如!”于是钱二连加快脚步朝前走去,几乎是在小跑。双花追不上,就抱着酒瓶一屁股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双眼无神地望着那身西装潇潇洒洒地远去,一个劲地在心底责怪自己。
村小学一个叫马翩山的年轻教师刚好路过,看到那两瓶酒,吃惊得瞪大了双眼,看看双花,又看看酒盒,半天不肯离去。双花是名副其实的村花,那马翩山爱慕已久,也请人上门说过,老的同意,但双花不同意,嫌他邋遢,身上随时都有粉笔灰。双花回过神来,厌恶地瞥了马翩山一眼,问:“你没见过大姑娘?还没看够是不是?”马翩山红着脸,讪讪地说:“谁看你了?我是看那两瓶酒。”双花把酒往前一送,问:“你不是在城里喝过几年稀饭(师范)吗?你认认这是什么酒?”马翩山好不容易才逮住机会,连忙伸手接过来,说:“凡是识字的都知道,这是五粮液啊。”双花说:“我虽然只读到小学五年级,但也认识这三个字,就是不知道它好不好。”马翩山卖弄道:“谁不知道这是跟茅台一样的好酒啊,我一个月工资还买不起两瓶!在哪里捡来的呀?”
姑娘生气地把酒抢过来,说:“捡来的?你家运气好的话也捡一瓶给我看啊!”说完白了他一眼,又看看逐渐消失在山路尽头的那身西装(此时只是一个黑点),有些失魂落魄地起身往回走。马翩山明白了,冷笑一声道:“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钱家庄的钱吊二!”原来钱二连跟马翩山是初中同学,他们刚刚还遇见了,不过是马翩山先跟他打招呼。钱二连当然知道,这狗家伙最喜欢狗眼看人低,以为考上个小师范有个小工作就高人一等了不起,平常不会主动跟平头百姓打招呼,他能主动喊他,主要是看在堂哥的份上,于是也礼节性地招呼下,就匆匆忙忙地往前走。
看看对自己不屑一顾的姑娘,又看看即将消失在山道尽头的钱二连,马翩山不由仰天长叹,自言自语地说:“鲜花,就是这样插在牛粪上的。”
七
杨红青回到家里,已是早上九点多钟了,大儿子杨桥关过来说:“爹,昨天钱二婶来摆寨,说钱乡长已经答应把乡政府的篮球场包给我了。篮球场加上那段路,弄得好会有两三千净润,这下建新房的钱就有了。关键是,你帮他家的事情怎么样了?”杨红青愣了愣,毛毛汗就出来了,问:“我——我帮她家什么忙?”杨桥关没有发觉父亲的异常,说:“钱二婶不是请你带钱二连去说双花吗?事情怎么样了?这门亲要是开得成,你转正的机会就大多了,听说只要钱乡长到教育局打声招呼,你的指标就有了。”
杨红青教了二十多年民办了,做梦都想转成公办教师。其实跟他一发的民办教师已经有两批转正了。当初叫他去读省中函(省中等师范函授学校),他嫌麻烦,加上还要浪费精力花费钱,所以没去。结果省中函毕业的,第一批就转正了,他心里那个悔呀,简直没法形容;也曾经有人劝他过语数双教材关(按规定只要过了一关就OK),他过了语文,同样嫌麻烦,说不必多此一举,结果第二年教材过双关的人全转正了,他心里就不止是悔了,还有恨,恨自己命不如人。此时听大儿子说只要帮钱二连说成双花,不但能顺利拿到工程,自己转正的事情更是稳上加稳,于是心里的那个悔和恨呀,简直没法形容,但又不敢跟儿子直说,只好敷衍:“二连还在幺姨妈家呢,我回来拿点东西,马上就回去。”
杨红青假装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又匆匆忙忙地往张家沟赶。杨红青走得很急,几乎是小跑,边走边在心里祈祷:“菩萨保佑,钱二哥还稳在那里。”可算路不跟算路来,刚刚走到半路,山路一转,钱二连就出现在他面前。他连忙一把拉住甩秧甩秧的钱二连,气喘吁吁地说:“钱二哥,你怎么回来了?我是回家来找东西的,我们赶紧回去!”钱二连淡淡地说:“人家不喜欢我,还回去干嘛呢?说媳妇就跟要小狗儿一样,东家要不成就到西家嘛,有什么大不了的?”杨红青着急地说:“二哥你说什么话呢?这个事情是有老规矩的,头回不打狗,二回不装烟,但那都是女方家故意装的,你这样聪明的人又不是不懂,他们是在考验你!”钱二连冷笑道:“哈哈,考验我?你以为我不懂?他家都把我提去的礼信退回来了,还是考验我?”按规矩,表演头回不打狗二回不装烟那是故作矜持,也可以说是考验男方的诚意,但都是在不退礼信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退礼信,那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死了心吧,我家姑娘不会放给你!
眼见敷衍不了钱二连,杨红青也没办法了,只得仰天长叹。钱二连看了看神色凄凉的杨红青一眼,说:“杨老师,双花把酒还给我,我没接。那酒还是你家杨桥关提去送我哥的呢,那么贵的两瓶酒,够你教半年书。反正这门亲是开不成了,如果心疼的话你就去提回来,以后有转正机会时还可以提去找人帮帮忙。”杨红青没想到事情会落到这一步,软软地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又长长地叹了口气,才弱弱地问:“钱二哥,你是在替你哥退我家礼信吗?”钱二连见他如此可怜,哈哈一笑,说:“杨老师,男子汉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怎么能这样呢?如果我妈问起,我就说是我自己看不上双花。”
钱二连这样一说,杨红青的心里就舒坦了些,此时再看钱二连,居然比以前顺眼多了,心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干脆把春花放给他算球,开个靠背亲比认个转弯亲强多了!”这个想法刚刚形成,杨红青就挺直脊梁,看着钱二连的西装说:“二哥你说得对,咱们东方不亮西方亮,说不成双花,我再帮你说个更好的。虽然一亲二戚的,但她家做事情的确太气人,不能便宜了他们。你在这里等着我,我去把酒提回来。”钱二连觉得杨老师这把年纪了还玩这招也真好玩,于是哈哈一笑,说:“好,那你快去快回,我在这里抽烟等你。”说完伸手入怀,掏出包驰牌来,一看是没开封的,随手扔给杨红青,说:“杨老师,这包烟原本就是你的,被我多包了一晚上,拿去装支给你那个幺姨夫,量死他!”
伸手接过那包魂牵梦萦向往已久的驰牌烟,杨红青不由激动得双手乱抖,心想二哥啊,你昨天要是这样慷慨的话不就好了嘛,哈哈!
八
半个小时后,杨红青终于气喘吁吁地返回张金六家。双花正在圈门边喂猪,抬头看见他,问:“大姨爹,你还没回去?”杨红青一愣,说:“我在你们寨上的张金有老师家摆寨呢,老朋老友的一年难见几次面,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接着假装东张西望,问:“钱二哥呢?”双花茫然地问:“哪个钱二哥?”杨红青说:“就是我带来的那个小伙呀。”双花脸一红,眼里流露出伤心的神色,说:“他——他回去了。”杨红青假装愣了一下,又问:“你家退他礼信了?”双花低着头说:“没有啊,没有。”说完为了转移话题,就踢了那个抢食吃的大半槽猪一脚,骂道:“猪瘟收的,抢啥子抢?”杨红青心里骂道:“哼,还看不出嘛,这家老的小的都不是好东西,还挺会装呢!”
杨红青在心里骂完后又老着脸皮说:“双花,你都十八九岁的老果果了,规矩应该是懂的,既然看不上人家,就应该退人家的礼信。”双花毕竟还嫩,不是杨红青的对手,事情一被说破,脸就更加红了,毛毛汗也出来了,弱弱地说:“我没有看不起他,是他自己要走的。”杨红青在心里冷笑:“好你个双花,小小年纪就想跟我玩阴的。”于是又说:“双花,人是大姨爹带来的,生意没做成也不能怪谁,怪只怪你们没缘分,按照规矩,礼信是要退给人家的,不然我们就要被挖脊梁骨。这样吧,拿来给大姨爹,我帮他带回去,挨邻槛近的也好有个交代。”
通过这番交锋,双花就彻底败阵了,嘴往平房方向一扭,说:“在我房间,自己去拿。”说完就哭了起来。杨红青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心肠,来到双花房间,找到那两瓶五粮液,再找条布袋装好,拎了出来。双花泪眼婆娑地望着他,他远远地对双花说:“双花,大姨爹带来的你看不上,我也不能怪你,萝卜酸菜各有所爱嘛,大姨爹真心祝福你能够嫁个县委书记的公子,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说完转身就走,匆忙的脚步有点逃跑的嫌疑。
双花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搞得那两头猪也跟着情绪低落,小的那头突然一嘴把猪食盆掀翻。双花止住哭声,随手抓起棍棒,狠狠地砸去,边砸边骂:“你个老狐狸,看老娘不砸死你!”那猪吃痛,惨叫一声,逃回圈去了,另一头也跟着逃进去。双花关好圈门,张金六就挎着花篮,扛着锄头,拱耸拱耸地回来了,问刚刚擦干眼泪的双花:“钱二哥起了没?”双花面无表情地说:“走了。”张金六愣了下,问:“你退他礼信了?”双花点点头,说:“太阳都照平了还不起,我看不惯,就退了。”张金六白了她一眼,骂道:“你个狗啃的,也不看看事路,懒人自有懒人福,天天起早摸黑的穿得起西装吗?提得起好酒吗?我刚刚碰见马老师了,他说那五什么酒,要七八十块钱一瓶呢!还有你知道那个钱二哥是什么人吗?马老师说,他就是钱乡长的弟弟钱二连,马上就要到乡政府上班,半脱产干部,三两年就能转正,说不定十年八年后,现在的钱乡长变成钱县长,他摇身一变,就是钱乡长了。”
张金六说完,把花篮锄头一扔,坐在厅口里气得胸脯扯风箱。双花心里那个悔呀,简直没法形容,连忙跑回自己房间,关上门躺在床上又“嘤嘤嘤”地哭起来。王雀妹提着薅刀回来了,刚刚进院子,张金六就跑过去一把抓住衣领,本想扇她一耳光的,看着她眼里的血丝,心肠一软,放下手来,长叹一声说:“没奔头了,老子也出门打工去。”说完转身走向那根梨树下的画眉笼。那只画眉听见他的声音,闻见他的气息,老早就在笼子里上蹿下跳地欢叫着。
九
一个多小时后,杨红青又回到与钱二连相遇的地方,可钱二连已经不在了,大石头下面留有两个香烟头。杨红青捡起烟头一看,心里不由一沉,原来不是带把的驰牌,而是短支烟,并且还是合作。“合作合作,一元一条;买上一条,奖赏一包!”想起街头小贩的这串吆喝声,杨红青不由自主地把手伸进衣服口袋,把那盒硬壳壳的香烟摸出来,白色的壳子上印着一个烫金的隶体字:“驰!”再看看那精美的包装,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烟,绝对是真烟。”杨红青在心里说,同时又看看手里用布袋装起来的酒,突然明白了,这烟跟酒一样,都是别人送给钱运龙钱乡长的,搞不好连那套西装,也是别人送给钱乡长的,钱乡长喝不掉、抽不完、穿不下,又拿来送给堂弟钱二连!
想通这一节,杨红青就释然了,更加坚定决心要把女儿杨春花嫁给钱二连。他在心里想:“找到这个好姑爷,以后钱乡长用不完的好东西,至少有一半是我老杨的,呵呵。”杨红青笑了,这一刻他居然没有想起大儿子承包篮球场、小儿子承包乡食堂和自己民办教师转正的事,更没有想起春花今后的幸福生活,他脑袋里装满的,只有五粮液、茅台酒、西装和驰牌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