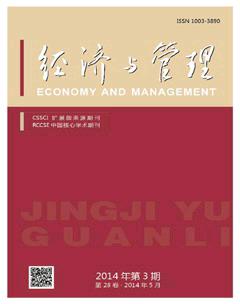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及其影响因素
陈卫+靳永爱
摘要:本文在微观视角上考察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情况,分析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发生的水平和影响因素。根据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计算,1990年以来违反政策生育的比例为18.95%,但不同人群和不同政策类型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在控制宏观和中观因素的条件下,回归模型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微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个人特征显著影响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发生,同时,社会环境、家庭因素也具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完善生育政策具体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政策类型;生育行为;性别偏好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4-0118-1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13
作者简介:陈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靳永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How Well Has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Worked: A Micro Level Analysis
CHEN Wei1, JIN Yongai2
(1.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unauthorized fertility behavior using the 2005 National 1% Population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the national rate of unauthorized births averaged at 18.95% over the last 20 years. The rate for different policy areas varies substantially. Factors at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unauthorized fertility behavior. This research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revising and improving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Keywords:family planning policy; types of fertility policy; fertility behavior; sex preference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又一重大举措。
政府部门希望通过政策调整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时期人们的生育意愿,但事实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对不同人群的作用和影响程度却是不一样的。多数人会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在政策范围内生育,甚至有调查表明,在一些地区如江苏,尽管政策规定的一些人群有生育二孩的权利,但仍有很多人只生一个孩子[1]。但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违反生育政策,特别是农村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普遍。一些研究发现农村多胎率较高[2];有研究者调查发现一些地区出现二胎超生热现象[3]。因此,当前正值政策进一步调整完善时期,对以往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分析违反政策生育的原因,加深人们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认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区环境、家庭经济状况、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等都是影响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国内外有大量关于生育行为的研究,但专门研究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却很少,仅有的一些也只是简单地、描述性地分析原因,提出对策,而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撑。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利用全国大型调查数据和定量方法,在合适的理论指导下研究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在控制宏观和中观因素的条件下,考察影响该行为的微观因素,分析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形成机制,力图为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分析框架
目前解释生育转变的理论有三个:人口转变理论、微观经济学理论和低生育模型。人口转变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了人口转变的发生,其核心思想是发展促进生育率下降。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的阐释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是解释影响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社会经济因素的理论基础,也是选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自变量的依据。同时,人口转变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为本文分析中国妇女生育行为的区域差异性奠定了理论基础[4]。
生育的微观经济模型从家庭或个人决策的角度探讨生育行为和生育观念的转变,主要包括莱宾斯坦的孩子成本效用理论、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伊斯特林的供给需求理论、考德威尔的财富流理论。这些理论均从经济学中的理性决策角度阐释家庭的生育决策,分析孩子的成本和效用的变化是如何促进生育行为转变的,虽然是通过观察生育行为的时间演变创立的理论,但是从空间角度也是有解释力的。这为本文选取变量和解释实证数据结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人口转变理论和微观生育经济学理论提到的因素只能间接地通过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来影响生育行为,而邦戈茨(Bongaarts)提出的低生育模型则从一个更为直观的和直接的层面解释了个人的生育行为选择[5]。他提出生育率由非意愿生育、孩子死亡替补效应、性别偏好、进度效应、不孕效应、竞争效应和意愿生育数共同决定,前三个因素会导致实际生育水平提高,后三项则对生育水平有抑制作用。随着避孕技术的普及,非意愿生育减少,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也使得替补效应减弱,而不孕效应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进度效应、竞争效应、性别偏好和意愿生育数直接影响了我国妇女的生育行为,而最直接的决定因素又是性别偏好和意愿生育数。
以上三种理论分别从宏观、微观以及中观提供了生育行为转变的解释,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相应的也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寻找。宏观的社会环境(包括现代化发展程度、生育政策和文化制度)作用于中观的家庭因素和微观的个体,既影响家庭和个体的特征,也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同时,社会环境、家庭因素和个人特征综合作用,又导致不同家庭的孩子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效用,同时使人们形成对孩子成本和效用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特定的性别偏好和意愿生育数量,最终形成实际的生育行为,即生育数量和性别结构。
二、数据和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此次全国性的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覆盖全国各省市区,样本量大,代表性强,而且是按家庭户进行调查,对家庭基本信息、家庭子女状况和其他一些关键的个人社会经济变量都有涉及,在缺乏确切的出生登记数据和计生数据的情况下,是研究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最佳选择。
1.概念界定
本文的研究主题——违反政策的生育行为,仅指在数量上超过了政策的规定,即只能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了两个或以上的孩子,能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生育了三个或以上的孩子,实行“一孩半”政策的人群第一孩生育了男孩还继续生育,或者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但生育了三个及以上的孩子。本文的违反政策生育不同于计生部门所说的“计划外生育”,计划外生育除了从数量上判定外,还包括违反其他规定,如未达到政策规定的二胎间隔等。受数据限制,本文只从数量上识别违反政策生育行为,无法考虑生育间隔、生育年龄等计生部门规定的其他指标。
2.样本选择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虽然是按户登记,但数据最终以个人形式呈现,因此需要进行配对,将个人数据转化为家庭数据。本文研究的是妇女的生育行为,因此,数据配对也以妇女为基础进行,将孩子信息、丈夫信息和妇女信息进行配对。配对数据使用的是2005年小普查数据的20%样本,因为数据是按个人而不是家庭抽样,配对时会出现三类情况:一是母亲和孩子信息完全配对成功;二是只有孩子信息,抽样时母亲漏掉了;三是漏掉了部分孩子的信息。第二、三类数据由于信息不完整,无法进行分析,第一类母亲和孩子信息均完整的则是本文的分析对象。识别一个家庭的所有孩子是否都在数据中,通过对比变量R34填写的“存活子女数”和数据配对后计算的家庭孩子数,二者相等则可以判定孩子信息没有被遗漏。由于是随机抽样且样本量大,所以有遗漏对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年龄35岁以上、1990年以后生育第一个孩子、夫妻均为初婚和汉族且非流动的女性。主要原因如下:①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不断调整的时期,各省在遵循中央精神的前提下,根据各省
实际情况制订计划生育条例,20世纪90年代初,各地生育政策基本稳定。②我国对于少数民族、再婚夫妻的生育政策规定相对更为复杂。③本文研究违反政策的生育行为,对于尚未走完生育期的女性无法衡量其是否有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已经发生了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除外)。35岁以上的妇女基本完成了生育,可以认为达到了终身生育水平[6]。④1990年以后生育的第一个孩子在2005年最大只有15岁,正处于上初中或高中阶段,不会因为外出打工或上大学等原因而在调查时户口不在户内,这使得对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和结构判断更为准确。⑤我国生育政策实行的依据是户口所在地而非居住地,无法获得流动人口户口所在地的详细信息,无法判断流动人口的生育政策类型,因此,本分析中不考虑流动人口。最终的有效样本量为36976个。
3.因变量的设置和操作
本文的主要因变量是“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生育”,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将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赋值为1,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赋值为0。
因为涉及行为与政策之间的关系,需要详细考虑各地区的政策类型。我国的生育政策基本可以归纳为:城镇居民(不包括少数民族)实行一孩政策;农村居民(不包括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又分为三类,一是北京、上海等地实行一孩政策,有五个省
(海南、宁夏、青海、新疆、云南)
和四个试点地区(恩施、酒泉、翼城、承德)实行二孩政策,有19个省、自治区实行独女户有间隔地生育第二胎政策;另外还有针对少数民族和特殊人群(如归国华侨)的生育政策[7]。
2000年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采集了345个地区级的政策生育率数据,有335个地区级数据与2005年个人原始数据匹配[8]。有研究者分析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的关系时,对地区政策生育率简化分类,分为一孩政策(政策生育率在1.3以下)、一孩半政策(政策生育率在1.3~1.6之间)和二孩及以上政策(政策生育率大于1.6)[9]。根据张二力划分的政策类型和各省相应的计划生育条例,同时结合妇女和丈夫的户口性质,判定每个家庭所属的真正政策类型。这样确定了每个家庭应该实行的生育政策类型后,可以根据生育孩子数和孩子性别结构判定其生育行为是否合法:对于一孩地区,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都是违法生育;对于一孩半地区,除了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包括只生了一个孩子和第一孩是女孩生育了第二孩的人,其余均为违反政策生育;对于二孩地区,生育了三个及以上孩子的都是违法生育。
需要说明的是,广东省在1998年10月通过了新的《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农村由二孩政策调整为一孩半政策。对广东省妇女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判定以1998年10月为准,识别第二个孩子的出生时间,如果出生在1998年10月以前则为合法生育,如果出生1998年10月以后,则根据第一孩的性别进行判断,第一孩为男孩则第二孩是违反政策生育,第一孩为女孩则是合法生育。
另外,有些省份实行夫妻均为独生子女或夫妻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由于本研究选取的是35岁及以上的妇女,2005年小普查只调查了30岁以下人口的兄弟姐妹情况,所以无法判断家庭类型。但实际上,2005年35岁及以上的妇女均在1970年以前出生,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非常高,这一时期独生子女非常少。而且,2005年小普查数据显示,2005年30岁的独生子女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3%,比例非常小,35岁以上的独生子女会更少,双独家庭或单独家庭所占比例也将很小。因此,无法判定数据中的双独家庭或单独家庭不会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
4.主要自变量
结合已有研究结果和理论,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设计了违反政策生育行为产生的影响因素框架。根据这个思路框架,从2005年小普查数据中选取合适的自变量(见表1)。
5.研究方法
本文先采用双变量分析法分析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初步确定各影响因素的作用。然后,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单独看某个自变量的影响。由于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判定与政策类型和生育孩子数量及性别结构直接相关,无法在一个模型下考察性别偏好的作用,本文将分政策类型构建模型,分别来看性别偏好的影响。
三、结果与分析
1.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水平与差异
根据2005年1%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在1990年以后生育第一个孩子、夫妻均为初婚、汉族、非流动、35岁及以上的妇女中,违反政策生育比例达到18.95%。这一比例在不同地区、不同生育政策类型和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人群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在宏观上,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往往违反生育政策的比例越小,但是各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地区发展指数与违反政策生育比例之间并非严格的线性关系。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但同时,生育行为还会受到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文化习俗、社会政策等。例如,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但是违反政策生育比例已经达到了38.79%。
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产生限制作用。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全国一刀切的“一孩”政策,而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和家庭的具体情况实行多样化的政策[10],可分为一孩政策、一孩半政策、二孩政策和其他政策,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占全国一半以上[11]。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违反政策生育比例最高,达到了21.69%,其次是二孩政策地区,比例为18.43%(见图1)。一孩政策地区大部分是城市地区,经济发达,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看,我们预期会有较低的违反政策生育比例,但数据计算结果却相反,一孩政策地区仅略低于二孩政策地区,为17.91%。进一步分析一孩政策地区不同户口类型的比例差异发现,城市户口违反政策生育比例确实较低,但农村非常高,达到了36.82%。
为了深入探索不同政策类型地区生育行为出现的差异,我们通过对比不同政策地区的孩次构成情况来进一步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一孩政策地区虽然违反政策生育比例也较高,但是三孩及以上的高胎次生育比例非常低,违反政策主要发生在二孩上。一孩半政策地区违反政策生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第一孩为男孩,但仍然继续生育二孩的人;二是生育了两个以上孩子的人。与二孩政策地区对比,一孩半政策地区三胎及以上的高孩次生育比例小,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在
生育
二胎时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即这些妇女在生育了一个男孩的情况下还继续生育了第二个孩子。
在中观层面,家庭因素与违反政策生育行为有很大关系。家庭收入与违反政策生育的风险之间呈负向关系。收入越高,违反政策生育比例越低。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家庭违反政策生育的比例达到了约23.27%,随着收入的升高,
该比例几乎呈线性下降,月收入达到5000元以上家庭违反政策生育风险大大降低,违反政策生育的家庭仅为7.27%。
居住模式与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关系与预期不一致。与父母一起居住的人有17.86%违反政策生育,而不与父母居住的人有19.06%违反政策生育。要进一步研究婚居模式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分清是从妻居还是从夫居形式,父母和子女一起居住的时间是在生育孩子之前、之中还是之后。但受限于数据,无法进行更详细地分析。
[JP2]微观层面的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有直接的影响。数据显示的初育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与违反政策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与现有研究结论一致,初育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发生的风险。年龄和违反政策生育比例几乎是线性负相关。用线性回归进行拟合,初育年龄可以解释违反政策生育比例差异的95%以上。受教育程度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影响也几乎是线性的。违反政策生育比例在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妇女中为27.12%,从初中开始迅速下降,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该比例仅有3.49%。其他的社会经济特征与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关系也与预期一致。比如,农业户口违反政策生育的比例是非农户口的两倍多,有工作的人遵守政策生育的情况要好于没有工作的人,有社会保险的人更可能遵守政策生育,其中没有养老保险的人违反政策生育比例是有养老保险的人四倍多,没有医疗保险的人违反政策生育比例高于有医疗保险的人约十个百分点。
[JP]
人们违反政策生育,归根结底是对孩子的数量和性别结构的意愿和偏好造成的。在只生两个孩子但却是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妇女中,只有13.9%的人有两个女孩,有60.2%的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25.9%的人有两个男孩。在生了三个孩子的妇女中,“女女男”性别结构的妇女违反政策生育比例最高,达到37.83%。且此可见,男孩偏好较为明显。
2.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
为了考察上述影响因素的独立作用,本部分进行回归分析。模型1在全国层次上构建回归模型,考察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政策、家庭环境、个体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的作用。但由于不同政策会直接导致不同生育行为,包括孩子的数量和性别结构,因此,分政策地区构建模型能更深入地了解各自变量在不同政策地区影响的差异性和共性。模型2和模型3是一孩政策地区的回归结果,因变量分别为“是否生育第二孩”、“生育第二孩的人是否生育第三孩”。模型4、5、6是一孩半政策地区的回归结果,因变量分别为“是否违反政策生育”、“是否生育第二孩”、“生育第二孩的人是否生育第三孩”。模型7、8、9是二孩政策地区的回归结果,因变量与一孩半政策地区相同,详见表3。
(1)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制度。
首先看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政策。虽然生育政策类型与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二者分别代表的是不同的社会环境因素,全国六大行政区的划分大体能反映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制度,生育政策类型则代表了政策环境。除了中南地区外,与西北地区相比,其他地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风险要小。中南地区违反政策的可能性变高主要是因为广东省属于中南地区,广东省由于文化等一些其他独特的因素,其生育行为与其经济发展水平背离较远,违反政策生育比例非常高,所以尽管中南地区在整体发展水平上要好于西北地区,它的违反政策生育风险仍高于西北地区。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东北地区虽不如华东、华北地区发达,但违反政策生育比例非常低(4.27%),不仅生育率低,而且性别选择也没有其他地区严重。目前没有人专门研究过东北地区的这种现象。这可能和东北地区是传统的工业基地,城市化水平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移民较多和计划生育执行力度较强有关。结合前面省级经济发展水平与违反政策生育比例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经济发展水平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并非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违反政策生育比例越低”的线性关系。不能完全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解释中国妇女的生育行为,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观念,如男孩偏好以及政策的执行力度同样会对生育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验证了人口转变在中国的区域不平衡性和复杂性。
(2)计划生育政策类型。
生育政策类型的回归结果显示,一孩半和一孩政策地区比二孩地区更容易发生违反政策的生育行为。其中,一孩半地区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概率比二孩地区提高了1.01倍,一孩地区则比二孩地区提高了3.04倍。这意味着,政策较为宽松的地区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可能性较小,相反,政策较严的地区更容易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虽然随着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展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育意愿发生了较大转变,理想孩子数也大大减少,但是两个孩子似乎是人们的普遍理想。同时,性别偏好,尤其是男孩偏好尚未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而发生根本转变。在生育数量偏好和性别偏好的双重作用下,政策限制越严的地区,人们更容易违背生育政策。[JP]
需要解释的是,以上结论似乎与“城市地区更发达,因此更不容易违反政策生育”的观念矛盾,因为一孩地区大部分是城市地区,按照一般常理应该推论出,与二孩地区相比,一孩地区更不可能违反政策生育,但回归结果恰好相反。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笔者将政策类型与其他自变量进行交互,分析违反政策生育比例,结果发现,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有养老保险改变了回归系数的影响方向,也就是说,在控制受教育程度或养老保险的情况下,一孩政策地区确实比二孩政策地区更容易违反政策生育。如表4所示,在未上学、小学、初中几个受教育层次上,一孩政策地区违反政策生育的比例远高于二孩地区和一孩半地区,不仅农村一孩地区如此,城市一孩地区也较高。不过一孩政策地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违反政策生育比例低于二孩和一孩半地区。而一孩地区未上过学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违反政策生育的较少,初中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较多,其中,高中及以上者占了45%左右,初中者43%左右。二孩和一孩半政策地区在文化程度的分布上刚好呈相反方向,即
违反政策生育者中高中及以上的人非常少,初中及以下的人占绝大部分。同样,在没有养老保险的人中,一孩地区比二孩和一孩半地区更有可能违反政策生育(见表5)。而二孩地区和一孩半地区
违反政策生育者中有养老保险的人非常少,均低于5%,一孩地区则接近一半。所以结论是,发达地区其实在通过改进其他因素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比如,发达地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多,有养老保险的人更多,教育和社会保障都会显著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
(3)家庭因素。
与描述统计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模型结果显示,并非是家庭月收入越高,违反政策生育风险越小。月收入5000元以内的家庭收入提高对违反政策生育风险有显著的降低作用,但5000元以上的家庭与500元以下的家庭相比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如果将违反政策生育风险用曲线表示,那么在其他因素一样的条件下,收入与违反政策生育风险之间的关系是正“U”型曲线,即
收入的两端——低收入和高收入违反政策生育的风险较大。根据微观生育经济学理论,低收入贫困家庭孩子生育养育成本低,而父母从孩子身上获得的收益大,如提供劳动力、提供养老保障、壮大家族势力等,孩子的价值大于成本。同时,贫困家庭受传统生育观念——如“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影响更深,因而容易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而随着收入的升高,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均上升,家庭把孩子当作收入来源的要求变小,同时更高的收入意味着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孩子的训练、教育和发展上,孩子作为劳动力的时间就少,而且收入越高,孩子作为父母老年保障的效用减小,这就是莱宾斯坦在孩子成本效用理论中提出的“收入效应”[12]。但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升高,人们对孩子的数量偏好又逐渐显现,两个孩子是人们普遍追求的理想孩子数,而高收入家庭有能力承担违反政策带来的经济惩罚以及其他成本,为了实现数量偏好或性别结构偏好,也容易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行为。需要解释的是,在一孩半政策地区,收入的影响表现为“收入越高,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可能性越低”,这与我们的结论实际并不矛盾,主要是因为在一孩半政策地区,有很高家庭月收入的家庭非常少,2000元以上收入的家庭不到10%。这也说明收入有“门槛效应”,收入只有达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对违反政策生育风险有正向作用。二孩政策地区收入影响基本不显著,主要是因为二孩地区基本上是落后的农村地区,受传统观念影响更大,而且2000元以上收入的家庭比较少(不到5%),人们违反政策生育主要是由性别偏好引起,而受收入的影响较小。
回归结果显示,是否与父母同住在全国层面对一孩半、二孩政策地区影响不显著,但在一孩半、二孩地区无论是对违反政策生育发生风险还是对生育下一孩次发生风险的影响方向都是正的,而在一孩政策地区,与父母同住会显著地降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风险。一孩半和二孩政策地区都是农村地区,父母的传统生育观念更容易影响子女的生育选择,而在一孩政策地区,与父母居住会降低违反政策生育的风险,受数据限制,无法进行深入的分析,具体原因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4)个体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
个体是生育决策的主体和生育行为的实践者,个体的一些特征将直接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从人口学特征来看,妇女的初育年龄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发生风险具有明显的降低作用,妇女的初育年龄每增大一岁,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风险就降低5%(模型1)。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妇女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妇女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可能性不断降低。回归结果充分体现和验证了已有研究结论,初育年龄的推迟直接影响生育期的长短,也间接地体现了生育观念的变化和竞争性因素的影响(如上学、就业)。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也会通过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推迟生育年龄而影响生育行为。
户口性质、工作状况和是否有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反映了妇女的社会经济特征。户口性质主要体现了城乡之别,城市和农村在发展程度、生育文化、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的差异都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反映在违反政策生育行为上,主要表现为农村妇女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可能性大于城市妇女。
是否有工作在全国层面没有显著性作用,在一孩半和二孩政策地区模型结果显示,没有工作的人更易于违反生育政策。而在一孩政策地区,没有工作的人违反政策生育的可能性比有工作的人小,与前面对政策类型的解释一样,回归系数出现方向性的改变与加入养老保险、收入等几个控制变量有关。但在生育三孩的风险上有无工作没有显著的差异。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会显著影响违反政策的生育行为,没有养老保险的妇女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概率是有养老保险的妇女的3.94倍,而医疗保险的缺失将违反政策生育概率提高了11%(模型1)。这既说明社会保障对生育行为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养老保险的作用大于医疗保险,由此可见,“养儿防老”的观念仍在人们的生育行为中有所体现。
控制变量的模型结果显示,第一个孩子年龄越大,妇女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风险也越大,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迟,妇女的生育行为也在发生变化,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在增加。
(5)性别偏好。
分政策类别看性别偏好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所有模型均能体现性别偏好的强烈影响。
一孩政策地区,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风险大小取决于第一个孩子的性别,第一孩是男孩的妇女与第一孩是女孩的妇女相比,前者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概率降低了63%。再看前两孩的性别结构对生育第三孩风险的影响,与前两孩都是女孩的妇女相比,有两个男孩或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的妇女更不容易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发生风险均降低了80%以上。
在一孩半政策地区,与只有男孩的妇女相比,只有女孩的妇女更不可能违反政策生育,这是由政策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判定违反政策生育是根据第一孩性别而定,第一孩如果是男孩生育第二孩就是违反政策生育。儿女双全的家庭违反政策生育概率是只有男孩家庭的2.28倍。与一孩政策地区表现的规律一样,一孩半地区第一孩的性别会影响第二孩生育风险,第一孩是男孩的妇女生育第二孩的风险大大降低,这一方面是由于政策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性别的偏好。性别结构偏好在第三孩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相比较于前两孩是女孩的妇女,生育了两个男孩或一男一女的妇女生育第三孩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其中儿女双全的人比只有男孩的人下降风险更大,说明人们有在男孩偏好基础上追求儿女双全的倾向。
在二孩政策地区,与一孩半政策地区不同的是,只有女孩的家庭更容易发生违反政策的生育行为,反映了人们有通过多生来实现性别偏好目的(即生育一个儿子)的倾向。儿女双全家庭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概率是只有男孩的家庭的12.11倍,体现了人们的性别双全偏好。同样,与其他两类地区类似,第一孩是男孩的妇女生育第二孩的可能性降低,前两孩是两个男孩或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的妇女继续生育第三孩的风险大大降低,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偏好。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微观层面上探讨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程度和影响因素。根据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1990年以后生育第一个孩子、汉族、初婚、35岁及以上未流动的妇女违反政策生育的比例是18.95%。而不同人群和不同政策地区又存在较大差异。回归分析显示,与二孩政策地区相比,一孩政策地区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风险最高,其次是一孩半地区,这意味着政策越宽松的地区人们越倾向于在政策规定范围内生育。
政策类型、受教育程度、养老保障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发生风险影响非常大。养老保障比医疗保障的影响作用更大。在分政策类型考察性别偏好的作用时,模型结果显示,无论是在一孩政策地区,还是一孩半政策地区或是二孩政策地区,性别结构的影响系数均非常大,因此可以推断,性别偏好始终是导致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行为发生的主要因素。
受数据限制,本研究无法考虑漏报因素。漏报尤其是低年龄漏报是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13~14]。比如,翟振武、陶涛利用教育数据对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检验,得出在考虑死亡的情况下2000年普查数据0~3岁组每个年龄组漏报了近340万人[15]。由于本研究未考虑到漏报,可能会低估违反政策生育比例,但是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可以判断,虽然数据存在漏报情况,但本身不会对结果和结论产生影响。对目前普查数据评估的一个一致的结论是低龄组中女婴漏报多于男婴[16~17]。出生漏报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这些地区很多农民想生男孩,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男孩[18]。这与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一致的。本研究的政策含义中,除了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制度建设可以减弱和消除违法生育的基础外,二孩地区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较低发生风险启示我们,政策类型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选择,适时、适当地完善生育政策是必要的。“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满足部分群众的生育愿望,使计划生育政策得以更好的实施,有利于调控我国人口变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 茅倬彦.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差异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9,(2).
[2] 梁中堂,阎海琴.中国农村多胎生育状况及对策[J].中国人口科学,1991,(2).
[3] 朱红权.鄂西北农村近年二胎违反政策生育热现象的调查和思考——基于湖北省枣阳市几个村庄的实地研究[J].人口与发展,2008,(6).
[4] 马妍,刘爽.中国省级人口转变的时空演变进程——基于聚类分析的实证研究[J].人口学刊,2011,(1).
[5] Bongaarts, J. 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Preferences in Posttransitional Societies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1, (27).
[6] 王谦.应用队列累计生育率分析我国生育水平变动趋势——兼与郭志刚教授讨论[J].人口研究,2008,(11).
[7] 杨菊华,宋月萍,瞿振武,陈卫.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8] 同[7].
[9] 张二力.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5,(1).
[10] 同[7].
[11] 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政策的多样性[J].人口研究,2003,(5).
[12] 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13] 翟振武,陶涛.低年龄人口数据质量的分析与评价[J].中国人口科学,2010,(1).
[14] 于学军.对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总量和结构的估计[J].人口研究,2002,(3).
[15] 同[13].
[16] 翟振武,杨凡.中国出生性别比水平与数据质量研究[J].人口学刊,2009,(4).
[17] 张广宇,原新.对1990 年代出生漏报和生育水平估计问题的思考[J].人口研究,2004,(2).
[18] 同[17].
参考文献:
[1] 茅倬彦.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差异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9,(2).
[2] 梁中堂,阎海琴.中国农村多胎生育状况及对策[J].中国人口科学,1991,(2).
[3] 朱红权.鄂西北农村近年二胎违反政策生育热现象的调查和思考——基于湖北省枣阳市几个村庄的实地研究[J].人口与发展,2008,(6).
[4] 马妍,刘爽.中国省级人口转变的时空演变进程——基于聚类分析的实证研究[J].人口学刊,2011,(1).
[5] Bongaarts, J. 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Preferences in Posttransitional Societies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1, (27).
[6] 王谦.应用队列累计生育率分析我国生育水平变动趋势——兼与郭志刚教授讨论[J].人口研究,2008,(11).
[7] 杨菊华,宋月萍,瞿振武,陈卫.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8] 同[7].
[9] 张二力.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5,(1).
[10] 同[7].
[11] 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政策的多样性[J].人口研究,2003,(5).
[12] 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13] 翟振武,陶涛.低年龄人口数据质量的分析与评价[J].中国人口科学,2010,(1).
[14] 于学军.对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总量和结构的估计[J].人口研究,2002,(3).
[15] 同[13].
[16] 翟振武,杨凡.中国出生性别比水平与数据质量研究[J].人口学刊,2009,(4).
[17] 张广宇,原新.对1990 年代出生漏报和生育水平估计问题的思考[J].人口研究,2004,(2).
[18] 同[17].
参考文献:
[1] 茅倬彦.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差异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9,(2).
[2] 梁中堂,阎海琴.中国农村多胎生育状况及对策[J].中国人口科学,1991,(2).
[3] 朱红权.鄂西北农村近年二胎违反政策生育热现象的调查和思考——基于湖北省枣阳市几个村庄的实地研究[J].人口与发展,2008,(6).
[4] 马妍,刘爽.中国省级人口转变的时空演变进程——基于聚类分析的实证研究[J].人口学刊,2011,(1).
[5] Bongaarts, J. 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Preferences in Posttransitional Societies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1, (27).
[6] 王谦.应用队列累计生育率分析我国生育水平变动趋势——兼与郭志刚教授讨论[J].人口研究,2008,(11).
[7] 杨菊华,宋月萍,瞿振武,陈卫.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8] 同[7].
[9] 张二力.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5,(1).
[10] 同[7].
[11] 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政策的多样性[J].人口研究,2003,(5).
[12] 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13] 翟振武,陶涛.低年龄人口数据质量的分析与评价[J].中国人口科学,2010,(1).
[14] 于学军.对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总量和结构的估计[J].人口研究,2002,(3).
[15] 同[13].
[16] 翟振武,杨凡.中国出生性别比水平与数据质量研究[J].人口学刊,2009,(4).
[17] 张广宇,原新.对1990 年代出生漏报和生育水平估计问题的思考[J].人口研究,2004,(2).
[18] 同[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