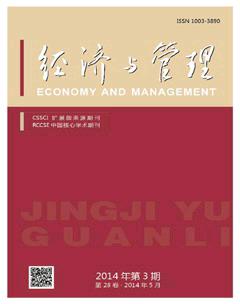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决策的个案访谈分析
摘要:文章通过实地访谈,深入分析了家庭迁居的决策过程、家庭不同迁居行为的依据,以及家庭成员在决策过程中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家庭的迁居决策是在整体资源配置下实现的,迁居的地点一般由家庭在流入地的经济因素、发展因素与社会资本因素共同决定,不同批次迁移的家庭成员进行迁居的时间间隔多以经济条件为标准。最终,受到家庭生命周期以及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家庭会做出在城市定居或者返乡的迁居决定。最后,本文将家庭迁居决策过程总结为“五阶段”,即商议期、配置期、决策期、跟随迁居期、迁居结果期。
关键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家庭决策;迁居行为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4-0065-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07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making in China:Based on the Deep Interview
SHENG Yinan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dentify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family migration, analysis the basis of different migration behaviors, and explore the interactions of family members during decisionmaking according to the indepth interview.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realized by allocation the human resources in the family. The immigrant area is influenced b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apital factors of the family. Time lags between the foregoers and the other family members are determined by economic situation. The stage of the familys lifecycle and the 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will affect the familys migration decision.It is concluded as five phases of family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cluding negotiation, allocation, decisionmaking, following migration and decision results phase.
Keywords:floating population, family migration, family decisionmaking, migration behavior
我国举家外出农民工的规模正在逐年递增,2012年已经达到3375万人[1]。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的规模不断增加,开始引发研究者的讨论与关注。对我国乡-城人口流迁过程中家庭化迁居的研究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家庭化迁居的研究框架超越了个人的范畴,以家庭这一基本的人类组织和社会单位作为研究对象。以往对流动者个人流动或迁移的研究多侧重于个体的行为和特征;但是家庭化迁居的研究基础更为复杂,家庭的成员关系、家庭结构、家庭禀赋等层面都可能对家庭的迁居决策产生影响。本文的目的是研究乡-城人口流迁过程中的家庭迁居决策行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拓展以家庭为主体的最优化决策的研究,也可以对人口迁移理论进行拓展与延伸。
已有对家庭迁移决策的研究多从静态视角,探讨在人口流动行为发生之前家庭成员间的协商机制。从决策主体而言,家庭的主要决策者一般是父母或者男性户主[2~3],丈夫与妻子会衡量整个家庭在迁移后的经济收益和损失,当丈夫在迁移后收入的提高能够弥补家庭的损失时就会决定家庭迁移[4~5]。王春超等认为中国农村家庭户的经济决策模式是“男女共商”型[6]。谭深认为单一的家庭经济目标并不能解释家庭迁移的决策与动机的复杂性,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和成员间的互动在家庭策略的形成过程中更为重要[7]。孙朝阳对家庭策略下劳动力迁移的性别选择进行分析,认为家庭对成员流动的决策是按照性别劳动分工而进行的安排[8]。除了对家庭迁移决策中成员协商机制的研究,还有学者建立起家庭迁移决策模型来分析家庭迁移的决策行为。蔡昉较早地建立了家庭迁移决策经济学模型,对农户的迁移决策进行实证研究[9]。马瑞等建立了农村劳动力职业流动和家属随迁的决策模型,其基本假设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决策是依据一定风险水平下对预期收益与成本的比较[10]。
总的来看,现有研究多为静态研究,集中于对流迁行为的某一个特定时段的决策研究,例如先行人向外流动的决策,或者配偶、子女跟随流动的决策,缺乏对家庭迁居行为全过程的动态研究。此外,现有研究多将家庭的特征作为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之一,而不是作为流动或迁移决策的主体。本文将在家庭迁居理性程度假设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理性程度下的家庭决策行为和家庭作为迁移主体在迁居决策链条中的作用机制,利用实地访谈资料对家庭迁居全过程中的决策行为进行分析,包括家庭协商模式、先行者的选择、迁居方式、家庭迁居地点、迁居时滞的权衡和对最终迁居结果的抉择等,力求对现有研究进一步拓展。
一、 家庭迁居的理性程度假设
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基础。随着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拓展,理性人假设开始受到置疑,尤其是来自新制度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对有限理性的研究。有限理性指出,现实世界中充满了不确定因素,使个人无法获得完全信息,而人的计算和认识能力又是有限的,不能无所不知。然而,理性与非理性并非绝对对立的两个方面。西蒙整合了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对理性研究的极端倾向,将理性的程度划分为直觉理性、行为理性与完全理性;在心理学领域,哈耶克也将经济人决策的理性程度划分为理性不及、理性无知、理性非理性等。行为经济学派也不反对对理性程度进行分类[11]。我国学者何大安将行为人的理性状态划分为高、中、低三种程度,并将时间作为理性实现程度的重要因素[12]。本文建立家庭迁居的理性程度假设,将家庭作为迁居决策的行为主体,并将迁居决策的理性程度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一是理想理性程度,即无限接近完全理性的理性程度。在完全理性阶段,家庭能够最大化地发挥认知能力,充分地搜集信息,环境中的不确定信息几乎为零,这与现实世界的情况有所差别。家庭可以精确地计算迁移系统为家庭带来的收益和成本。
二是实际理性程度。家庭受到现实环境中不确定信息和因素的干扰,在一定时期内尽量地搜集可能获得的信息,尽可能地发挥可能达到的认知能力,按照满意原则做出迁居决策。家庭在迁居过程中除了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可能受到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制度与文化因素、家庭的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状况,以及家庭的人力资本和个体发展等因素。这种理性程度是最贴近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的。
三是直觉理性程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家庭难以对外界环境进行有效的判断,很容易受到干扰,使认知和判断产生偏差。在人口流动的初期,由于农村人口获得迁移信息的途径比较闭塞,一般依靠农村社区中其他流动人口的示范效应实现。家庭迁居决策多属于直觉理性,使人口流动表现出极大的盲目性和赶潮流式的集中性。随着人口流动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对人口流动的有序管理降低了流动的盲目性和无序性,而农村家庭对流动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减少了家庭决策的直觉理性程度。
本文将家庭作为决策主体,在家庭实际理性程度假设的基础上,分析家庭化迁居的决策过程和行为方式。这里,家庭迁居的决策机制是指农村家庭户作为主体,对人口流动与迁居过程中所需的信息进行搜集、分析和判断,对内部资源进行配置,并随家庭的发展或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决策的机制。
本文按照家庭化迁居的过程,将家庭迁居决策划分为迁居起始决策、迁居过程决策和迁居结果决策(见图1)。在第一阶段,即家庭化迁居的起始期,家庭会做出个人或部分人外出流动的决定,其前提是个人的流动行为对家庭整体利益有所提升,或者至少不会降低整个家庭的福利。那么,家庭对福利上升的判断将成为迁居决策的主要动因。在家庭化迁居的过程阶段,家庭可能对先行者、迁居地点等进行选择,并通过阶段性流动的方式逐步将其他成员带到城市中,也有可能举家迁居到城市中。从第三阶段,最终的迁居结果来看,家庭可能选择长期居住,甚至在城市中定居成为城市家庭,但也可能最终决定返回原居住地。
在家庭的实际理性程度下,家庭会在衡量迁移的成本和收益之外,综合考虑影响家庭迁居的各种因素,其中可能包含传统文化因素、社会学因素、制度背景因素等。为了准确地展现家庭迁居的决策过程和作用机制,笔者的研究方法以深度访谈为主,结合了部分调查数据进行说明。本文在河北省保定市展开了深度访谈,并应用了中国人民大学2012年“北京市非正规就业人口调查”的部分访谈资料,调查对象均为在城市中居住三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研究数据应用了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监测数据2010年下B卷,调查地区为北京、郑州、成都、苏州、中山、韩城6个城市,总样本量为8200人。
二、 家庭迁居起始阶段的决策
1. “协商共议”是家庭化迁居的主要决策模式
康奈尔(Connell)等认为家庭迁移决策有两种决策方式,即户主做出迁移决策,家庭中的迁移者接受户主的决定;或者所有家庭成员达成共识[13]。中国传统家庭权力的中心以父权制为主要制度形式,父系、父权、从夫居制构成了父权制家庭的规则体系。迁移方式以一家之主的意见为绝对地位,其他家庭成员自上而下共同行动,执行迁移行为。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家庭迁移一般以康柰尔研究中的前者为主要决策形式。
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家庭现代化进程表现为传统家庭转为核心家庭,个人的价值高于家庭,更加倾向于性别平等,压制传统和习俗等[14]。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家庭的权力中心发生转变,父权在家庭中的绝对地位受到削弱[15]。家庭商议模式由“唯父命是从”向“协商共议”的决策方式转变:一方面,女性通过流动行为提高了经济收入,在家庭的经济活动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妻子与丈夫“议价”的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人口的流迁行为促进了家庭现代化变迁,带来了性别间的重新协商。绝大多数的被访者表示,家庭在面临流动等对家庭会产生重大影响作用的事件时比较民主,家庭成员之间会互相商议。如果流动者坚持向外流动,其他家庭成员不会特别反对。即使其他家人最初有反对意见,但是通过相互商议、妥协,能够最终达成共识。家庭一般会重新配置家庭内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有序分工,以确保外出务工的家庭成员没有后顾之忧。例如:
C03(女,28岁):我老公先决定要出来打工(家庭迁居的先行者),当时我们家里面都是反对的。因为家里面工作都挺稳定的,收入也还可以。但是他说想出来闯一闯、看一看,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在这边打工。现在家里都支持我们出来打工。(问:为什么现在他们支持了?)因为在外面收入还可以,家里面公公婆婆现在还年轻,他们也还照顾的过来。家里的土地都被承包了,每年收一些租金(家庭进行协商,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
2. 对家庭的整体收益与个人的追求进行权衡
家庭做出迁居决策的最重要的动因是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家庭在衡量流动的收益与成本时会考虑不同的因素,使迁居行为可能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
一是追求经济收入或预期经济收入的满意,例如C02(男,25岁):“老家的收入太低了,每个人分得的土地只有几分,根本不够生活。我们那基本都靠出来打工赚钱。”
二是追求成本与收益的满意,如C01(男,43岁):“我已经在外面打了二十多年工了,现在在N大食堂里面工作。这边的收入虽说不算高,但也还可以,总是比在老家的收入要高,不好也不会过来。跟这边相比,我们老家的消费水平更高。在这边工作容易攒钱。”
三是追求门槛的最低化(最满意),如C03(女,28岁):“我们两个人在老家的收入也不错……但是老家的消费和收入都比在这边高,在家主要是花的比较多,朋友也比较多,用(钱)的(方面)比较多。我们两个人在这边,相比之下更容易攒钱。”
年轻的流动人口更加注重个人发展因素。不少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在决定向外流动时,会听取家人的意见,但更加顾及个人的追求。他们认为,年轻时期外出闯荡、打拼,了解家乡外面的世界十分重要。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他们重视自身的未来发展,有意愿融入城镇成为市民。同时,对土地的依赖性较低,很多人从未从事过务农,也不想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例如:
C08(女,26岁):我以前在N大上学,学的是物流专业。毕业之后,经过朋友介绍在这里工作。我以前在家就不干农活,所以也不想回家种地。
3. 对闲暇与收入进行比较,达到家庭整体效用最大化
在家庭生产理论中,家庭将时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时间用于在市场中工作获得经济收入,另一部分时间用于闲暇,即个人用于在市场工作和家庭工作之外的时间。家庭将有限的时间在闲暇与收入之间进行分配,使两者之间呈现替代效应。类似地,农村家庭会对迁居后的闲暇与收入进行比较,进而影响到迁居决策。在家庭整体收入尚未达到某一水平时,家庭成员会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而选择外出(或不外出)流动,放弃闲暇。如C01(男,43岁):“像我们在老家里干活时,都没什么事可做,比较轻松。在这边工作,每天要起早贪黑的,还是比较累。”
反之,当经济收入达到某一水平后,收入对家庭整体效用的提高作用开始递减,相反,闲暇的增加能够使家庭的效用得到显著地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流动人口会更倾向于选择闲暇,而非经济收入。如C10(男,32岁):“在老家的收入更高。如果包二十亩地,一亩地就能挣千八百的,就是太累。在这(城里),一个月才能挣一千多块钱,买房也买不起。但是在城里打工轻松多了,在老家种地比较累。所以我现在还是会留下来打工。”
三、 家庭化迁居过程中的决策
1. 家庭资源配置下的先行者流动
先行者一般是家庭中的壮年劳动力。他们是获得经济收入的中坚力量,肩负着通过外出流动来增加家庭整体福利的责任。一旦先行者决定外出流动,整个家庭就会进行资源的分配与整合,例如,长辈帮助照看孩子,兄弟姐妹帮助代为耕种土地、看管房产等。这些安排可以保证家庭生活在成员流出后不会受到影响,使家庭平稳度过成员的外出流动阶段。
C06(女,34岁):家里最先是我丈夫决定出来打工,正好有朋友在N大食堂工作,他介绍我们过来工作。后来我和我老公同时出来打工,现在在城里做餐饮。我们现在还年轻,想出来见识见识,这边的收入更高。现在家中还有孩子和公公婆婆……公婆照顾孩子,家里的房子、土地让弟弟照看,种地的收入也归他。
2. 迁居地点:经济因素、发展因素与社会资本因素
调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对迁居地点进行选择时,首先考虑经济因素:如工作机会、经济收入,分别列选择流入地原因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其次是发展因素:学习技能、增加眼界、孩子的教育,分列原因的第三、第五和第七位。最后是社会资本因素:亲朋好友、家人在流入地等,也会吸引流动人口后续流动(见表1)。这说明,经济因素和发展因素是家庭在实际理性程度的过程中首要考虑的因素。
社会资本对家庭选择迁居地点的影响较为复杂。费孝通曾提到,乡村人际关系的亲属关系会形成差序结构,最内层是直系血缘关系,其次是旁系血缘关系,最外层是地缘关系[16]。流动人口对迁移地点的选择也呈现差序结构的现象。从其就业联系的网络来看,有直系亲属的地方是迁居地点的首选,其次是有旁系亲属的地点,最后是熟人和老乡的聚集地。从社会网络的支持来看,亲友、老乡能够为流动人口提供工作机会、住房,以地缘为特征的老乡间的帮助则更为常见。流动人口自身也依据差序结构将其他亲友带到现居住地。如C17(男,30岁):“我最早跟着老婆的表哥来北京做打印,帮他打工。老板包吃包住,老婆有时来北京的打印店里帮忙,有时在家看孩子、种田。”
乡土秩序在城市环境下不断延续,但也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发生了嬗变。一些流动人口不再将老乡作为雇佣员工的首选。流动人口碍于乡土之情,对老乡的雇佣成本会增加,如果老乡工作不够积极、努力,也不方便直言。因此,流动人口在社会交往领域更多的是接近自己的老乡,但是在劳动关系领域,他们却不愿意选择老乡。
C14(男,23岁):我来北京是因为亲戚(舅舅)在北京开装修公司,而且可以提供住的地方,自己就跟着过来了……在R大学校卖凉菜。我还叫了表弟来帮忙卖。表弟是亲戚,刚开始做比较方便,成本低。店开大以后不想雇老乡,主要看能力和头脑。我个人比较注重人际关系,老乡做得不好反而不太好相处。
C15(男,21岁):老乡都是干这个的(卖废品),亲戚也在这,他们都做得不错。过来(打工)可以有住宿,认识的人互相帮忙,成本就比较低,投资大就赚得多。现在觉得请外地人干活比找老乡要好,可以给工资低一些。
3. 迁居时间间隔:以经济条件为标准
迁居时间间隔是考察家庭化迁居倾向的重要指标[17]。如果后续到来的家庭成员的时间间隔较短,说明家庭“举家迁居”的趋势更为明显。访谈资料表明,对于有意愿将其他家庭成员带到城市的流动人口,迁居的间隔一般不是具体的年限,而是抽象的经济条件。如C08(女,25岁)表示:“我打算等自己结婚成家,收入比较稳定可以养家,而且弟弟结婚可以独立生活以后,就把父母接出来,(让他们)享受比较好的生活。”根据移民网络理论,流动人口在带动其他亲友流动的过程中,可能需要提供诸如住房、工作机会等帮助,这要求先行人有足够的能力在城市中立足。而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实现。已有研究显示,各批次家庭成员流动到城市的平均时间间隔大约在3~4年[18]。这说明,分批次的家庭成员向城市的迁居并不是某个仓促的决定,而是一个审慎的过程,其判断的主要标准一般是经济条件。
四、 家庭迁居结果的决策
1. 依据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判断迁居决策
家庭迁居决策会受到家庭成员关系和生命周期阶段的影响,但家庭关系的利益序列却有很大差别,抚养和赡养的地位并不平等。传统代际关系中的“反哺模式”尽管在延续,但是受到了弱化。
从家庭劳动力配置的角度来说,当流出地家庭中有其他兄弟姐妹的帮助时,对上一代人养老的压力就得到了分解。如C01(男,43岁)表示:“我有个弟弟在家里面。弟弟和弟妹都在县城上班,他们每到节假日都会回家照顾父母,所以我在外面也不担心老人养老的问题。”从时间角度来看,对父母的赡养在短时间内不是流动家庭考虑的重点。如果父母无人照顾,那么直到父母年事已高时才将他们接到城里,或者考虑返乡照顾父母。C10(男,32岁)说:“等父母老了,自己不能照顾自己,生活无法自理的时候,就接来住到一起。”显然,传统家庭制度中的辈分等级关系也受到人口流动的冲击,日渐式微。
相对而言,孩子居于家庭关系利益序列中的首位,许多家庭的迁移决策以孩子的教育和发展为中心。例如,C19(女,26岁)表示:“现在主要考虑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等以后有了孩子,孩子的教育应该由父母自己来,不能长期和爷爷奶奶一辈的人在一起,隔代人对孩子教育不好。孩子将来大了之后没办法在北京参加高考,必须回老家(重庆)读中学,那时候我可能会回家陪孩子。”有些家庭举家迁居,就是为了让孩子接受城市中更好的教育。例如,C09(女,39岁)说:“我是和老公同时出来打工的。出来打工就是为了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城里的教学条件比老家好。现在家就在孩子学校周围不太远的地方。”
当流出地家庭中没有孩子,并且父代人还有能力获得经济收入时,流动人口向农村家庭的汇款相对较少,其经济收入一般用于在城市的生活。与传统的代际财富流动相比,流动人口的子代向父代的代际财富流有所减少。特别是刚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经济基础尚不牢固,所得收入大都留在本地消费,不会向流出地汇款。例如,C04(男,26岁):“现在刚就业,不会往家里汇钱,家里也知道我的情况。家里的收入还可以,不会向我要钱。我现在的工资基本上足够自己在城里生活的花销。”而中年人的经济收入一般以孩子为中心进行积累,在父母不提出需求时一般不会汇款,以便能尽快地在城市中积累财富。例如,C10(男,32岁)说:“父母有地,还有一些退休金,现在能自己照顾自己,所以没给他们寄钱,在这边赚的钱先顾着孩子,是给孩子留下的。”
2. 根据相对剥夺感差异调整迁居决策
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认为,相对剥夺感是影响家庭迁居的重要因素[19~20]。本次访谈发现,家庭感受的相对剥夺感与参照群体有关。家庭将农村中其他家庭作为参照群体时,当感受到与其他家庭的差距时就会做出流动决策。但是,相对剥夺感的参照对象会在流动之后发生改变。流动家庭融入城市生活之后,他们会将参照群体改变为城市家庭。并且,流动家庭的相对剥夺感不仅来源于城镇人口,同样来自于相同身份的农民工中的成功者,如“老板”这一群体。
流动家庭在大城市与参照群体相比,在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等方面会感受到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因此,大城市中的许多流动家庭会放弃在城市流动,选择返乡。如C17(男,30岁)表示:“在北京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里没有根,而且生活成本太高,孩子上学就是烧钱,老板的孩子上个幼儿园就得交十几万,老板交得起我们交不起,大孩子曾经也在北京上过两个月幼儿园,太贵了就没继续上,还是回老家上比较便宜。房价也贵得很,工作个十年也只够交首付。以后肯定会回家。”
中小城市的流动家庭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相对较弱。例如,C01(男,43岁)认为:“这几年的收入感觉还可以。打工以后,感觉我们家与一般的城市家庭相比也不差什么。”C06(女,34岁)也认为:“在这里挣得多,消费也不算太高。我们家现在已经有车有房了(没有户口),感觉跟城里人经济状况比也差不多。”当流动人口有在中小城市长期定居的意愿时,会考虑购买住房等,就会将城市人口作为参照对象,相对剥夺感也会相对增强。尽管能够感受到这种差距的现实存在,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会因此而选择返乡,仍然愿意在城市中继续工作。换言之,在流动家庭的预期中,他们认为在城市中通过一段时期的努力,是能够达到城市人的经济收入或生活水平的。例如:
C10(男,32岁):现在感觉城里的孩子家境是不错的,住房不是问题,最起码爷爷辈儿有房子,父母亲有房子,他自己就会少奋斗好几年,家里也能给安排工作,生活基本保障是没问题的。但是从农村进城的人首先就需要为自己奋斗一套房子,每月工资三千左右买套房子是很困难的。现在能维持生活还是在这里上班吧,找一份这样有养老保险的工作也不容易,慢慢攒钱买房。
C12(男,34岁):目前我家在城市里的问题很多,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买房买不起。挣钱的速度没有房价上涨的速度快。我现在就是五十多平米的房子,我想换成一百多平米的房子,但每年赚的钱只够消费的,没太多积蓄。这一点不如城里家庭。打算按揭慢慢还房款吧。
3. 迁居的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城市的就业、教育等对流动人口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他们对未来的目标还不明确。有些举家迁居的家庭,他们在城市中拥有相对稳定的生活,但可能因户籍、生活成本等原因,对长期定居持有疑虑。家庭在流出地的宅基、耕地、社会关系,使流动人口怀有故土感情,想“有空就回去看看”(C08,女,26岁),甚至“我们两个人(丈夫和妻子)都想回家养老”(C10,男,32岁)。几乎所有参与访谈的流动人口都表示不会放弃在家乡的宅基和耕地。宅基、耕地不仅具有“风险规避”的意义,也是流动人口心理上的寄托。
C09(女,39岁):现在在当地(城市)已经买了房,也有了车,生活过得还可以。但就是没有户口。目前父母和孩子现在都在身边,在老家的房产、土地现在都让弟弟照看,收入也归他。以后在城里更稳定一点,可能会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不过等我和老公年龄大一些之后,我们还可能回老家盖房,在老家养老。
C12(男,34岁):孩子在这上中学,生意在这里发展,经济收入都已经投入在这里,不能轻易就放弃这边的生活。眼下自己还年轻,还想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短期内都会在这里生活,现在不会考虑回家。但是,如果老人身体不好了,肯定会回家照顾老人。家里的老宅子也还得留着,以后我们老了也许还要回去呢。
流动家庭对未来养老地点的期望也体现了迁移结果的不确定性(见表2)。对未来养老地点需要“看经济条件再定”和“没想过”的比例共计43.12%。这表明,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对未来在城市中长期生活还持观望态度。除此之外,选择返回户籍所在地农村的居首位,占31.84%,显示了家庭回迁决策在生命周期中的阶段性。而回到户籍所在地城镇的约占10.21%。相对大中城市而言,小城镇的消费水平更低,也便于流动家庭与农村家庭密切联系。在户籍所在地的小城镇养老,成为流动人口的另一种选择。“以后是不是要长期留在北京,还要看情况再做打算。等孩子上小学了就回老家去做个小生意。我们濮阳的房价今年六千一平米,这还是当地最贵的,所以回老家去,日子过得比在北京强多了。”(C17,男,30岁)
五、 小结
本研究将家庭迁居决策总结为五阶段的决策链条。五阶段是指家庭迁居决策的商议期、配置期、决策期、跟随迁居期、迁居结果期全过程。
家庭的决策起始于家庭的内部商议,因此,第一阶段是商议期。在商议期中,家庭成员通过商议决定家庭是否迁居,以及确定外出流动的人数、地点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家庭更多地体现出协商共议的协商模式。传统的家庭制度与家庭成员关系模式受到人口流动的冲击,降低了父权的绝对控制地位,未婚的女性也同样拥有议价的权力。家庭迁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或花费相对较少的成本(中小城镇),来获得家庭整体收入——成本的最满意。
当家庭做出向外迁居的决策后,家庭会对内部的劳动力资源重新整合和配置,即为配置期。在先行者外出后,整个家庭会成为一个相互配合、协调运作的整体,通过对家庭成员进行重新分工,保证在外流动的人口能够顺利生活、工作,以维持整个家庭的稳定。
决策期是指家庭通过衡量闲暇与收入效用、流动的预期收入和成本、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等因素,对迁居人数进行选择;按照人口流动的乡村人际关系的差序结构,即按照直系血缘关系、旁系血缘关系以及地缘关系由近至远的顺序,选择迁居地点。
在跟随迁居期,家庭会对留守的家庭成员是否迁居,以及留守家庭成员与首批迁居人口的时间间隔进行决策。经济标准是判断迁居间隔的最主要因素。一般而言,当首批迁居的人满足一定的经济条件后,才会将其他家庭成员带到城市中。
迁居结果期,流动家庭会对定居或回流进行决策。流动人口对返乡或定居的选择与家庭生命周期密切相关,同时也体现着传统代际关系的转变。孩子的教育问题将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回流的主要因素,高额的教育成本会促使流动家庭返乡。对老年人的赡养会通过家庭内部资源的重新分配来解决,当老年人需要照料时,流动人口可能会选择回流,或者将老人接到城市中共同生活。从当前我国家庭化迁居的情况来看,户籍制度的制约以及大城市中高昂的生活成本成为流动家庭定居的最大困难,流出地的家庭禀赋是流动家庭的最后一道保障,也是他们的心理寄托。这使得迁移的最终结果体现出“走一步、看一步”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2012年农民工监测报告[EB/OL].[2013-05-27]http://www.gov.cn/gzdt/2013-05/27/content_2411923.htm.
[2] 张文新.近十年来美国人口迁移研究[J].人口研究,2002,(7).
[3] 王志理,王如松.中国流动人口带眷系数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与经济,2011,(6).
[4] Jacob Mincer.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8,(8).
[5] Steven H. Sandell. Women and the Economics of Family Migration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7,59(4).
[6] 王春超,张静.中国农户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农户跟踪调查的研究[J].经济前沿,2009,(10).
[7] 谭深.家庭策略,还是个人自主?——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式的性别分析[J].浙江学刊,2004,(5).
[8] 孙朝阳.家庭策略视角下农村已婚劳动力转移的性别选择[J].安徽农业科学,2009,(1).
[9] 蔡昉.迁移决策中的家庭角色和性别特征[J].人口研究,1997,(3).
[10] 马瑞,徐志刚,仇焕广,白军飞.农村进城就业人员的职业流动、城市变换和家属随同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1,(1).
[11] 陈宇峰.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新古典批判[J].经济学家,2005,(4).
[12] 何大安.行为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J].中国社会科学,2004,(4).
[13] Connell John, Dasgupta Biplab, Laishley Roy, Lipton Michael. Migration from Rural Areas: The Evidence from Village Studies [M].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24-25.
[14] 唐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J].社会学研究,2010,(3).
[15] 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0,(4).
[16] 费孝通.乡土中国[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4.
[17] 洪小良.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07,(6).
[18] 盛亦男.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J].人口研究,2013,(7).
[19] Stark Oded, D. Bloom.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
[20] 蔡昉,都阳.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检验相对贫困假说[J].中国人口科学,2002,(4).
3. 迁居的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城市的就业、教育等对流动人口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他们对未来的目标还不明确。有些举家迁居的家庭,他们在城市中拥有相对稳定的生活,但可能因户籍、生活成本等原因,对长期定居持有疑虑。家庭在流出地的宅基、耕地、社会关系,使流动人口怀有故土感情,想“有空就回去看看”(C08,女,26岁),甚至“我们两个人(丈夫和妻子)都想回家养老”(C10,男,32岁)。几乎所有参与访谈的流动人口都表示不会放弃在家乡的宅基和耕地。宅基、耕地不仅具有“风险规避”的意义,也是流动人口心理上的寄托。
C09(女,39岁):现在在当地(城市)已经买了房,也有了车,生活过得还可以。但就是没有户口。目前父母和孩子现在都在身边,在老家的房产、土地现在都让弟弟照看,收入也归他。以后在城里更稳定一点,可能会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不过等我和老公年龄大一些之后,我们还可能回老家盖房,在老家养老。
C12(男,34岁):孩子在这上中学,生意在这里发展,经济收入都已经投入在这里,不能轻易就放弃这边的生活。眼下自己还年轻,还想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短期内都会在这里生活,现在不会考虑回家。但是,如果老人身体不好了,肯定会回家照顾老人。家里的老宅子也还得留着,以后我们老了也许还要回去呢。
流动家庭对未来养老地点的期望也体现了迁移结果的不确定性(见表2)。对未来养老地点需要“看经济条件再定”和“没想过”的比例共计43.12%。这表明,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对未来在城市中长期生活还持观望态度。除此之外,选择返回户籍所在地农村的居首位,占31.84%,显示了家庭回迁决策在生命周期中的阶段性。而回到户籍所在地城镇的约占10.21%。相对大中城市而言,小城镇的消费水平更低,也便于流动家庭与农村家庭密切联系。在户籍所在地的小城镇养老,成为流动人口的另一种选择。“以后是不是要长期留在北京,还要看情况再做打算。等孩子上小学了就回老家去做个小生意。我们濮阳的房价今年六千一平米,这还是当地最贵的,所以回老家去,日子过得比在北京强多了。”(C17,男,30岁)
五、 小结
本研究将家庭迁居决策总结为五阶段的决策链条。五阶段是指家庭迁居决策的商议期、配置期、决策期、跟随迁居期、迁居结果期全过程。
家庭的决策起始于家庭的内部商议,因此,第一阶段是商议期。在商议期中,家庭成员通过商议决定家庭是否迁居,以及确定外出流动的人数、地点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家庭更多地体现出协商共议的协商模式。传统的家庭制度与家庭成员关系模式受到人口流动的冲击,降低了父权的绝对控制地位,未婚的女性也同样拥有议价的权力。家庭迁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或花费相对较少的成本(中小城镇),来获得家庭整体收入——成本的最满意。
当家庭做出向外迁居的决策后,家庭会对内部的劳动力资源重新整合和配置,即为配置期。在先行者外出后,整个家庭会成为一个相互配合、协调运作的整体,通过对家庭成员进行重新分工,保证在外流动的人口能够顺利生活、工作,以维持整个家庭的稳定。
决策期是指家庭通过衡量闲暇与收入效用、流动的预期收入和成本、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等因素,对迁居人数进行选择;按照人口流动的乡村人际关系的差序结构,即按照直系血缘关系、旁系血缘关系以及地缘关系由近至远的顺序,选择迁居地点。
在跟随迁居期,家庭会对留守的家庭成员是否迁居,以及留守家庭成员与首批迁居人口的时间间隔进行决策。经济标准是判断迁居间隔的最主要因素。一般而言,当首批迁居的人满足一定的经济条件后,才会将其他家庭成员带到城市中。
迁居结果期,流动家庭会对定居或回流进行决策。流动人口对返乡或定居的选择与家庭生命周期密切相关,同时也体现着传统代际关系的转变。孩子的教育问题将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回流的主要因素,高额的教育成本会促使流动家庭返乡。对老年人的赡养会通过家庭内部资源的重新分配来解决,当老年人需要照料时,流动人口可能会选择回流,或者将老人接到城市中共同生活。从当前我国家庭化迁居的情况来看,户籍制度的制约以及大城市中高昂的生活成本成为流动家庭定居的最大困难,流出地的家庭禀赋是流动家庭的最后一道保障,也是他们的心理寄托。这使得迁移的最终结果体现出“走一步、看一步”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2012年农民工监测报告[EB/OL].[2013-05-27]http://www.gov.cn/gzdt/2013-05/27/content_2411923.htm.
[2] 张文新.近十年来美国人口迁移研究[J].人口研究,2002,(7).
[3] 王志理,王如松.中国流动人口带眷系数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与经济,2011,(6).
[4] Jacob Mincer.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8,(8).
[5] Steven H. Sandell. Women and the Economics of Family Migration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7,59(4).
[6] 王春超,张静.中国农户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农户跟踪调查的研究[J].经济前沿,2009,(10).
[7] 谭深.家庭策略,还是个人自主?——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式的性别分析[J].浙江学刊,2004,(5).
[8] 孙朝阳.家庭策略视角下农村已婚劳动力转移的性别选择[J].安徽农业科学,2009,(1).
[9] 蔡昉.迁移决策中的家庭角色和性别特征[J].人口研究,1997,(3).
[10] 马瑞,徐志刚,仇焕广,白军飞.农村进城就业人员的职业流动、城市变换和家属随同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1,(1).
[11] 陈宇峰.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新古典批判[J].经济学家,2005,(4).
[12] 何大安.行为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J].中国社会科学,2004,(4).
[13] Connell John, Dasgupta Biplab, Laishley Roy, Lipton Michael. Migration from Rural Areas: The Evidence from Village Studies [M].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24-25.
[14] 唐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J].社会学研究,2010,(3).
[15] 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0,(4).
[16] 费孝通.乡土中国[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4.
[17] 洪小良.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07,(6).
[18] 盛亦男.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J].人口研究,2013,(7).
[19] Stark Oded, D. Bloom.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
[20] 蔡昉,都阳.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检验相对贫困假说[J].中国人口科学,2002,(4).
3. 迁居的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城市的就业、教育等对流动人口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他们对未来的目标还不明确。有些举家迁居的家庭,他们在城市中拥有相对稳定的生活,但可能因户籍、生活成本等原因,对长期定居持有疑虑。家庭在流出地的宅基、耕地、社会关系,使流动人口怀有故土感情,想“有空就回去看看”(C08,女,26岁),甚至“我们两个人(丈夫和妻子)都想回家养老”(C10,男,32岁)。几乎所有参与访谈的流动人口都表示不会放弃在家乡的宅基和耕地。宅基、耕地不仅具有“风险规避”的意义,也是流动人口心理上的寄托。
C09(女,39岁):现在在当地(城市)已经买了房,也有了车,生活过得还可以。但就是没有户口。目前父母和孩子现在都在身边,在老家的房产、土地现在都让弟弟照看,收入也归他。以后在城里更稳定一点,可能会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不过等我和老公年龄大一些之后,我们还可能回老家盖房,在老家养老。
C12(男,34岁):孩子在这上中学,生意在这里发展,经济收入都已经投入在这里,不能轻易就放弃这边的生活。眼下自己还年轻,还想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短期内都会在这里生活,现在不会考虑回家。但是,如果老人身体不好了,肯定会回家照顾老人。家里的老宅子也还得留着,以后我们老了也许还要回去呢。
流动家庭对未来养老地点的期望也体现了迁移结果的不确定性(见表2)。对未来养老地点需要“看经济条件再定”和“没想过”的比例共计43.12%。这表明,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对未来在城市中长期生活还持观望态度。除此之外,选择返回户籍所在地农村的居首位,占31.84%,显示了家庭回迁决策在生命周期中的阶段性。而回到户籍所在地城镇的约占10.21%。相对大中城市而言,小城镇的消费水平更低,也便于流动家庭与农村家庭密切联系。在户籍所在地的小城镇养老,成为流动人口的另一种选择。“以后是不是要长期留在北京,还要看情况再做打算。等孩子上小学了就回老家去做个小生意。我们濮阳的房价今年六千一平米,这还是当地最贵的,所以回老家去,日子过得比在北京强多了。”(C17,男,30岁)
五、 小结
本研究将家庭迁居决策总结为五阶段的决策链条。五阶段是指家庭迁居决策的商议期、配置期、决策期、跟随迁居期、迁居结果期全过程。
家庭的决策起始于家庭的内部商议,因此,第一阶段是商议期。在商议期中,家庭成员通过商议决定家庭是否迁居,以及确定外出流动的人数、地点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家庭更多地体现出协商共议的协商模式。传统的家庭制度与家庭成员关系模式受到人口流动的冲击,降低了父权的绝对控制地位,未婚的女性也同样拥有议价的权力。家庭迁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或花费相对较少的成本(中小城镇),来获得家庭整体收入——成本的最满意。
当家庭做出向外迁居的决策后,家庭会对内部的劳动力资源重新整合和配置,即为配置期。在先行者外出后,整个家庭会成为一个相互配合、协调运作的整体,通过对家庭成员进行重新分工,保证在外流动的人口能够顺利生活、工作,以维持整个家庭的稳定。
决策期是指家庭通过衡量闲暇与收入效用、流动的预期收入和成本、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等因素,对迁居人数进行选择;按照人口流动的乡村人际关系的差序结构,即按照直系血缘关系、旁系血缘关系以及地缘关系由近至远的顺序,选择迁居地点。
在跟随迁居期,家庭会对留守的家庭成员是否迁居,以及留守家庭成员与首批迁居人口的时间间隔进行决策。经济标准是判断迁居间隔的最主要因素。一般而言,当首批迁居的人满足一定的经济条件后,才会将其他家庭成员带到城市中。
迁居结果期,流动家庭会对定居或回流进行决策。流动人口对返乡或定居的选择与家庭生命周期密切相关,同时也体现着传统代际关系的转变。孩子的教育问题将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回流的主要因素,高额的教育成本会促使流动家庭返乡。对老年人的赡养会通过家庭内部资源的重新分配来解决,当老年人需要照料时,流动人口可能会选择回流,或者将老人接到城市中共同生活。从当前我国家庭化迁居的情况来看,户籍制度的制约以及大城市中高昂的生活成本成为流动家庭定居的最大困难,流出地的家庭禀赋是流动家庭的最后一道保障,也是他们的心理寄托。这使得迁移的最终结果体现出“走一步、看一步”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2012年农民工监测报告[EB/OL].[2013-05-27]http://www.gov.cn/gzdt/2013-05/27/content_2411923.htm.
[2] 张文新.近十年来美国人口迁移研究[J].人口研究,2002,(7).
[3] 王志理,王如松.中国流动人口带眷系数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与经济,2011,(6).
[4] Jacob Mincer.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8,(8).
[5] Steven H. Sandell. Women and the Economics of Family Migration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7,59(4).
[6] 王春超,张静.中国农户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农户跟踪调查的研究[J].经济前沿,2009,(10).
[7] 谭深.家庭策略,还是个人自主?——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式的性别分析[J].浙江学刊,2004,(5).
[8] 孙朝阳.家庭策略视角下农村已婚劳动力转移的性别选择[J].安徽农业科学,2009,(1).
[9] 蔡昉.迁移决策中的家庭角色和性别特征[J].人口研究,1997,(3).
[10] 马瑞,徐志刚,仇焕广,白军飞.农村进城就业人员的职业流动、城市变换和家属随同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1,(1).
[11] 陈宇峰.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新古典批判[J].经济学家,2005,(4).
[12] 何大安.行为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J].中国社会科学,2004,(4).
[13] Connell John, Dasgupta Biplab, Laishley Roy, Lipton Michael. Migration from Rural Areas: The Evidence from Village Studies [M].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24-25.
[14] 唐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J].社会学研究,2010,(3).
[15] 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0,(4).
[16] 费孝通.乡土中国[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4.
[17] 洪小良.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07,(6).
[18] 盛亦男.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J].人口研究,2013,(7).
[19] Stark Oded, D. Bloom.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
[20] 蔡昉,都阳.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检验相对贫困假说[J].中国人口科学,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