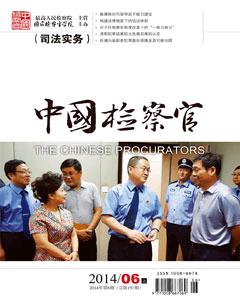略议贪污罪的主体身份与共犯数额
文◎范连玉
略议贪污罪的主体身份与共犯数额
文◎范连玉*
本文案例启示:贪污罪的主体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的人员或上述机关、单位委派到其他单位的人员,且须依照法律从事公务。贪污集团的首要分子对整个集团所犯的罪行承担责任,贪污犯罪集团的一般主犯和一般共同贪污犯罪案件的主犯对其所参与的犯罪数额承担责任,共同贪污犯罪的从犯以其参与的犯罪数额承担责任并应从宽处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100872]
[基本案情]黄某原任孝南区毛陈镇西汊村村委会主任,程某原任高村村委会委员兼报账员。2008年4月,孝南区某局为该村维修泵站,黄某利用职务之便,将政府留给该村的一套抗旱排涝设备作价12700元抵给某局,所得款项被黄某据为己有;2009年至2012年3月,国家对农户种田进行补贴,黄某将村集体16.9亩的土地面积指使程某以黄某二哥为户主上报,骗取国家惠农资金4365元,账款被黄某据为己有;2012年下半年,孝硚高速公路征用该村土地。在征地补偿过程中,黄某指使程某将黄某被征土地多报0.763亩,并将村集体0.4亩土地以黄某妻子为户主上报,两项共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15119元,账款被黄某据为己有;2012年下半年,程某在协助毛陈镇从事孝硚高速公路征地补偿款的发放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将村集体土地2.973亩以个人名义上报,并将征地款38649元据为己有。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第一、黄某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第二,在认定程某与黄某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形下,黄某、程某各自应对多大的数额负责?
一、关于贪污罪主体身份的理解和认定
首先,根据刑法第93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有两个特征:第一,必须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的人员或者上述机关、单位委派到其他单位的人员。第二,必须依照法律从事公务。根据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会谈纪要》(以下简称 《纪要》),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特定条件下行使国家管理职能;二是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具体包括:(1)依法履行职责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依法履行审判职责的人民陪审员;(3)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农村和城市基层组织人员;(4)其他由法律授权从事公务的人员。
其次,根据《纪要》,“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那些不具备职权内容的劳务活动、技术服务工作,如售货员、售票员等所从事的工作,一般不认为是公务。
最后,在实施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时,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利用了自己职务上的便利,如果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尽管实施了行为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也不能认定为贪污罪。因此,如何理解“利用职务便利”,也就影响到对主体行为的定性。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营、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主管,主要是指负责调拨、处置及其他支配公共财物的职务活动;管理,是指负责保管、处理及其他使公共财物不被流失的职务活动;经营,是指将公共财物作为生产、流通手段等使公共财物增值的职务活动;经手,是指领取、支出等经办公共财物的职务活动。不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要件,相对于不同的贪污行为而言,具有不同的含义。
在本案中,对于政府留给该村的一套抗旱排涝设备,作为孝南区毛陈镇西汊村村委会主任的黄某对其负有协助政府管理职责,符合“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因此,黄某利用自己职务便利,将抗旱排涝设备作价12700元抵给某局所得的款项据为己有,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
同时,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以下简称 《解释》),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产的,应以贪污罪论处。黄某协助政府进行农户种田补贴和公路征地补偿款的发放工作,属于《解释》所规定的“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因此,黄某利用自己职务上便利,指示程某骗取惠农资金和征地补偿款总计19484元,属于共同贪污犯罪。程某作为高村村委会委员兼报账员,在协助毛陈镇政府从事孝硚高速公路征地补偿款的发放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将村集体土地2.973亩以个人名义上报所获得的征地款38649元据为己有,也符合上述《解释》之规定,应以贪污罪论处。
二、共同贪污犯罪中“个人贪污数额”的理解与认定
根据刑法第383条的规定,对于个人实施的贪污犯罪,依照罪责自负的原则,以“个人贪污数额”确定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但在共同贪污犯罪的情形中,这里的“个人贪污数额”究竟是指犯罪总额、参与数额、分赃数额还是平均数额,规定并不明确,导致各共犯应对什么样的数额负责就成为了理论和实务界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对此,在1997年刑法颁布前,刑法理论上有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犯罪总额说、分担数额说、平均数额说和综合数额说等不同主张。
分赃数额说认为,各共犯只对自己实际分得赃物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此说将个人非法所得的数额作为处罚的基础,体现了罪责自负的原则。但对于贪污未遂、贪污既遂但尚未分赃或共同挥霍贪污所得的情况以及数人共同参与贪污,其总的数额达到了贪污罪的定罪数额标准,但单凭各共犯分得的赃物数额都达不到定罪数额标准的情况下,如何定罪处罚却无法处理。分担数额说主张根据各共犯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参与的数额、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地位、作用和整个案情,确定各共犯应承担百分比的责任来换算责任份额。该说注意到了各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却忽视了共同犯罪刑事责任的整体性这一特点。参与数额说主张各贪污共犯应对本人实际参与的贪污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该说有一定可取之处,尤其对于一般主犯和从犯是可以适用的,但不能适用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综合数额说认为,应综合考虑全案因素,确定各共同贪污犯罪行为的大小,然后据此定罪量刑。此说实际上并未提出任何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标准,不利于实践操作。平均数额说认为,对各贪污共犯的处罚应当依照各共犯所得贪污总额的平均数额来分担刑事责任。该说对于解决贪污未遂和贪污既遂但尚未分赃或共同挥霍贪污所得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借鉴之处,但也存在与分担数额说一样的缺陷。犯罪总额说主张以共同贪污犯罪的总额确定各贪污共犯的刑事责任。此说要求各贪污共犯对整个犯罪数额负责,固然体现了共同犯罪原理,但不加区别地要每个罪犯都承担其他共犯的罪责,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尽管学者间关对“个人贪污数额”存在分歧,但《纪要》对此作出了较为合理的界定:刑法第383条第1款规定的“个人贪污数额”,在共同贪污犯罪案件中应理解为个人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共同贪污的数额,不能只按个人分得的赃款数额来认定。对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从犯,应当依照其所参与的共同贪污的数额确定量刑幅度,并依照刑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然而,司法实践中应如何确定各共犯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尚存有解释的空间。
笔者认为,根据共同犯罪的责任原理,依照刑法第26条第3款、第4款以及第27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各共犯应承担责任的“个人贪污数额”,适用刑法第383条第1款各项所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可以为各共犯选定所应适用的法定刑幅度,即贪污集团的首要分子对整个集团所犯的罪行承担责任,贪污犯罪集团的一般主犯和一般共同贪污犯罪案件的主犯对其所参与的犯罪数额承担责任,共同贪污犯罪的从犯也是以其参与的犯罪数额承担责任并应当对其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在本案中,黄某单独作案一次,共同作案两次,其犯罪数额为32184元;程某单独作案一次,共同作案两次,犯罪数额为58133元。这里的犯罪数额是指黄某、程某个人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共同贪污的数额,而不是黄某、程某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