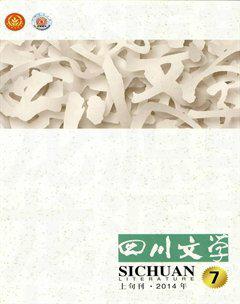意外(小小说二题)
◇李 云
一
汪市场教儿子汪小胖写“民”字。儿子,他说,民工、人民、人民币,都有民,这是个多么常用的字!你老爸我几乎天天跟民打交道,这个字下面的两提勾都向右,这一点都不难对不对?你们老师说你不会写,怎么可能?你老爸我这么聪明能干,儿子也不会笨,是不是?汪小胖使劲点头。
很快,汪市场发现,汪小胖写的这个字,下面的两笔提勾老是向左。汪市场捉住他的手,一笔一划地耐心地教,可能教了一百遍,可刚放手让儿子自己写一个,汪小胖还是把提勾朝左边勾去。是可忍孰不可忍,啪!一个耳光赏过去,汪市场咆哮着冲进厨房,拖出正在做饭的老婆李翠花:“你去教!气死老子了!”
汪市场在厨房抽闷烟,回想起开家长会的情景。
儿子汪小胖上小学一年级了。按户籍就近入学汪小胖该读镇里的小学,可汪市场仗着自己在县城里修了几个菜市场,认识一些人物,就花了一笔重金把儿子送进了县里最好的实验外国语学校。他指望儿子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好大学,成为有文化的人,不要像他除了钱啥都没有,明里暗里被人洗涮戏弄。他本来叫汪富贵,硬被别人改成汪市场。他听着心里不爽,感觉有轻蔑的意思。可他不能跟人较真,人说是抬举他呢。
老师按孩子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把家长分成了三堆。对三堆家长讲不同的事不同的问题,说不同的话。最后把汪市场留下来了,说他儿子的问题比较特殊,所以他不属于三推中任何一堆。为什么特殊呢,因为汪小胖不会写民字,必须把这个任务布置给家长,叫他回家教。汪市场想这还不容易,就拍胸口保证教会。
现在他算是失败了,痛苦地揪着头发,把希望寄托在老婆身上。
老婆又教了数十百遍,汪小胖还是要把民字下面的两提勾向左勾。他手中的笔好像中了魔似的非要朝左,任爹妈怎么骂怎么打毫不改变。
汪市场听见老婆大呼小叫喊拿板子来,他立即拖着一米长三寸宽的钢板过去,汪小胖躲在墙角瑟瑟发抖,一见那钢板,猛地把衣服撩起蒙住脑袋,像一只顾头不顾尾的鸵鸟。汪市场抡起钢板没有打下去。只一屁股坐在地上,指着墙角,气急败坏:“你、你、你不是我的儿。”
他老婆白了他一眼,像牛一样喘粗气:“你什么意思?什么叫不是你的儿?”
汪市场打了一个激灵。他本来气头上一骂,被老婆如此一问,倒提醒了他什么。此后三天,汪市场不吃不喝躺在床上像死人一般。
第四天,汪市场跟老婆说,他要到外省去谈个生意。
汪市场这一走就没回来。李翠花意识到他不会再回来后才去查看,家里的现金、存折、卡和账本都不在了。她本打算去报警的,可想了一想,自己手里还有这套住房和商铺呢,再说还有个儿子呢,就由他去吧。
离家出走的汪市场在一个和以前完全没了往来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他把以前认识的一个女人接来了,住在一起,一心想再生个儿子。这一次他得保证儿子绝对是他的种,现在这个女人成天和他守在一起,在这个地方不认识任何人。
他老婆李翠花也算是个精明过人的人了,跟随他摸爬滚打多少年,一直做他的会计兼出纳,过手的钱像河里的水哗啦哗啦地日夜流淌,从没出过差错。而现在这个女人的头脑似乎比李翠花的还好用,说话滴水不漏,做事八面玲珑,汪市场想,跟这个女人一起生个孩子,无论是男是女都应该不会有问题。
一年后,汪市场的手上就抱着一个婴儿了,还是个男婴,他简直高兴得快疯狂了。他认为上帝待他不薄,给了他无限希望。
他又开始拼命赚钱。为这个宝贝儿子建立教育基金。
一转眼,这个小儿子又上小学了。汪市场很紧张,怕开家长会。每次他都让孩子他妈跟学校老师联系。每次他都问老师说什么没有,那女人都说没有说什么呀。孩子看上去健康、正常的,他便放下心来。
孩子读二年级时,有一天汪市场鬼使神差翻看了他的写字本,突然大叫一声“天啊,我的老天啊”,晕倒在地。原来小儿子也和汪小胖和一样,写的“民”字,下面两提勾一律向左。
二
这天,张迪上车发现一号位有人坐了,是一个时髦女郎,穿着一件金黄色的紧身衬衣。他摸出自己身上的票,递到那位女郎面前,很客气地说:
“请你看看你的座位号。”
那女郎瞟了他一眼没有反应。
他站了一会,对她说:“我晕车,所以两天前我就预定了这个位子。”
张迪是一个科研人员,他们的科研基地在距市区120公里的一个山沟里。进出沟里的路蜿蜒曲折凹凸不平,每个月他都有三四次往返。每次无论坐什么车他都晕晕乎乎很是难受。后来他发现乘坐长途公交车似乎要好受点,于是他长期预定这条路线的长途车的一号位子。一号位在司机背后,靠窗。每次往返他都坐一号位。久而久之,他和司机、票务员混熟了,买不买票那个位子都会留给他,已成惯例了。
这时女郎淡淡地说一句:“我也晕车。”
“那你应该早点买下这个位子的票呀。”张迪说。
“那我现在就买这个位置。”女郎掏出一张100元大票递给售票员。售票员看一眼张迪,没有动弹。
张迪说:“这张票我已经买了,钱给他没用的!”。
乘客陆续上车,有票的依票号入座,没票的现场买。人们对争抢座位的事习以为常了,所以都只冷眼旁观。
司机走过来调解,对女郎说:“美女,这个帅哥提前买了票,他坐自己的位子不是很应该吗?你说是不是?请你起来让他。”
女郎说:“大哥,票是虚的,座位是实的。谁先来就先坐。”
“不讲理是不是?你太不可理喻了!”张迪气愤地伸手去拉女郎的胳膊。
女郎说:“别碰我啊,就算你有理,碰了我就没理了。”
张迪想想也是,这下拿她没辙了。
看来她就是耍无赖也铁了心要抢这个座位。
司机看局面僵持了,转而跟张迪商量,说下一班车相隔十分钟,他可以打电话请售票员把下班车的一号位留出来,希望张迪同意。
只能如此了。张迪只好下车等了将近一刻钟,坐上了另一班车。
上路不久,张迪他们就被告知:前一趟车出车祸了。
司机更加谨慎,小心翼翼地驾驶。售票员开始动员乘客做好抢救伤员的准备。
等他们赶到一个急弯处,就看见前一班车掉到了几十米深的悬崖下,车已散架,乘客四处散落。他们是最先赶来救援的人。
大家紧急救人,张迪这一辆车上的所有人都开始行动。哭喊声、呼救声响成一片,那场景真是太惨了,车内车外都是伤者,有的只剩一口气,有的气都没了。乘客的随身物品遍地都是。
张迪搬掉一堆扭变形了的座椅,发现下面躺着一个年轻女郎,已经昏迷过去,无声无息,那件金黄色衬衣他是熟悉的,半小时前,他和她因为争抢座位而争吵。
张迪一把抱起了她,那女子已然面目全非,但她睁开了血肉模糊的双眼。张迪立刻安慰道:“别怕,现在没事了,没事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抱起她走向路边,找一处平坦处轻轻放下,嘴里还不停安慰道:“马上救护车就到了,你坚持一下呵!”说完想站起身,再去救人。
他的衣袖被拉住了,是女子拉住了他。躺在地上的她,艰难而真诚地说:“对不起,刚才,我、我、抢了、你的座。”
张迪想说“没关系”,可说不出口。他心绪复杂,你抢了我的座能没关系吗?这关系多大呀!本来应该是我受伤的,硬生生被你抢去了,你哪是抢了我的座,你是抢了遭遇车祸的劫难呀。你替我去赴难的,应该是我对你说“对不起!”
张迪哽咽着鼓励她挺住,马上就有救护车来了。
张迪就那样半搂着她,为她流着泪,也为自己的侥幸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