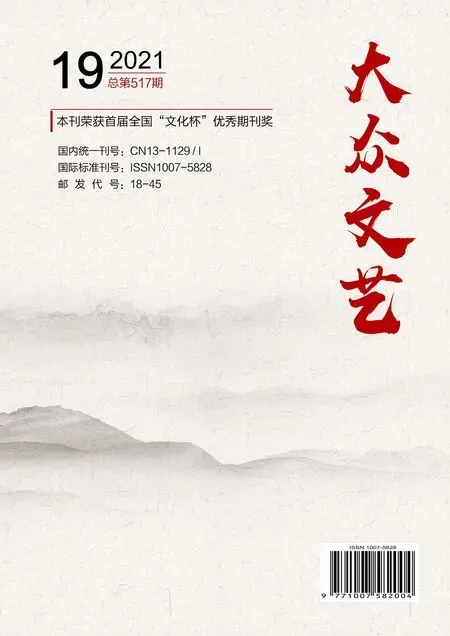超古典主义叙事
——黔东南当代民族水墨创作管窥
(凯里学院艺术学院 556011)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主要以苗族、侗族文化为主。在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通和碰撞中,发展出超越古典主义水墨视觉经验之上的绘画表现形式——超古典主义民族水墨,其主要基于本土苗族和侗族的山水、人文、景观等绘画内容,介由黔东南水墨画家作为创作和传播的主体,抒写真山真水。如果说评价艺术家的艺术价值,是要看艺术家在美术史上的影响和地位,那么,黔东南的当代民族水墨创作形式在中国当代水墨史中的探索,是否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美术史中的上下文关系
中国自近代以来所构筑的知识体系早已深深地烙上了现代主义的痕迹,中国现当代的美术学体系,基本上是美其名曰的“国际化”路线。如今依然有不少美术研究学者探索中国艺术本土化或民族化的可能性途径,并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实验,但在艺术本体论的阐释域度中,这个命题依然悬置,没有形成彻底而完整的学术标准。而且在当代的艺术语境中,还往往沦为靠贩卖中国符号而谄媚西方人的把戏。对于新中国美术来讲,始终存在着一种本土艺术“逆生长”的文化现象。正因如此,发展“油画民族化”和“现代水墨画”的声音始终回荡在当代中国美术的山谷。更有甚者,在八五美术新潮运动以后开始呼唤艺术自律,却仍旧是对照西方形式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文化逻辑的邯郸学步。
1985年,《江苏画刊》刊发了李小山的文章《当代中国画之我见》,对于中国画的命运,发出了急迫而焦虑的声音“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这个论调并非中国画坛的现状,却忍不住让我们回望已在博物馆中被束之高阁的藏品,黄公望、八大山人的山水画灿若星辰,却反衬当代水墨甚至山水画的黯淡无光。不是我们的画家出了问题,而是被两个方面扣住了命门:一是自清代以来的拟古和泛古,使我们在审美观念中推崇古格厚重的历史。二是中国传统水墨画,特别是山水画,无论在内涵还是形式上均策源于中国文化的积淀,并在民族性话语的图式表达中彰显时代趣味。既然清楚地发现了这样的事实,如果再一味地仿古,那便只能用新文化和古文化断层后的艺术形式和用传统眼光来作水墨画,而无法在当代语境中实现当代水墨画的图式转换。在当代水墨领域如此,在民族水墨创作中亦然,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撑起民族水墨的脊梁呢?以黔东南州代表的苗、侗民族山水画创作语言颇有自足的叙事意味。
二、黔东南超古典主义水墨的文化逻辑
古典意义上的中国水墨画发展到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的时代,便已逐渐从典范走向式微,尽管中国当代水墨画家决意抓住现代水墨的稻草,但斩获甚微。当我们看到一大批单纯为了追求观念而索然无味的图式,并用时过境迁的艺术观点装扮自己的时代新衣,我们不禁要站在民族文化的逻辑中去探索本土水墨的视觉图式。
(一)超古典主义水墨自述
从艺术史的逻辑发展来看,超古典主义是从未出现过的专有名词,与之相对的则是我们对于“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认知。古典主义,在西方艺术上主要是指上至古希腊及古罗马的古典时代文化的认同;中国现代文化学术界对古典主义的界定则是以古典时代的文化品味作为评判价值高低的标准,并试图模仿其风格。无独有偶,在古典主义的发展脉络中,曾一度在法国拿破仑时期,出现过新古典主义,其内涵旨在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主义艺术样式,所以马克思曾用一句话来评价新古典主义,称其就是“穿着古罗马的服装,用借来的语言,上演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超古典主义”是区别于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概念,它不复兴任何中国艺术史中的古典水墨样式,它是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美术家协会的一些水墨画家群体组成的,旨在传承中国传统水墨的笔墨人文情境,以表现现代化语境中,黔东南州的青山、绿水、飞瀑、吊脚楼、古楼、花桥、古榕、梯田和水车等为视觉文化资源为图式诉求的水墨创作形式。其中涌现出来一批以侗族画家杨长槐和欧阳克景为代表的,旨在传承黔派山水的艺术家。
杨长槐擅画水,其作画特点既注重对传统之研习、传承,更注重对自然的观察与领会,其画水之法可谓另辟新径。画家从乌蒙山高处飞泻下来的“天水”,从黄果树瀑布倾泻在白水河上的奇异景象,得到创造的灵感。观他画中激流飞瀑,巨流奔泻,既有水的聚散无端、无所不往、奔腾不息的精神,又赋予了水更多的精神文化内涵,而画家自身也从其中得到情感的倾注与表述的满足,对于观看者而言,则从画家充满激情的绝技中得到图像强大的视觉表现力的震撼。王朝闻先生曾评说:“在贵阳花溪观长槐山水画新作,深感九年来他飞跃般超越自我,纸上之激流或飞瀑无声胜有声,丰富了马远所探索之山水画法,这一可喜成就基于长槐熟谙黔山黔水之独特个性。”
(二)苗侗诗性水墨的超古典主义内涵
诗人荷尔德林说:“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但就这句诗而言,便是黔东南文化特征的集中体现。黔东南的视觉文化是以《苗族古歌》为创作蓝本,并用视觉形式加以物化,由于苗侗民族没有文字,于是绘画与民族工艺便成为图载文化,而代代传唱流传,因此黔东南的古典艺术传统是饱含诗性的,也就进一步导致了作为民族水墨现代化的超古典主义自诞生之日起,便如原始美术史诗般的情调般富有美的韵律。而就后古典主义水墨而言,不妨借助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理论:一方面,所谓诗意的栖居,我们要根据栖居的本质来衬托黔东南民族的生存;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把诗的本质比兴为水墨绘画,甚至超越水墨画形式本身的一种文化内涵,也许是进一步超脱时代语境,寻求诗与栖居的本质属性。同海德格尔的思想一样,超古典主义的文化内涵本身便具有东方禅悦的境界
(三)黔东南超古典主义水墨画的滥觞
黔东南历来把写生创作作为实验水墨的根基,所以超古典主义的水墨创作均来自苗岭侗寨,来自每一首动人的山歌,所以黔东南的山水画最为打动人的,不在于它的传统承续,也不在于它的现代形态,而是那种从水墨语言中折射出来的民族情境,是苗侗画家带有自传性的生活经验和人格显现。
纵观中国当代水墨,我们无法在众多的名家中搜索到领军者,这个时代最不需要的就是那种仅仅能够继承文化传统的艺术家,而是能够具有美术史价值的艺术家。超古典主义正在进行这样一场运动:使每个黔东南的美术家深入村寨、深入民间,在现代化民族图式探索的基础上,抛弃严格的技术规范和僵化的审美标准,创造出真正具有超古典主义意味的笔情墨趣来。有基于此,黔东南的超古典主义水墨创作,既不会仰视西方文化,也不会圈住传统抱残守缺。苗侗民族的生活经验和向国际开放的现代观念将给黔东南的水墨画拓宽新的天地,这些图式经验的转换,我们可以从黔东南本土的艺术家创作中可见一斑。
三、欧阳克景的超古典主义实验
在中国绘画史中,山水画的发展有着自己清晰的文脉。水墨山水作为“文人画”的必经之路昭示着中华民族集体的文化智慧,却也因文人相轻而桎梏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创造动力。有基于此,欧阳克景有着自己的体认,他师从侗族山水画家杨长槐先生,习得黔山黔水的造化奇崛之妙,并以苗岭侗寨的真山真水为起点,同时又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文化态度兼采西方现代绘画,使其作品呈现出跨文化的审美理想。
近两年来,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作品中的两点变化:其一,深入黔东南腹地开展写生创作,寻找自己的绘画个性。他选择黔山黔水民族村寨的原因固然有浓郁的民族情结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作为土生土长的黔东南人这里的山水形态和民族人文可以为画家提供自由、宽广的水墨表现空间。现代的叙事语境,水墨的放纵挥洒,书写性的勾勒以及水波空间无限延展的可能性,都可以在它的山水画中得到印证。其二,在不背离传统笔墨精髓的基础上,探寻现代化语境中民族山水画创作新的可能性。与传统图式大相径庭的是,时代背景孕育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因此民族村寨现代化生活的标志汽车、摩托车和机动三轮车在与农耕时代的运输方式——挑担和人力运输的图式在山水画中分庭抗礼,他在用这种有趣的图像冲突,表现山水画中的非常态情境,深山藏村寨,苗侗醉清风,只有在诗意的环境里,山木泉石的水墨语言才会得以凸显。这些都是他在迈向超古典主义绘画语言的尝试,
结语
台湾现代水墨之父刘国松先生曾说:“我们作为中国的水墨画家,既不能完全抱住古人的尸骨不放,也不能跟着西方的乐队起舞。我们应该想,我们能对中国文化做些什么?”当许多当代画家仍旧在试验水墨姓中还是姓西,甚至中西合璧之时,黔东南的水墨画在当代水墨艺术中提示出民族语言的问题意识,另辟出称之为超古典主义的叙事语言。
参考文献:
[1]李小山.当代中国画之我见[J].江苏画刊,1985(7).
[2](德)海德格尔.人,诗意的安居[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3]舒世俊.《水墨的诗情——从传统文人画到现代水墨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4]东山魁夷.《中国纪行——水墨画的世界》[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
[5]鲁虹.《现代水墨二十年》[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6]多米尼克·塞克里坦.《古典主义》[M].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