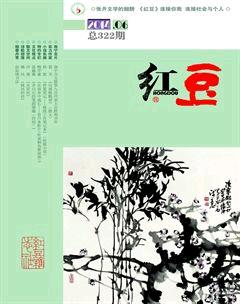文字的疆域(评论)
毕亮,1985年生于安徽桐城,现居新疆伊犁。新疆作家协会会员。
一、关键词:寻找
“我既不清楚来时的路,也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要去的方向。”葛芳说。
去年春天,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和葛芳成为同学。因为她曾经在新疆生活过,也因为她有亲戚在我生活的伊犁,话题就从这里开始,慢慢就熟识起来……两个月后各奔南北,她回到苏州,我还在伊犁,各忙各的,偶尔联系。突然有一天她在QQ上说,说要去南极了,我们都很惊讶。之后她就不声不响出发了。
时间到了今年春节(去年,我们也是春节一结束就去往鲁院),就读到了葛芳以南极之行为背景、经历的长篇散文,才对她的南极行前后有了少许了解。
评论家韩子勇就认为作为私有文体,散文是与个体生命亲密无间的,也是最人性与人道的文体,它的叙述人称是“我”,它说面对的是“我们”。写小说出身的葛芳大概是深谙其中道理的,她也有着丰富的散文创作经验。这是我看她的散文集后知道的。
葛芳的这一组南极行的散文,与之前的散文集《空庭》《隐约江南》中的篇章、风格等相差不小。或许,前面两本散文集,写的都是熟悉的江南,无意为之,行云流水。而这一组文章,可谓预谋已久,谋篇布局构思良久,多了不少雕琢的痕迹。我觉得这是作者刻意为之,亦如她谋划许久只为到世界的最尽头。
也是在和葛芳熟识后才知道,她在到鲁院前刚刚辞去公职,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职业者,写作成了爱好,也成了她的寄托。当时,我就觉得这不一定是好事。人一旦对某件事期待太多,压力往往随之数倍地增大,写作对于葛芳即是如此。好在从学校回去后,这种情况没在她身上出现。和爱人一起经营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行走、写作。小说、散文,左右开工,佳作不断。葛芳的生活状态,也被班里许多人羡慕。
但细读这些作品不难发现,压力在葛芳身上是很明显存在的。她创作的压力,可谓是多方面的。对葛芳而言,这是好的,也是不好的,一念之间全凭创作者如何把握了。通读鲁院以来葛芳的小说、散文创作,尤其南极之行的系列散文,可以看出葛芳对自己的把握,已经渐入娴熟。
伟大的博尔赫斯说,我的一生都是在书籍中旅行。在他看来,天堂应当是图书馆的模样。爱读书的葛芳必然会和博尔赫斯产生共鸣。有一次从她的微信朋友圈晒的书架上看到了为数众多的博尔赫斯著作。从葛芳的行文来看,受博氏影响也是无法否认的。所以到南极,当有机会途经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寻找博尔赫斯也成了理所当然。在文章《寻找博尔赫斯》里,寻找的状态让人察觉了葛芳的急迫。有些时候,在读文章时甚至有葛芳和博尔赫斯重合的印象,葛芳所要寻找的,正是她自己。之所以如此,难道是因为她深信博氏的用自我否定的方式来思考?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葛芳想要寻找的,在动身出发到南极时,都是不定的,或者说无目标的。“孤独的寻找者,在星空之夜唤起了自己内部压抑已久的力,挣脱了日常观念的所有限制,让灵魂开始做致命的飞翔,以此达到那个虚无纯净的世界。”在《寻找博尔赫斯》之外,作者再以一篇《寻觅》来记录她处于寻找中的状态。
知道要寻找,说明葛芳也知道自己在迷失。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离开体制初期的彷徨,顿时表露无遗。这也仅仅只是短暂的瞬间,到世界最尽头的刚开始,葛芳就找到了“无数种可能”,于是“不再恍惚,澄净空远”。
二、关键词:孤独
“内心的孤独,是一种绵密的情绪。”葛芳说。
和葛芳同在苏州的作家车前子说过,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是压力下的挣扎,有的是社会的压力,有的是家庭的压力,有的是名气的压力,也就是虚荣的压力。
我觉得葛芳的写作,是孤独的压力。我甚至把她的南极之行,看做是这种压力之下的出走。这样的出走当然不是逃离。就像毛姆说的,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最好的批评者。同样的,每个人的孤独也都只有自己最知道。葛芳的认知,可能比常人更清晰。
“很多年以来,体制内的生活心为形役,当不如意、孤独袭击时,我经常一脚油门驱车到太湖,看湖水浩淼,看沙鸥翔集。突然有一天,在快要四十岁时,想明白了。转身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生活原本是为着自己而活,没有必要去牵绊太多无谓的琐碎。”这是一种孤独。也是这种孤独,促使葛芳的逃离,步入另一种孤独中。截然不同的孤独。一种身在樊篱的孤独,另一种是解脱的孤独。通往两种孤独之间的桥梁,即是写作。
罗兰·巴尔特认为写作正是一种自由和一种记性之间的妥协物,它就是这种有记忆的自由,即只是在选择的姿态中才是自由的,而在其延续过程中,已经不再是自由的了。于是产生了孤独。在葛芳的这个系列文章中,可以发现在往南极路上,尽管有一百多个同伴,但孤独无处不在。就和所有的书都是一本书那般,所有的孤独又何尝不是一种孤独?这是我在看到葛芳一再写到孤独时想到的。其实在看葛芳这组散文之前就稍有体悟。
读到葛芳这组散文之前,我刚看完一本记录海上航行的日记集,一百几十天的航行,海员们的孤独在日记里得到了尽情的体现。这种孤独,在我看来和萧红的孤独也相差不大。葛芳的数十天行走南极的孤独亦是如此。孤独不到一定程度,葛芳大概也不会在一篇篇文章中一次次写到孤独来让自己难堪。仅在几百字的《海上漂流梦中醒》短文中,葛芳有不下三次直接写到孤独:“我是真正孤独地在海上漂浮”、“我们彼此孤独着”、“我将在深海中交付我最孤独又单纯的念头”……
写作产生孤独,孤独产生写作,都已不重要。葛芳以几万字来写一次行走,这样的行走对她定然至关重要。何况几万字还是以散文这个文体,而不是其他的文体来呈现,更显得不一般。
对边缘身份文学创作有很深研究的评论家韩子勇在《散文的自由》里说,面对散文,我们永远是新手。每一篇作品出世前都显得笨手笨脚、疑虑重重。那种轻车熟路的人,是危险的。散文是它自己的消耗品,而且是不可再生的复制品,不要指望一篇篇地永远写下去,不要指望一本接一本地辑册成书。
葛芳以消耗自己来成就了长文《到世界的最尽头》。
三、关键词:放逐
“谁会一开始将我自我放逐,在苦难中漂泊终其一生?”葛芳说。
葛芳以远走南极的方式来自我放逐,让熟悉她的人也不免吃惊。比多年前,她只身行走新疆一待数月来得更加彻底。
本雅明在《单行道》里谈到散文写作时,认为写作一篇好散文,要经过三个台阶:宛如作曲时的音乐阶段,宛如筑瓦时造屋的构建阶段以及宛如织布时的编织阶段。看过《到世界的最尽头》,我觉得葛芳以这三个阶段为杆赋予实践。在眼睛的疆域,走到世界的尽头虽然可以什么都不想,但在漫长的黑夜,也只好通过背诵诗歌和散文来对抗黑暗。
这种对抗,与其说是面对黑暗,毋宁说面对的是自己。从体制之笼陡然走出,复得返自然,倒不如更彻底地走到世界尽头再折回。可以说,也是一种重新再来。“灯塔”所给予的希望,没有在黑夜飘扬过海之人无从想象。放逐之后的海阔天空,葛芳真切体会后,欲罢不能。随之产生言说的力量,同样欲罢不能。不知道是否在葛芳放逐时的预料之中。
一切写作都是呈现出被言说的语言所没有的封闭性。写作绝不是交流的工作,它也不是一条只有语言的意图性在其上来来去去的敞开大道。但葛芳在罗兰·巴尔特所谓的不是敞开的大道上却越走越远。终于走到了血脉里。以自己的行万里路、写数万个字来佐证乔伊斯“写你头脑的东西是不行的,必须写血脉里的东西”的结论。值得与否,甘苦自知。看葛芳的写作,自得其乐。
我不知道葛芳在写这些时,是否会感到周作人遇到过的两种困难:其一是说什么,其二是怎么说。且看葛芳洋洋洒洒的下笔,行云流水,知堂先生的困难到底没有发生在葛芳身上?通观《到世界的最尽头》全文,虽是行走文章,却不是平常的游记,也不是走马观花式的印象记。这在人文地理文章大行其道的今天,葛芳此举殊为难得。
毕生很少写游记的孙犁先生,对游记文章却有老道的认识:游记之作,固不在其游,而在其思。有所思,文章能为山河增色,无所思,山河不能救助文字,作者之修养抱负,于山河于文字,皆为第一要义,既重且要。看完葛芳的文章,对孙先生之思,更加服膺于心。或者说,在这里,葛芳和孙犁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