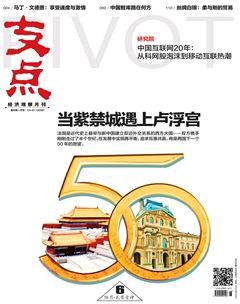加班禁令看上去很美
宋金波(媒体人)
前段一则来自海外媒体的消息称,法国新劳动法规定,晚上6点后到早上9点之前的非正常工作时间,公司将不允许向员工发送邮件,也不可以向员工打电话。
虽然这则消息引起的热议很快被法国以辟谣的形式降温——这不过是一个民间团体搞出来的、基本上不具备法律效力的东西。
但谁在乎准确事实是怎样?国人多数是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看到法国连八小时以外都把老板闲不住的手管起来,“水深火热”的中国白领质疑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暂且假定在工作时间上,欧洲确实比我们“先进”,那么,我们可否赶超呢?“可否”,有两层意思。一是应该与否,接受与否;二是能不能落实。法律规则中的两个层面,一是初级规则,即在法律上会否接受某种观念,比如说,是否有必要对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做出上限或下限的规定。二是次级规则,就是初级规则怎么落实,比如,如何认定过劳死?何种情况下业余时间可以被“征用”?
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关于政府对劳动时间的介入争论已久。后者似乎更占优势,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都规定了劳动时间上限,并对加班行为做出限制。
但很多人未必了解,中国法律关于劳动时间的初级规则,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如规定每天加班不超过l小时,还规定了较高的加班工资。而美国法律中除规定每周标准工作时间为40小时外,对加班时间的上限没有硬性规定。
但这是否减少了加班行为呢?大量研究都证明,很难。甚至在多因素综合作用下,高标准的初级规则,实质上鼓励了加班行为,特别是一线劳动工人。这种鼓励既对一些工人起作用,使他们“自愿加班”,也对雇主起作用,使他们倾向于迎合工人的加班意愿。高标准规则被双方广泛违犯,结果只能是法不责众。国内讨论加班问题,总要求严刑峻法,提高违法代价,未免过于简单化。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简单归纳,主要包括:次级规则的疏漏缺乏,这一点可以向因“过劳死”而闻名的日本学习;对工人基本工资包括加班基准工资的随意更改权在企业手中;工会角色与西方的差异使工人劳动议价能力不强;劳动者社会保障缺失导致的劳动焦虑与强迫倾向。
显然,这些原因并非都能一鼓作气解决。
其实欧洲的劳动时间问题,也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法国与北欧就不同,南欧与西欧又两样。如法国的政策,是用高税收迫使该退的退,以保证就业率,但这一点被证明效果不好。2008年之后,对于劳动时间与国民经济总体效率的相关性,也有争论,正反例证都有。顺带说一句,中国经济落后必需“加班”的结论也说服力不强。
总的来说,欧洲普遍是法律劳动时间不长(法国是每周35小时加大量假日,南欧假日更多),但实际劳动时间不短。休息时间很长,但休息质量变低。这和现代工作形式变化是有关系的。
北欧国家如瑞典,尝试 “部分工作时间”,类似灵活劳动制的用工形式,且用法律保障不同用工身份的转换。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可能“赶超欧洲”的一种可能。现代通讯联络技术使“部分劳动时间”可能性加大,大数据应用也可以使不同工种对加班做出不同选择不再那么难。中国劳动者多样性巨大,至少一部分人可以先尝试起来。
说到底,顺应社会发展,利用现代科技,减少高标准“一刀切”规定,使不同行业、工种乃至地域的人有可能通过局部博弈,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方式,将是国人可能赶超欧洲的弯道上可以见到的共同未来。(支点杂志2014年6月刊)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