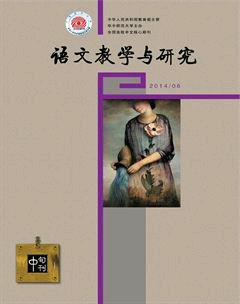评说《荆轲刺秦王》
《荆轲刺秦王》收入《战国策》,充分表现刘向的“史识”,其中诸多的悲喜因素,令人玩索不尽。我这里仅作笑谈。
一是燕主无雄才大略,外交才能平庸,朝中无人。想当年,燕昭王有乐毅的辅佐,各国诸侯乃至周天子谁敢小觑。“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这不只是说“丹”智谋有限,决策失误,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燕国当时朝中无人。既没有燕昭王那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又没有乐毅那样深谙“行军用兵之道”的将帅,下而“以荆卿为计”。其实,君主不必是集治政、治军之才于一身的大材,但首先能像刘邦一样“将将”,且不说是否有将可将,至少,你应该有让手下将帅放手用兵的耐性和胸怀。《开国大典》中,巴大维曾对蒋说:“贵军作战,部队推进到哪里,蒋先生可以迅速飞抵前线指挥所,直接参与指挥,而毛泽东不行,他只能在后方听前线的汇报。”这也正是燕太子的致命弱点——没耐性,急于求成。“日以尽矣……丹请先遣秦武阳”,他急了,坐不住了;“太子迟之,疑其有改悔”“荆卿岂无意哉”,他不信任荆轲。“成大事功”虽非都是“秤心斗胆”者,起码是稳沉持重、胸襟开阔者,而燕太子不是。燕太子“善养士”“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而对荆卿的武学造诣一概不知,无知人之明。何况,找遍燕国,仅得一个秦武阳,那是人才匮乏。连一把匕首还需进口,何谈军工。所以燕太子主燕,“刺客不行”也必败。
二是秦王虚有其名,既无远见卓识,又无宽广胸怀,贪得无厌,利令智昏。千古政要,短见重利者必败。自秦孝公至始皇,“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蒙故业,因遗策”,南取北收,追亡逐北,统一天下乃必然之趋势,又何败之有呢?一则秦王志大识浅,器量狭小。“督亢”虽乃燕国的一块肥沃的土地,却只易、霸之一隅,为弹丸之地而亲见来使,且未见国书,而轻信蒙嘉,有失缜密;武阳“色变振恐”于前,秦王不疑,荆轲把袖持刀“揕之”而不能脱,“剑长”而“不可立拔”,根本没有“万世”之君的那种镇定、从容与威严,统一天下只是因六国诸侯失策而侥幸得之,实非旷世贤主。二则用人不察。有蒙嘉这样贪图小利者立于朝中,再有赵高等祸乱朝纲,祸国败家只在早晚。三则面对三寸的“匕首”,武功低劣的荆轲,而“群臣惊愕”“尽失其度”,满朝文武,竟无一个处变不惊,胆识、器量过人的佼佼者,秦国纵然统一了全国,又能保持多久呢?“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不过是“白日梦”了。若非一个保健医生“夏无且”为之解围,江山易主,群小自散,何来“刘项引颈”观其东巡?拉倒吧。
三是荆轲武功低劣,感情用事,自负轻敌,此乃办事之大忌。荆轲没有看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不懂得独力难以挽狂澜于即至之理。人说“良将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其所事之主如上所说,非贤明之君,却要凭一己之力挟秦立盟,逞匹夫之勇,无异于螳臂当车,蚍蜉撼树。其次荆轲无自知之明,既无毛遂那样抵百万雄师的三寸之舌,更没商纣托梁换柱,张飞“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的上乘武功,“惜哉剑术疏”。连幽居深宫,胆小,见刀而惊恐,力怯智短,“剑坚”而“不可立拔”的秦王都不能制服。刀利,却“提秦王”而“不中”;体健,仅能与秦王“还柱而走”,而不能挡住“药囊”;力怯,只可与秦王“以手共搏之”罢了。至于“倚柱而笑,箕踞以骂”,三岁孩童也常作此状,不足道哉!第三,荆轲没有得力的助手。秦武阳12岁杀人,可谓“初生牛犊不畏虎”,“色变振恐”,足见不能“称向时之闻”了。更何况秦王与荆轲“还柱”“手搏”时,不知武阳已吓成什么样子,读者自去想象。燕人平原,一生志在报秦,是“荆轲有所待”者,何故没到?个中原因,我们也不难猜测。可以说,此人未出,其智已在荆轲之上了。行刺至少也应该有一样像样的兵器吧。冷兵器时代,长一分,则多一分胜算。求之于国外,“取之百金”“淬之以药”,试之于人,“无不立死”的“利匕首”,实不如周杰伦的“三截棍”好使。还是朱熹说得好,“轲匹夫之勇,其事不足言”。
可以说,国内没有能谋善断的主子制定周密的行动计划,外交上也没有相应的配合措施,身旁没有胆大心细、机智灵活、勇武善战的帮手来使唤,手中又没有一个称手的家伙,自身又没有一招置人于死地的武功,失败是必然的。“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正是也。
当然,国家多事之秋,荆轲只身赴秦,其不畏强暴,不避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品质是可贵的,正体现了历史上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美。其人格精神实乃历史天空中的一颗璀璨明星,是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时,激励华夏儿女奋斗不已的精神动力。
陈兆刚,教师,现居湖北房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