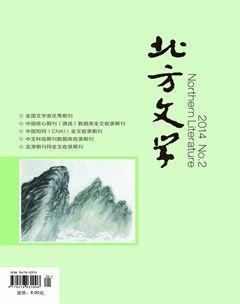家庭中的沉默者
摘 要:眷村第二代所掀起的眷村文学思潮对眷村生活进行了书写,刻画了眷村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形象。但是,相对作品中的父亲形象,母亲形象很少出现,即使出现,也没有多少话语或者说话的权力,传统思想、眷村的现实环境和眷村第二代的创作动机等因素决定了母亲的沉默,造成了眷村母亲的失语。
关键词:眷村;第一代;母亲;失语者
七十年代末出现,八九十年代形成创作潮流的眷村文学由眷村第二代掀起,多以追忆和写实的形式书写了竹篱笆内的生活,刻画了眷村第一代与第二代人的悲欢离合。在对第一代的书写当中,作家书写了家庭中顽劣的青少年与父亲的争吵,或者女孩儿与父亲的浓浓的父女情或女儿对于父亲的怨恨。但是在作品中,母亲或者出场次数少而时间短暂,或者逃离眷村,成为了家庭的缺席者,或者由于精神上的原因,远离了正常人的生活……总之,母亲形象在作品中要么选择了沉默,要么失去说话的权利,成为了眷村小说中的沉默者。
眷村的生活简单而平淡,父亲忙于工作或常年不在家,母亲负责家庭的日常生活,大多数母亲“操心的事都是家用啦、孩子功课啦、丈夫前途啦、明天菜价啦……”[1],整日算计的是如何用微薄的薪水支撑孩子众多的家庭等琐碎的家庭事务。这就使母亲形象显得比较“大众化”,性格不够鲜明,很难给青少年时期的作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也难以引起作家的写作兴趣。同时,很多母亲自觉遵守传统妇道,不多说话,使得很多母亲成为了“在场的沉默者”。在眷村小说中,涉及家庭生活书写的作品有《老爸关云短》、《写不成的书序》、《孽子》、《将军碑》等,这些作品多以父亲与第二代为主要人物,表现父亲与儿女的亲情或情感冲突,而以母亲为主要形象的作品较少。在描写家庭生活的作品中,母亲的出现的次数比较少,说话也不多,就像《沧桑》当中的卢太太,当干儿子大潭告诉她自己的姐姐与妈妈不愿见面的时候,她只重复一句“这不好”,不愿多评论别人的家务事。在故事结尾,旧时的感情全部回来,面对杨青情感失控的哭诉,内心翻江倒海,但只一句“杨青,话怎么这么说……”[2]。《小毕的故事》中,毕妈妈每日都安静忙家务事,从不东家长李家短,两家人中秋赏月,她也是少说少吃,为大家剥柚子、扇蚊子。在一些家庭中,也有些母亲迫于父亲的权威,没有多少发言的权利,就像《将军碑》中的将军夫人,儿子被将军罚练习敬礼,她只能在一旁默默陪着流泪,终于知道父亲的下落,欣喜地告诉将军,却遭到将军的痛斥,最后服药自杀。
相对这些安分守己的母亲,还有些母亲不满意清贫的生活,或者不满于感情上的平淡,过起了别样的生活。就像《沧桑》中的杨青,只是因为不甘心:没有人使唤、生活单调、乏味,而自己依然很漂亮,于是就与别人偷情,最终导致了夫妻情感的破裂,与女儿反目。还有《想我眷村的弟兄们》中,毛头的妈妈或许是耐不住没有男人的生活,或许是甘于做别人的情妇,经常留一个“神秘”的中年男子吃晚饭、过夜,导致邻居对她的疏远。但后果远远不仅如此:杨青的不安分,又加上偷情事发,受到村人的非议,即使十几年后在眷村重新出现,姚太太一类的流言传播者依然不放过她。在流言和现实的作用下,她成了传说中的坏女人。她没有解释、辩白和忏悔的机会,丈夫不欢迎她的到来,二女儿面对她就像陌生人,大女儿对她更是恨之入骨,无论如何不愿与她相见。毛头妈妈的作为被邻居指指点点,大家认为她不是什么光彩的人,打牌都不愿约她。受此影响,女儿一心想逃离家庭。眷村的消息传播很快,一家发生的事,很快整个村都能知道,很快就成了人们饭后的谈资。在人们的传播中,这类不安分的母亲经过加工,变成了眷村的负面形象,受到村人的唾弃,丧失了辩白的机会。所以,这类母亲遭到了眷村人的反感,难以受到眷村人的尊重,在家庭中也因自己行为的“不端”而得不到家人的认可,所以她们在实质上被剥夺了话语权,失去了语言的影响力。
眷村本省就是一个奇异的地方:居住的军眷来自大陆各地,几百人的村子,各色的人……很多孩子还会有这样的妈妈:对周围的事情漠不关心,也不在乎时间的流逝;有些则疯疯癫癫,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就像《旧爱》中程典青的母亲,得了“环境失调症”,不常出去,整天坐在家里,不做任何事情,也听不到村里关于女儿的风言风语。父亲看到有男孩送女儿回家而询问女儿时,她不仅不过问,还打断丈夫的话,让大家保持安静,不要吵。典青班里要去郊游,她希望母亲能有所理会,起码有一点点,但是母亲并没有。她准备离家出走的时候事实上渴望能够被父母发现,引来惩罚,这似乎也是一种关心,但在另外房间的母亲压根就没觉察到她的一切行为。安静的母亲仿佛停滞在另外的一个世界,现实的事情与时间的流逝仿佛与她无关。这种冷漠和安静充满了家里的每个角落,使女儿窒息。还有《伊甸不再》中的甄妈妈,因为太爱甄爸爸而精神恍惚,整天跟丈夫吵闹,不管家里的生活,骂邻居之后被丈夫毒打,整日变得昏昏沉沉,年幼的女儿不得不从小就撑起了家庭的重担。这种母亲或者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不参与现实生活,或者精神恍惚,脱离了正常人的世界,也成为了“在场的缺席者”。
苏伟贞曾经说过,眷村里“总有妈妈跑掉而不是经过离婚摆脱村子(或者说逃离这种生活)。”[3]就像《孽子》当中阿青的母亲,嫁给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男人,生活在类似贫民窟的地方,每天拼命地洗衣服赚钱,终于受不了这种生活,与人私奔。而《离开同方》中,丈夫常年驻守外岛的李妈妈受人诱骗,生下孩子之后就消失了踪影,留下两个孩子。这些母亲逃离了眷村,剩下年幼的孩子和沉默寡言的丈夫相依为命,家庭中不复存在母亲这样一个角色。眷村家庭的一种奇特现象就是老夫少妻,国民党从大陆仓皇撤退,很多军眷留在了大陆。在反攻大陆还有希望的日子里,许多军人没有在台湾成家,直到反攻无望后,才成立家庭,但这时候他们都已经是四十多岁,就娶了一个足可以当自己女儿的本省女子,就像《小毕的故事》中,小毕的父母一样。夫妻间年龄的差距,生活的贫苦与绝望,使很多女人受不了而逃走,就像《四喜忧国》中四喜的妻子一样,经常逃回娘家,四喜只好把她剃光了半边头,让她怀孕,才留住她。所以,很多眷村家庭是不稳固的,母亲这一角色很可能会消失,就像《孽子》中,母亲消失之后,家里只有阿青兄弟和父亲生活:《沧桑》中,杨青离开之后,包家的孩子只能自力更生,大姐做有妇之夫的情人接济家人。
还有些写家庭生活的眷村小说中,母亲从开始便处于缺席状态,就像《消失的球》中,“我”从小便没了娘,是由父亲抚养长大,家庭成员只有爷爷、父亲和我三个人,有关家庭的书写也一直集中在父子之间;《想我眷村的弟兄们》中,英英的母亲没有出现,英英离家多年后重新出现,与父亲发生分歧,争吵后父女关系破裂。眷村小说在书写家庭生活的时候,很多涉及到父子、父女两代的冲突,对父亲这一形象有思考,这不能不说是由于“文学作品常是厚母亲薄父亲的”[4],正是文学中的厚母薄父,导致了了对父亲的反复书写,减少了写母亲的笔墨。
眷村文学是掌握了话语权的眷村第二代在眷村即将消失的时候,对自己早年成长时光的的追忆,也是成长地即将失去而引发的无根的焦灼感的一种宣泄,更是对于自身身份定位的一次追问。在作品中,对于父亲的书写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己外省人这一特殊族群身世的追问与思考。而在第二代眷村人的笔下,眷村的母亲,或者忙于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或者在父亲的权威面前没有发话的权利,或者远离常人的生活,仿佛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或者逃离眷村,逃离这种生活,她们大多是沉默的,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也是,在作品中也是。
参考文献:
[1]苏伟贞:《老爸关云短》,《魔术时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
[2]袁琼琼:《沧桑》,《台湾眷村小说选》,台北:二鱼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86页
[3]苏伟贞:《眷村的尽头》,《台湾眷村小说选》,台北:二鱼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8页。
[4]张大春:《权威与挫败》,《张大春的文学意见》,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71页。
作者简介:隋双双,现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endprint
——以《台北人》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