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在内心的灯盏
布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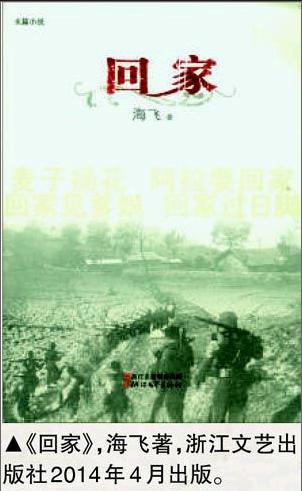
小说家海飞用了二十万文字,构筑了一条七十多年前的回故乡之路,漫长而曲折,崎岖而险峻,源自于遥远的远方,通往遥远的家乡……回家的道路上,行进着各色人等,有国军逃兵、新四军金绍支队伤兵、日本入侵者、日本俘虏、皇协军、汉奸、土匪、离井背乡的普通男人与女人等等。还有日军战死者的骨灰坛子。多支队伍并排行进在回家的路上,义无反顾,朝前走着。此起彼伏地上演着一幕幕悲壮、激烈、艰苦卓绝、苦难,甚至无耻、卑劣的人间活剧。
文字构筑的画面中,炸弹在虎扑岭汹涌炸开,弹片四射,泥石横飞。时值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或四十年代上半叶,国军和新四军联合在此伏击一支日本联队,战斗异常激烈。小说就此展开,各色人等相继进入指定位置。
国军十五岁的小号兵蝈蝈,啃着冰冷的地瓜,蜷缩在战壕里抬头望天,心中想着一座叫临安的县城。临安是蝈蝈的老家,一座特别江南的县城,“蝈蝈特别盼望能回家上山打核桃。”随着蝈蝈的视角,《回家》的各色人等依次登场。
真正的主角是新四军老兵陈岭北,进入阵地前刚从禁闭室出来。禁闭期限尚未满,还差三天,因为要打仗了所以把他放出让他参战。禁闭的原因是:吵着要回家娶含辛茹苦独立支撑着陈家的寡嫂。走出禁闭室时,连长拍着陈岭北的肩头,说,其实我也想回家。
关于“回家”的铺垫指向明确且气场很足,情绪的营造也非常到位。国军和新四军的伤兵、逃兵在一场战后如破棉絮般被击溃,最后集体走上了回家之路。在雪雨连绵的江南冬春,家是亮在每个人内心的灯盏……
选择让老鼠山上的土匪麻三带队打扫伏击战场,是海飞在长篇小说构架中谋篇布局游刃有余的最明显体现。土匪军师陈欢庆,从日本少尉遗体的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信,是少尉写给在日本的妻子美枝子的,信写得简单,说美枝子我会尽快地回来的,你得养好咱们的孩子。妻子和女儿,我常想起故乡的山川河流……妻子给我那个保命符,我一直珍藏。我愿意回家……
军师读完信后,所有土匪都没有说话。陈欢庆目光低垂,他说了一句声音很轻却非常深刻的话:这个混蛋也有老婆和女儿,也有家,他说他想回家。
随着海飞绵密而潮湿的文字一路往前走去,回家的涵义在海飞笔下变得深远而阔大起来,并渐渐上升到家园、家国,甚至精神的层面。
陈岭北在小说的开头因战事将临而提前走出禁闭室时,与连长有过一番对话:连长冷着脸说,你真想回家?陈岭北说,我不信你就不想回家。连长说,日本人不走,我不回家。一天不走,一天不回家。一年不走,一年不回家。一辈子不走,一辈子不回家。
后来,有了一场伤兵陈岭北指挥的,一批下级兵士们参战的“四明山战事”。这是一支东拼西凑的部队,战前陈岭北大声嘶吼,想回家的,赶紧把鬼子和汉奸给赶尽杀绝。
再后来,陈岭北带着大家继续往北走着,路过了自己的家乡丹桂房。没有想到的是丹桂房也被日本兵洗劫了,家园像洪灾过后般尽毁,陈岭北心里一直想娶的寡嫂棉花也死了,整个村庄被掏空。那些从未上升到“国家”高度一心只想回家的士兵们,没有一个选择回家。这是海飞特意构建的凡夫俗子的精神世界,如此亲切,如此真实地生活在茂盛的文字中。在长久的沉默以后,他们血肉模糊地抱紧自己手中的枪,所有人选择一路向北,北面不远处的江苏,是新四军的驻地。
家国以及精神意味由此而更加浓烈……十分自然,如此真实。
回家阵容无比浩大,包括日本军官送日本战死将士的骨灰回家。
陈岭北为首的国共两军伤兵,联合伏击了运送日本阵亡者骨灰的车队。伏击者们发现了车上“排列整齐的骨灰坛”,于是举起了手中的武器。“随即有几个陶罐碎了,骨灰飞扬起来,洒了一脸。”他们的嘴上吼着,这些骨灰,全要扔进茅坑,全扔掉。一起参与伏击的日本战俘香河正男见状大喊:“不许对骨灰不敬,不许对骨灰不敬。”陈岭北见状上前,阻止了战士们的行为,低声嘶吼:“死者为大。人家都已经死了,你要是敢再动骨灰坛子,我让你成为骨灰。”
让我们回归母题。路在脚下,隆冬已过,冰封的大地已经开始松动温润起来,战乱中的家园即便满目苍痍,但草长莺飞还是如期而至。故乡在前方,以灯盏的形象在一闪一闪亮着,亮在每个人赶路回家的人的内心深处,尽管遥远,却永不熄灭……
在《回家》中,海飞通过一位法国传教士杜仲之口,说出了作家普世的文学精神:“爱你的家,爱你的父母儿女,爱你的仇人,爱你身边一切的事物,爱云朵、大地、稻谷,以及所有的事物,爱这个世界……让耶莫里娜的光,穿透黑暗。我要回法国了,我要回我的安纳西。”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