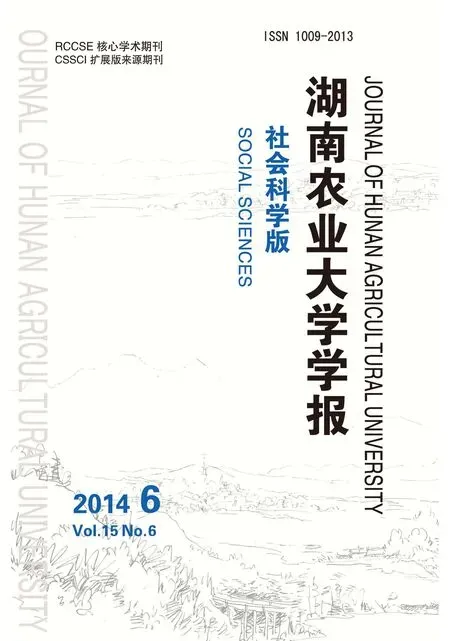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10个城市1 021份问卷调查数据
吴伟东
(暨南大学人文学院,广东 珠海 519070)
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10个城市1 021份问卷调查数据
吴伟东
(暨南大学人文学院,广东 珠海 519070)
基于厦门、天津和深圳等10个城市的1 021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水平较低,在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实际参加”占比分别只有 13.4%和 7.7%。进一步运用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企业民主参与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务工企业的规模、岗位类别、单位工龄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影响显著。年龄较小或者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机会受到限制。在中等规模的企业内务工、从事生产和服务类岗位、单位工龄较短或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企业民主参与的程度相对较低。来源地、性别、企业所有制、行业类别和工作更换次数等变量影响不显著。
农民工;企业;民主参与;影响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民主参与是现代民主体制的核心内涵,每一种模式的民主体制,都把其成员的民主参与置于核心的位置[1]。在中国,伴随城镇化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进程,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地区居住和就业的人口规模正逐步扩大。2013年农民工的人口已达 2.6894亿[2]。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范畴是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迫切需要,也是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客观发展趋势[3]。
企业民主管理是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而衡量其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于职工的民主参与。全国总工会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必须保障农民工的民主政治权利,逐步提高农民工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4]。
目前,有关职工企业民主参与的研究日趋深入。赵丽江等[5]指出,中国处于经济体制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关系重组、利益格局变化的特殊时期,在劳动者面临诸多困境的情况下,传统意识形态所坚持的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空心化,造成民主管理和职工合法权利的缺失,必须重新探讨职工民主参与的路径,强化职工的民主参与。陈昌举等[6]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职工民主参与制度日渐式微,必须在新形势下重新厘清职工民主参与的基本内涵和分析职工民主参与的法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重构职工民主参与制度。詹婧[7]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探讨了职工的企业民主参与的参与层次和动力因素。然而,专门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实证研究在现阶段仍处于空白,尚无法给这方面的政策实践提供有针对性的科学指引。为此,笔者拟基于厦门、天津和深圳等 10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及其影响因素,为改进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提供经验支持。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企业民主参与的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将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划分为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进行探讨。其中,个体层面聚焦的是个体之间的直接接触和沟通。薄岛郁夫指出,除了投票、选举活动之外,个别接触也是个体民主参与的途径之一[8]。通过与企业管理人员或者职工代表的直接接触和沟通,农民工表达自身的权益诉求,提出企业发展和完善的建议。在本研究中,将“提出合理化建议”作为农民工个体层面的企业民主参与。在调查问卷中的问题设置是“你是否给企业提出过合理化建议”,备选答案是“没有”和“有”。
同时,依据 2012年发布的《企业民主管理规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基本形式,企业应当尊重和保障职工依法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民主权利,支持职工参加企业管理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保险福利、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职工代表大会是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核心途径,职工代表拥有与企业在上述议题上平等协商的法定权利。因此,集体层面聚焦的是参加职工代表大会。能够被选举为职工代表、参加职工代表大会,农民工将能够在集体的层次进行民主参与,对企业的决策制定和发展施加影响。在调查问卷中,集体层面参与的对应问题是“你是否参加过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备选答案是“没有参加过”和“参加过”。
为了明确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的影响因素,运用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Logistic回归模型因变量分别为“是否给企业提出过合理化建议”和“是否参加过职工代表大会”,均为二分变量,适用于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在此基础上,两个模型中所纳入的自变量是一致的,包括农民工的来源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务工的企业规模、行业类别、所有制性质、岗位类别、单位工龄、工作更换次数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等(表1)。

表1 农民工样本的基本特征
数据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的“劳动者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库。此次问卷调查在厦门、天津、深圳、上海、南京、长沙、成都、温州、绵阳和长春等 10个城市展开。调查共发放问卷2 000份,获得有效问卷1 813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约为90.7%。其中来自农民工群体的有效问卷1 021份。调查样本中农民工群体的基本特征见表1。
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在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实际参加”占比分别只有 13.4%和 7.7%。同时,对比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意愿与实际参与情况的数据结果可以发现,大部分(64.5%和 59%)农民工具有企业民主参与的主观意愿,但最后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成功地实现民主参与。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意愿与实际参与情况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由此看来,客观的现实情况和企业环境,比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意愿更加重要。即使农民工拥有较高的企业民主参与意愿,但在外部环境支持不足或者存在阻碍因素的情况下,他们的企业民主参与仍然难以得到实现。
三、实证研究及其结果
运用SPSS 21.0对调查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见表 2。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回归方程中各个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通过检验,模型中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代表其对因变量的单独影响。
(1)个体方面的变量中,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效应都局限在特定层次上。其中,年龄变量对集体层面民主参与的影响为正,且通过 10%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26-35岁的农民工与 16-25岁的农民工相比,参加职工代表大会的可能性大幅度提高。换言之,处于16-25岁年龄段的青年农民工,集体层面的企业民主参与机会是较少的。而 35岁以上的农民工,参加职工代表大会的可能性比 16-25岁的农民工更高,同时低于 26-35岁的农民工,但其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受教育程度变量对个体层面民主参与的影响为正,且通过了 5%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比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工更多地向企业提出合理化建议,对个体层面的民主参与存在显著影响。高中学历的农民工,提出合理化建议的可能性与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工要略微降低,但其回归结果并不显著。民主政治权利的有效运用,需要个体对政治问题持有一定的兴趣,了解政治过程和议题,并且具备一定的能力去表达观点和自身的诉求[9]。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民工,很可能因为自身学历和认知因素的限制,阻碍了他们的企业民主参与。

表2 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Logistic回归模型
(2)企业环境方面的变量中,301至1 000人的企业规模对两种层面的农民工民主参与的影响均为负,且通过10%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而1 000人以上的企业规模对个体层面的民主参与的影响为正,且通过了 5%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与在 300人以下的企业内务工的农民工相比,在301至 1 000人规模的企业内务工的农民工,向企业提出合理化建议和参加职工代表大会的发生比率都明显下降,分别只有前者的41.7%和34.6%。在1 000人以上的企业中,农民工提出合理化建议的可能性与 300人以下的企业相比有所提升。这可能反映出企业管理的规范程度对农民工诉求表达的促进作用。总的来看,企业规模的扩大对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的抑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集体层面的企业民主参与,由于职工代表大会的人数比例问题,企业规模扩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往往是难以避免的。但同时,个体层面的企业民主参与,同样在301至1 000人的企业规模中显著下降,则很可能反映出这一规模的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存在参与途经缺乏、渠道不畅等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农民工的建议和诉求表达,导致他们无法实现个体层面的企业民主参与。农民的自我组织能力,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社会方面都比较低[10]。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也会同样存在这一问题。
(3)岗位类别变量对两种层面的民主参与的影响为负,且通过 5%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管理类岗位的农民工,在两种层面的民主参与的实现上,都要明显优于生产和服务岗位的农民工,后者在这两种层面上的发生比率均不到前者的30%,而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在职工代表大会的参与上只有前者的12.8%。对于较高层次即集体层面的民主参与,就职于行政事务、技术研发以及生产、服务类岗位的农民工,实现个体层面的民主参与的发生比率依次是管理类岗位的46.9%、 35.5%和 25.8%。这可能反映出行政事务类等岗位由于岗位的特点,较为容易实现个体层面的民主参与,但要实现集体层面的民主参与,则更多地受到岗位重要性的影响。一般而言,管理类、技术研发和生产、服务类岗位对于企业管理的重要性依次下降,在这些岗位工作的农民工的民主参与可能性也随之减少。就现行规定而已,《企业民主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企业领导人员和其他方面的职工组成,其中,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和领导人员一般不得超过职工代表总人数的20%。可以发现,现行的政策规定对职工代表的职务类别有特定要求,对管理人员的比例有所限制,务求确保职工代表的代表性。但从本次研究的结果来看,管理类岗位的农民工参加职工代表大会的发生比率,仍然明显高于非管理类岗位的农民工。这表明工作岗位对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的阻碍效应,生产、服务类岗位的农民工民主参与的机会仍然受到限制。
(4)劳动合同签订变量对两种层次的民主参与影响为正,且通过了 5%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分别多了32.3%和23.3%的机会去实现企业民主参与。而且,从上述发生比率来看,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是累加的:相对于个体层面的民主参与,劳动合同签订对于集体层面的民主参与所起的促进作用更大。对于个体层面的民主参与而言,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可能由于劳动关系的不确定性,缺乏动力去思考和提出合理化建议。而集体层面的民主参与,则可能由于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设置,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排斥在代表选举的范围之外。同时,单位工龄对个体层面的民主参与的影响为正,且通过了5%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只有5年及以内工龄的农民工,与拥有 10年以上单位工龄的农民工与相比,更少地向企业提出合理化建议,同时也少于 6-10年工龄的农民工。职工代表大会的参与尽管与单位工龄不存在显著相关,但在关系方向上是正向的:10年以上和 6-10年单位工龄的农民工,比 5年及以内工龄的农民工存在更高的可能性。这些数据结果也反映出劳动关系对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的重要性。规范和长期的劳动关系,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而非正式和短期的劳动关系,则会阻碍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
此外,来源地、性别、企业所有制、行业类别和工作更换次数等变量对农民工两种层面的企业民主参与都不存在显著影响。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目前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与他们的参与意愿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从农民工自身方面阻碍了他们的企业民主参与,年龄较小或者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机会受到限制;企业规模、岗位类别、单位工龄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对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影响显著,在301至1 000人规模的企业内务工、从事生产和服务类岗位、单位工龄较短或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在企业民主参与上受到限制。
总体而言,外部环境对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目前仍缺乏足够的支持。外来移民民主参与的形式和运用这些形式的程度,极大地受到某一具体框架下特定的制度性安排的影响[11]。制度设置的不合理或者无法得到有效落实,都将会严重地阻碍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因此,现阶段尽快通过对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完善,以及对农民工群体的支持,促进他们的企业民主参与。依据本次研究的结果,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方面的重点措施在目前应当包括: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积极拓展农民工民主参与的途径,并保证农民工参加职工代表大会的人员比例,确保农民工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同样能够获得足够的民主参与机会;推进《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并推动劳动关系的长期化发展。此外,通过继续教育提升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能力,也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
[1] Eggert N. and Giugni M . Does Associational Involvement Spur Political Integration? Political Interest and Participation of Three Immigrant Groups in Zurich.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6,(2):175–210,2010.
[2]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f ortune/2014-02/24/c_119477349.htm,2014.
[3] 邓秀华.长沙、广州两市农民工政治参与问卷调查分析[J].政治学研究,2009(2):83-94.
[4]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N].工人日报,2010-06-21.
[5] 赵丽江,张远凤.论发展工作场所的民主参与[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6):63-67.
[6] 陈昌举,王添翼.职工民主参与制度:目标·依据·模式[J].宁夏社会科学,2011(6):13-21.
[7] 詹婧.企业民主参与动力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
[8] 薄岛郁夫.政治参与[M].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
[9] Martiniello,M.Political Participation,Mobilis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Immigrants and Their Offspring in Europe.Willy Brandt Series of Working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thnic Relations,1/05. Malmö University,2005.
[10] 彭大鹏.让基层民主有力地运转起来——对成都新村发展议事会的考察[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18-122.
[11] Odmalm,P.Migration Polici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Inclusion or Intrusion in Western Europe[M].Palgrave Macmillan,2006.
责任编辑:陈向科
Migrant workers’ employee particip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a survey of 1 021 migrant workers from 10 cities
WU Wei-d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Jinan University, Zhuhai 519070, China)
The data from a survey conducted in Xiamen and other nine cities indicate that the employee particip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quite low. The individual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s just 13.4%, while the collective level is 7.7%. The analysis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finds that migrant workers’ age, education level, the size of enterprise they work for, posts, length of service and whether they sign labor contract or not all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is participation. Those younger or with lower education level have less opportunities in employee participation. Besides, those working for medium-side enterprises, or in the post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with shorter length of service or without labor contract, also participate less. At the same time, birth place, gender, enterprise ownership, industry category and employment history don'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is participation.
migrant workers; employee participation; influencing factor
C913
A
1009-2013(2014)06-0065-05
10.13331/j.cnki.jhau(ss).2014.06.012
2014-10-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ASH00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840053)
吴伟东(1979—),男,广东珠海人,南开大学—伯明翰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流动人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