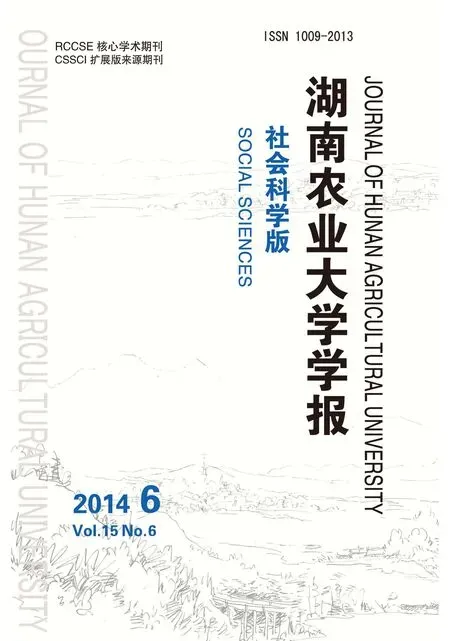价值迷失与农村老人自杀
——基于湖北京山J村的个案研究
刘锐,杨华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价值迷失与农村老人自杀
——基于湖北京山J村的个案研究
刘锐,杨华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农村老人自杀与结构转型、价值迷失有关,其诱因包括为子代着想、家庭矛盾、孤独无力、疾病困扰等。农村老人自杀的背后是农民价值系统的作用。农民价值可分为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主体性价值。本体性价值是基础,社会性价值是重要补充,它们统一于伦理性的“过日子”实践中,共同受村庄文化网络规范。主体性价值是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丧失后的伴生物,与现代性进村密切相关。家庭生活伦理性的丧失、村庄生活规范性的弱化造成农村老人本体性价值的坍塌、社会性价值的丧失和主体性价值的被迫选择,使其价值安放出现混乱,自杀成为归宿。
价值迷失;农村老人自杀;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主体性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国内外关于人类自杀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基本视角展开:
一是公共卫生学视角。弗洛伊德[1]提出“死亡本能”观念,认为人除了具有求生动力机制外,还有求死的动力机制。精神病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2]认为,自杀是克服生命感和死亡感,对他人进行报复的方法。精神病医生施奈得曼[3]认为,自杀者常常犯三段论错误,我(主)去自杀,我(宾)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主)要自杀。后来,施奈得曼[4]又提出“情痛”概念解释自杀。公共卫生学的分析多局限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领域,背后是对个体生命及存在境况的西方式关注,对中国学者研究自杀很有启发。其不足在于它过多关注自杀与精神病间的关系,并偏重从个体主义视角思考人性与价值,没有真正进入自杀者的生活世界。实际上,自杀的具体原因非常复杂,众多自杀现象的出现表明自杀不仅仅是私人问题,还是公共问题[5]。自杀不仅受个体主观选择的影响,还受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二是结构论视角。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开创了自杀研究的社会学传统,他将自杀当作社会事实来理解,认为自杀的发生与社会失范有很大关联。家庭社会正好像宗教社会一样,对自杀具有极其强大的免疫力[6]。涂氏所讲的家庭社会对自杀率的抑制,实际指代际关系稳定对家庭成员自杀的预防功能。国内结构论视角的研究延续了涂氏的分析理路,如刘燕舞[7]认为,当前家庭结构纵向及横向的变动为老人自杀提供了重要条件。陈柏峰[8]认为,京山农村老人自杀率高得惊人是代际关系深刻变动的产物,它与村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有关联。结构论分析视角的不足在于它对老人自杀的社会原因,如代际失衡、家庭矛盾等因素的说明预设着家庭结构的变动。但 2000年以后的一些地区,农村家庭结构渐趋稳定,老年人自杀却不降反增,结构论分析对此着力不多,也难以解释清楚。且结构论视角在经验研究的层次上存在着某些难以证明的困难,许多经验研究很难证明结构论者所预想的理论假设[9]。在分析具体自杀案例时,结构论者很容易陷入个体主义进路的陷阱,使个体与整体,统计与经验对立起来,导致方法论的困境[10]。
三是文化论视角。正是基于对结构论视角的反思,道格拉斯[11]主张揭示每个具体自杀行动背后的文化意义,通过事后的深度访谈对自杀情境做出解释性理解。国内学者尝试着此种思路,如吴飞[12]以“过日子”概念分析中国农民自杀现象。他认为,家庭对每个人的生命有着根本的存在论意义,自杀是对家庭生活中所受委屈的反抗,是亲密关系与家庭政治间张力的直接反映。杨华[13]等认为,农民不信鬼神和祖先,对死后世界缺乏想象,对生命缺乏敬畏,地方性知识中认为老人“没用该死”的观念为老人自杀秩序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氛围和文化基础。何兆雄等[14]认为,一方面中国文化对孝道过分强调,使个体言行被高度道德化;另一方面,老年人无论在家庭生活还是在社会交往中普遍地被视为负担,文化悖论的张力对老人自杀影响巨大。文化论视角下的自杀研究深刻把握到社会文化和社会观念对个体自杀的影响,对于避免结构论视角的缺陷和不足,开创自杀研究的新范式意义重大。不过,文化论分析依靠经验的移情理解和高度的提炼能力,使得其阐述要么停留在道德变迁层面,要么深入到人性论和生命权利层面,对价值变迁与老人自杀间的内在联系缺少细致透彻的勾勒。
有鉴于此,笔者拟延续文化论的分析思路,从农民价值类型及其变迁的角度研究老人自杀问题。19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里,湖北京山J村家庭结构渐趋稳定,老人自杀却不见减少,代际关系变动只能解释“变迁”中的老人自杀,却不能解释自杀秩序形成的深层原因。本文试图说明:老人自觉自如的走向自杀,与其本体性价值的沦落、社会性价值的乏力、主体性价值的疲软有关系;老人自杀并非吴飞[15]所言的表达出一种美好价值,或者表达出一种错误观念,而是在生命意义的孤独感、无力感、绝望感交汇影响下的自主选择;农民价值变迁正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二、农村老人的自杀类型
J村属于丘陵地形,地处江汉平原末端,村庄历史不到三百年,传统宗族文化较弱,村庄社会边界开放,家庭灵活性强,村民原子化程度高,直到1949年前村庄规范尚未形成。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进驻及政治改造,198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冲击使J村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人际交往快速转型,村民很快接受了各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因结构转型和价值变迁带来的农民“自杀潮”在J村却并不明显。
对J村老人自杀进行全面描述离不开对自杀现象的分类,由于自杀问题的敏感性和访谈技术限制,对老人自杀的分类只能是粗线条的。从自杀者的主观动机、客观原因和事后效果来看,自杀并不是孤立发生的,很难用单一类型去定位。当农民讲述或解释老人自杀时,会谈到很多直接、间接原因,这一方面提醒访谈者农村情况很复杂,不要武断下结论,另一方面也为分类研究自杀提供可能,当然,分类的合理性来源于对村庄经验整体性把握。以下从自杀诱因角度将农村老人自杀分为4类:

表1 老人自杀诱因的类型(N=31)
将老人自杀分为 4类并非自杀诱因的全部类型,但出于研究需要,笔者只粗线条分类,以便于后续学术分析。另外,老人自杀并不简单由某一诱因引发,有时兼有两种以上的自杀诱因,笔者根据现场感受和被访者的描述选取主要自杀诱因进行统计。
限于被访人的社区记忆,老人自杀距今年限越长,回忆越吃力,很有可能漏掉。不过依然可以从表2至表5老人自杀年代的描述中发现,2000年以后老人的自杀变化并不明显。这也印证了前述J村农民自杀无高潮和低潮区别的判断。其次,从表 1看出,孤独无力和家庭矛盾诱发的老人自杀所占比重较大,其他两种诱发型自杀所占的比重较小。
1.为子代着想诱发的自杀

表2 为子代着想诱发的自杀(N=6)
为子代着想诱发的自杀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自己得大病,为了减轻儿子的经济负担,不拖累家庭经济的后腿,老人甘愿自杀。6号、26号属于这种情况。6号老婆婆,80多岁,儿子们在供给粮食上推脱,老人无法生活,但她并不嗔怪儿子,只是等儿子插完秧,都有闲暇时间时,洗个澡,换上衣服,写好灵位,点上蜡烛,然后喝药死亡。对于6号来说,儿子们不承担赡养责任并无大碍,要紧的是不能拖累儿子们的生活,哪怕自杀,也要让他们尽量省心。
第二种情况是老人传承下来的于子有利、于己不利的精神信仰。12号、13号属于这种情况。13号婆婆, 80多岁,跟大儿子过,大儿子60多岁,经常犯病,身体不好,老婆婆去医院检查出顽症,她放弃治疗,回家上吊死亡。该婆婆自杀主要是看到子代被疾病缠身,想到自己长寿是儿子短寿的原因,为给儿子留个好名声,让儿子多活几年,老人甘愿自杀。
第三种情况是父代对不能给予子代好生活而心生愧疚,心甘情愿地走向自杀。老人单纯以子代物质是否丰裕来衡量自己是否该安度晚年以及儿子是否应该好好孝敬自己。有了这种“指标性对等”的考虑,老人自觉将代际关系变成理性人的物质交易[16],用自己的观念意识捆绑自己,逼迫自己因内疚悔恨而自杀。17、28号属于这种情况。
2.家庭矛盾诱发的自杀

表3 家庭矛盾诱发的自杀(N=9)
家庭矛盾诱发的自杀也可称为“怄气型自杀”。老人与村民吵架很难自杀,受子代数落几句则想到自杀,不是老人气性大,主要是老人在乎与子代的关系交往。家庭矛盾诱发的自杀可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客观原因促成的老人自杀,1号、4号、9号、11号、19号都是老人因生病照顾问题与子代争执,愤而自杀。19号老太太,70多岁,有老伴,儿子儿媳都在外打工,老太太生病不能动,打电话给儿子,希望其照顾生活,儿子不情愿地回来,赡养不尽心,与老太太发生口角,儿子骂了老太太,老人气不过,喝药死亡。
第二种情况是老人因日常琐事与子代发生口角,感觉委屈而自杀。18号、20号、21号、30号老人属于这种情况。20号老太太,80多岁,有一回见儿子抓鳝鱼,就问儿子要几条吃,儿子不但不给,还骂老人好吃懒做,母子两人就吵起架来,儿子恶狠狠地说:“你咋不买药喝,又不是没有老鼠药”。老人一气之下,回家就上吊自杀了。
3.孤独无力诱发的自杀

表4 孤独无力诱发的自杀(N=9)
孤独无力诱发的自杀与疾病困扰诱发的自杀的不同在于,老人的情绪、活动与子代的生产、生活相关联,此类自杀可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子代出于工作、生活、家庭考虑,要求老人自杀,老人感觉无力无奈,但他并不反抗,而是因应子代要求,在恰当时间里自杀,5号、7号、8号、22号、23号、29号均是如此。23号老人,70多岁,有一次生病,打电话给在外打工的三个儿子,儿子们回家说,“我们只请了 7天假,假期一满,就要回去上班,你死也得死,不死也得死,不然,以后死在家里,没人管你了”。后来老人在规定时间内死掉,儿子们办理完老人丧事,然后匆忙回去上班。
第二种情况是单过生活很孤独,亲人不在身边,一旦丧失劳动能力,亲人照顾的缺失将使老人感觉生活乏味无聊,在心情惆怅中认可“老人能动就该动,不能动就该死,该死而不死是不会做老人,老人活得太长了不好”的村庄观念,走向自杀。14号、27号、31号属于此种情况。退休老师屈X,74岁,1996年退休,儿女都有固定工作,家境不错,他很是盼望儿女回家看他。他自嘲说,“现在每天就三件事:一是拿退休工资,二是等儿女回家,三是等着进火葬厂。”他有时觉得活着很没意思,不自觉会有自杀的想法。
4.疾病困扰诱发的自杀
疾病困扰诱发的自杀多是自利性考虑,因为病痛的厉害,好转较慢,索性终结生命,减轻身体折磨。10号老人不慎被拖拉机从身上轧过,导致下半身瘫痪。老人坚持不去医院,在家中绝食,十多天后去世。村民解释说,主要是老人知道,治疗要受疼痛折磨,死了还解脱些。民间俗语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孝经》也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J村老人并不如此认为,他们大多觉得因大病处理掉自己生命很正常很自然,并没有什么后悔。

表5 疾病困扰诱发的自杀(N=7)
三、农村老人自杀背后的价值系统
2000年以后,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渐趋完成,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逐渐稳定,延续已有的结构变迁视角去考察老人的自杀问题,必然会陷入分析偏颇,解释乏力的误区。贺雪峰[17]认为,2000年后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表现在三个层面:治理结构之变、基础结构之变,农民价值与意义系统之变。其中前两个变化已能初步评估,价值系统的变迁效果则有待深入分析。J村老人自杀的特点在于,老人自杀并没有额外目的——追求意义圆满或反抗子代不孝,自杀本身就是目的——解脱自己、结束无意义的生活。无论是为子代着想诱发的自杀,还是家庭矛盾诱发的自杀,或者孤独无力诱发的自杀,抑或是疾病困扰诱发的自杀,本质上都与老人价值混乱相关联。相较于集体化时代,J村老人的物质生活已大大改善。笔者在该村没有发现老人因没有饭吃、没有钱用、极度穷困、走投无路而自杀的情况。老人自杀多与其意义失衡、心灰意冷、孤苦无聊有关,他们的自觉自愿自杀并没有给J村带来任何改变,哪怕是村民的一丝道德震撼都没有,自杀成为私人事件。问题在于老人也是理性人,他们竟然不反抗,不反思,静悄悄地自杀,不带走一丝一毫。韦伯认为,“行动”是由包含着意义的行为组成,“社会行动”不仅包含行动者赋予的意义,还包括广泛的意义系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行为”必然要经过“价值理性化”的升华[18]。要考察农民理性自杀背后的价值作用,首先需梳理清楚农民的价值世界。
吴飞[12]认为,“过日子”是家庭生活的过程,个人生命在家庭中展开。家庭不仅是基本的社会单位,还是个体意义实现的场所。中国家庭并非西方意义上界限分明的团体,家的范围具有极大的弹性,从核心家庭向外扩展,最大可到达宗族或村庄[19]。正是日常“柴米油盐酱醋茶”式的家庭生活与抚育成长、成家立业、养老送终的家庭继替[20]活动构建起世俗生活中的文化伦理和个体价值系统。不少村庄的老人对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强烈追求及拜土地公、拜观音大士等“巫术”活动都是农民价值世界里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们或者在家庭生活中完成,或者渗透到家庭生活中去,家庭生活搭建起农民的价值基础。笔者借鉴贺雪峰[21]对农民价值系统的分类与论述,对其进行系统阐释和拓展性分析。
农民的家庭生活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家庭内部的事务活动,二是家庭与家庭间的交往,个体不仅生活在家庭中,也生活在村庄中,他主要依靠家庭和村庄两个“场域”生产价值系统,当然,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个体也能在村庄之外构建意义体系。家庭和村庄对农民的意义建构作用巨大却又有本质差异。笔者将农民价值分类三类: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主体性价值。本体性价值靠家庭生活维系,社会性价值在村庄中生产,主体性价值主要在村庄之外完成。
(1)家庭生活的核心是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个体在家庭内部形成他的人格,形成对自己在更大社会中地位的自我评价与解释[22],家庭生活生产出个体的本体性价值。家庭内部有两对基本关系要处理——夫妻关系与父子关系,家庭成员最关心的事情是家庭的延续,不仅仅是家庭财产的传递,还有生命的代代相续。对于家庭成员来说,生育儿子、传宗接代非人力所能改变,儿子被农民赋予更大的伦理意义。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在传宗接代中生发出来,父子一体、夫妻一体只有放在血脉延续中才能理解,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谓之农民的本位性价值。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于父代来说,抚育多个儿子尽管困难,身上的担子加重许多,但他们把养儿子当作事业来追求,累断筋骨也再所不惜。绝后不仅意味着家庭延续的终结,而且意味着祖先人格的死亡[23]。正是儿子蕴含的宗教般意义,使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被纳入伦理轨道。婚姻的目的不是浪漫爱情的归宿,而是接续祖先事业,生育儿子,善待财产,促成族群绵延不断。一对夫妻如果没有儿子,他们会羞愧于自己的无能,无法向祖先交待,在村庄中抬不起头,人生也将因此灰暗许多。无论是对祖先的精神寄托,还是对儿子的价值期待,都要在家庭生活中展.,正是家族文化的浸染和渗透,正是现实家庭的生活逻辑,才使家庭的伦理意义凸显,个体的意义感也由此产生。
(2)完整的家庭生活尽管重要,却不能涵盖个体价值世界的全部,社会性价值要在村庄交往中获得。村庄是中国农民“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场所,是集生产、生活、娱乐、价值于一体的共同体。个体要在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处理与其他村民关系中确立社会性价值,成就村庄社会地位。社会性价值有两个获取来源:一是村民的基本社会评价,如好人或歹人,正常人或不正常人的二元划分。那些边缘人会遭遇村民排斥,难以获得好评价。二是在与村民的互动中感受自己的村庄位置,从中获取有意义的体验。除开少数经济贫困、道德败坏的村庄边缘人,大部分村民有“人活一口气,树争一张皮”的想法,都在乎村庄生活的体面和尊严。正是家户间面子竞争的胜出,参与公共事务的突出表现,让个体争取到社会性价值,获取到有意义的体验。对于个体来说,家庭生活过得和谐美满,有助于村庄地位的获得,反过来,村庄各种关系理顺了,被大多数村民认可,也会为家庭关系带来便利。社会性价值既是本体性价值的补充,也是家庭生活的无形构成物,无论个体还是家庭都看重村庄声誉。要想在村庄竞争中崭露头角,获取正面评价,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点滴积累。本体性价值的牢固确立使得村庄竞争尽管会带来伤害,个体依然能从家庭中汲取价值力量,继续参与村庄生活。当家庭生活与村庄生活被村庄伦理规范牢牢维系住时,社会性价值的争取与获得就会是良性且有效的,否则,村民会本能地将体现其声誉的外在物品,如房屋、家电等作为争夺或攀比的目标,不顾一切地竞争,带来资源的浪费与面子的名实分离。
(3)主体性价值与前两类价值有质的不同,前两类价值发生的场所不可选择,从出生伊始,个体就要习得并适应相应结构的生活浸染与价值培育,而主体性价值强调自主的生命体验和自如的价值追求,个体能够独立选择生活方式,依据观念心性皈依某种价值。农民获得主体性价值的前提是村庄社会边界开放,家门口的陌生人出现,个体能够自由选择关系圈子而不受传统价值结构的牵绊。主体性价值的获得有两个来源:一是参与现代生活,在不同的行业和兴趣领域与他人交往,接受团体组织的文化培训和价值引导;二是个体在物质生活之外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体验,如加入宗教组织,通过读书修身等活动提高品味境界。主体性价值的获得对大部分农民来说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他们很难逃离村庄结构来获取意义。当然,在村庄共同体瓦解、家庭结构核心化、村民生活原子化的条件下,农民可像城市人那样追求主体性价值。问题在于一旦缺失村庄结构和家庭结构的保护,个体很难抵挡住各种外来价值系统的侵袭,表面上的自主选择无助于现状的改变,甚至会恶化其生存状态和价值感受。主体性价值肇始于村庄结构的扁平化及家庭生活的不完整,当原有的价值系统被摧毁,个体就在能力有限性与命运无常性的摇摆中苦苦追寻立命之所。有些人将物质享受当作价值来体验,有些人将默会圣经旨意当作意义来追求,更多的人为日常生活的无聊、未来生活的不确定、世俗生活的艰难所击垮,稍有不如意,就以自杀结束对价值的追寻。当以家庭组织为载体,以村庄生活为补充的“过日子”逻辑被打破后,个体就会在价值混乱中无所适从、精神萎靡,他人的一个眼神、一句话就有可能调动其敏感心理,促发不可预期的个体行动。
四、价值迷失与农村老人自杀
1.本体性价值的坍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不断发动群众运动,族权父权夫权被彻底否定。与此同时,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推广科学话语和共产主义信仰,祖先祭祀和民间信仰被否弃,传统仪式的文化性和宗教性被剥离,只剩下一些程序性的民俗表演。现在的J村农民基本没有祖先观念和鬼神观念,他们每年会照例上坟烧纸,但大多数人不明了其中的意义,只是觉得大家都这样做,自己不做好像不太好。与农民观念变化相适应的是丧葬习俗。村民们说,“有个好老头,就有个好婚礼;有个好儿子,就有个好葬礼”。葬礼现在是越来越办得隆重,但葬礼形式的简化与程序的复杂与对逝者的敬意无关,只为彰显生者的社会面子,在丧葬活动上不愿花钱的村民会被人看不起,丧葬仪式的安排也没有什么禁忌。村民只相信科学,相信唯物论,人死如灯灭,拉出去埋了就行了。至于以前说的血脉延续,每个人都活在过去也活在未来等被村民嘲笑为封建迷信。在科学观的指导下,村民都认为,人死了精神也死掉了,只剩下尸体的处理,终会化为泥土,都认同火化,觉得干净方便。对于老人来说,生命的物质化及去神圣化使得他可随意处置身体,并无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他们感受不到子代送葬、举行祭祀背后的价值感,家庭仅仅由子代构成,自己活着的时候是负担、是累赘,死后也不会有“父子一体”的感受,如此生命观与家庭观为老人自杀创造了条件。
农民本体性价值的变迁还表现在生育观念上。即使国家政策允许头胎生女孩后还能再生二胎,J村人也只愿生一胎。村民们认为,生男生女都一样,甚至女儿更好些,女儿会照顾人,更体贴人,抚养女儿更少操心。村民不想生两胎主要是怕增加自己的负担,除开必要的教育与生活开支,父母还要给小孩买玩具、零食,送小孩上培训班。随着物价的上涨,小孩的零用钱和教育费用大大增加,搞不好自己的幸福就会被断送出去,这与以前强烈的生儿冲动和多子多福观念形成极大反差。正是关乎本体性价值的追求和传宗接代的宗教般使命,父代坚韧、执着地生育小孩,将之抚养成人,认为儿子是家庭存在的意义。现在随着传宗接代观念的丧失,老人很难找到顽强生活下去的意义,他要思考有限身体和无限意义间的连接问题,要思考物质的匮乏所带来的生活享受问题。所以,上述因疾病困扰而自杀和因孤独无力而自杀的现象无不是祖先信仰观念散落、延续香火观念缺失的产物。
2.社会性价值的丧失
个体除从家庭这个初级群体获取本体性价值,还要在村落交往中获得社会性价值。费孝通说,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要在传统规定下的社会里生活,必然要靠长老进行教化[24]。老人因生活经验丰富、年龄辈分较高、习得村落文化,必然在村庄公共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主要表现就是年轻人见到老人都会亲切地称谓、礼貌地打招呼;村民多会向老人请教根据什么时令插秧打药,如何管理农田的学问;在村庄事务中老人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决议时要将老人的言论充分考虑进去;老人之间会经常往来,谈家常、议子代、抨击不道德,宣扬善与真……那时的老人是有社会地位的,能够获得人们的尊敬与爱戴,能够感受到家户交往带来的尊严感与体面感。
而现在,年轻人见到老人不理不睬,有的人甚至恶俗的称呼、开低俗的玩笑;从生产领域退出后,老人的生活单调乏味,每天吃完饭后无所事事,只能房前屋后到处转悠;老人早已不是村庄中博学多才的人,他们的认识跟不上形势,被年轻人讥讽为“老古董”;村庄中属于老人的娱乐很少,有些老人甚至没人可聊天,只好坐上麻将桌,在金钱输赢中获得快感;年轻人围成圈子讲话,老人凑上去插话,无人回应,有时还被顶撞回去,甚至老人一走近,年轻人就慢慢散开。笔者调查时老人就抱怨,“老了就没意思了,也没人理你,玩都不知道怎么玩”。退出村庄关系交往,退出公共生活,老人获得社会性价值的源泉丧失。
3.主体性价值的被迫选择
当人们不再用祭祀祖先、传宗接代来获得超越性价值时,老人就只能在世俗的过日子中理解生命意义。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家庭成员的互相关心、互相照顾是老人走完余生的精神动力。在丧失经济权力支撑、文化资源维护后,老人不仅成为村庄中的弱势群体,而且也成为家庭中的弱者,他们没有追求正义和幸福的能力。在家中,他们和儿子分开居住,分开吃饭,不敢也不愿麻烦儿子,丧失不少与子代的交流机会;帮子代干农活,父子碰到一起也很难说上话,有时还要遭受儿媳妇的埋怨;即使坐在一起,儿子宁愿看电视,也不愿跟老人说几句话;儿子家里有什么事情,他不会同老人商量,老人要是关心下,会被挡回去,说老人多管闲事;生个小病,儿子说太忙,不愿回来看望;生个大病,儿子直接“判老人死刑”,不予治疗甚至施加精神暴力……在缺失伦常关系的家庭,每个成员应享有的尊重和关心被赤裸裸的现实击得粉碎,老人感受不到情感慰藉和儿孙绕膝的温情。
随着市场经济的刺激和大众传媒的渗透,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传统“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邻里关系瓦解,村民交往变得利益化、世俗化,家户关系变得松散化、冷漠化。农民职业分化带来经济分层,催生出激烈的社会竞争,引发村民为争夺社会性价值无所不用其极,即使冲破社会底线与价值下线也在所不惜。为了成为“人上人”,获得面子与实利,村民进行全面的投入产出分析,对家庭成员的经济价值作评估,老人即在经济算计之列。老人有劳动能力时,子代一般会推迟分家,让老人帮助种田、打理家务,老人要求单过不被同意。考虑到子代现实生活困难,老人也会与子代一起生活,帮忙子代干活赚钱。一旦老人丧失劳动能力,就会被视为竞争的累赘。此时,儿媳妇开始埋怨老人、家庭纠纷增多,代际矛盾不可调和,老人被迫提出分家。
若老人继续跟随子代生活,老人或者在倍尝子代言语羞辱和日常生活的孤单后,苦于无法补给残存的价值,索性选择自杀来解脱;或者变得极其脆弱而敏感,因子女的一两句言语感受到尊严受践踏,心中怒气爆发而自杀;或者为追求传统价值不懈努力,时刻想着为子代的幸福做力所能及的事,甘愿以个人的死亡缓和家庭的困顿与矛盾。当代际关系紧张,大家庭难以维系时,父代会选择单过,在小家庭中找寻价值安放之所。如此,当老人身体强健时,他凭借物质消费和体力活动来获得充实感;当身体生病无法动弹、无法享受时,老人会感到孤苦无依,自杀对他们而言是摆脱意义虚无的捷径;在身患疾病时,老人不仅要承受身体的疼痛,还面临价值世界的折磨,肉体的疼痛成为老人无助悲观的根源,而“老人能劳动就是个人,不能劳动就不是个人”的观念则促成了他们对自杀的算计和实施。总之,主体性价值的被迫选择与老人弱势地位的结合孕育出的不是个体的价值新生,而是价值灾难与自杀归宿。
本体性价值是个体价值系统的基础,有了本体性价值,农民的行动就有了方向和意义,就不会在人生根本意义问题上发生困惑,才能从事坚韧顽强的家庭生活实践。社会性价值在村庄生活中获得,是本体性价值的重要补充,正是本体性价值的存在使人们追求社会性价值时理智、平和、有底线,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统一于伦理性的“过日子”中,共同受村庄文化网络规范。主体性价值是现代性进村的产物,当前的农民很难体验到主体性价值带来的意义与尊严,相反,他们会时时感受到命运的残酷、生活的无助、意义的虚无。主体性价值是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丧失后的伴生物,带给农村底层群体的不是价值福祉,而是价值灾难。
老人自杀源于价值迷失,源于家庭伦理性和村庄规范性的弱化。随着村庄外向性的增强及经济社会发展,老人的村庄地位急剧下降,获取社会性价值的源头被堵塞。经过政治运动及市场化冲击,家庭伦常关系被抛弃,家庭生活变为自主关系建构,老人作为家庭里的弱者,本体性价值迅速坍塌,催生出老人因虚无、脆弱,赌气、孤独而轻易自杀的现象。村庄经济竞争的剧烈及本体性价值的丧失使年轻人为竞争社会性价值不惜一切,老人残存的本体性价值被子代利用后便走向自杀。从主体性价值的角度看,农村老人边缘性角色身份及主体性的被动获得带来的无助、无聊与痛苦为其自杀打开了方便之门。
[1] Litman,Robert.”Sigmund Freund on Suicide ”,Sigmund
Freud on Suicide.in:Essential Papers on Suicidel[M].New York University,1996.
[2] 季建林,赵静波.自杀危机与预言干预[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 Shneidman E.Suicide as Psychache[M].Northvale A ronson J,1993.
[4] Shneidman E.The Suicidal Mind[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5] 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6-8.
[6] 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 刘燕舞.自杀秩序及其社会基础——基于湖北省J县鄂村老年人自杀的个案研究[J].现代中国研究(日本),2009(9).
[8] 陈柏峰.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9(4):157-176.
[9] 张翼.社会学自杀研究理路的演进[J].社会学研究,2002(4):27-42.
[10] 刘燕舞.自杀研究:困境表述、理论检视与进路转换[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63-70.
[11] Jack Douglas,The Social Meanings of Suicide,Princeton[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
[12] 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3] 杨华,范芳旭.自杀秩序与湖北京山老年人自杀[J].开放时代,2009(5):104-125.
[14] He,Zhaoxiong & David Lester 2002,“Sex Ratio in Chinese Suicide.”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95( 2) .
[15] 吴飞.自杀与美好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2007.[16] 杨华.当前我国农村代际关系均衡模式的变化——从道德性越轨和农民“命”的观念说起[J].古今农业,2007(4):4-7.
[17] 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18] 李猛.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J].社会学研究,2010(5):1-30.
[19] 吕德文.“差序格局”的拓展性理解——行动单位的视角[J].江海学刊,2007(4):118-121.
[20] 桂华.论家庭继替——兼论农村家庭区域类型[J].未刊稿.
[21] 贺雪峰.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乡村治理的影响——辽宁大古村调查为例[J].学习与探索,2007(5).
[22]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50.
[23] 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9-32.
[2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6-67.
责任编辑:陈向科
Lost in value and suicide of elderly: Based on investigation in village J of Jingshan county, Hubei
LIU Rui, YANG Hua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Rural Governanc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The suicide of rural elderly is related with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lost in value, which may be motivated by much concern towards their offspring, family conflicts, loneliness or diseases. The author divides famer’s value system into three parts: ontological value, social value and subjectivity value. In this system, ontological value can be regarded as the basis and social value i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of it, which both are united under "living a peaceful life " practice and regulated by village culture network; while subjectivity value comes after the loss of the former two values,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modernization of village. Thus, the collapse of ontological value, the loss of social value and the forceful choice of subjectivity value may follow the loss of family ethics and weakening of village life norms, resulting the chaotic situation of value placing and suicide be the end.
lost in value; suicide of elderly; ontological value; social value; subjectivity value
F590;C913
A
1009-2013(2014)06-0046-08
10.13331/j.cnki.jhau(ss).2014.06.009
2014-09-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SH004);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
刘锐(1987—),男,湖北十堰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应用和乡村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