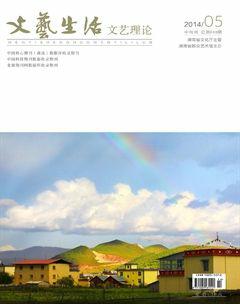《诗》“兴”运思的形式批评
翟丕锋
摘 要:本文以《诗经》文本阐释为基础,从“兴”的运思形式入手,对其进行形式意义的美学观照,认为,《诗》“兴”运思与形式的关联既体现在外物的形态美对创作者审美情感的唤起之中,又体现在创作者基于是否有助于“创造形式意味”而对纷繁审美意象进行简化的过程之中。
关键词:《诗经》;感兴;物色;形式批评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4-0001-02
“兴”的创始是《诗经》在艺术上的一个突出成就,其广泛运用构成了《诗经》独特的艺术风貌和审美价值。《文心雕龙·物色》赞语云:“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形象地将起兴与情感系连在一起,道出了“兴”之三昧。可以说,“兴”是中国古典抒情诗艺术创作的动因和推力,也是最能彰显中国古典美学特质的元范畴。“兴”的起因是由于外物之于主体心灵的偶尔触遇,这种触遇又在不期然间推动了主体从自然情感到审美情感的暗转,在强劲的创作冲动和情感凝定中,审美主体对外在物象予以抉要申发,将之创化为主体心灵中的审美意象,审美情感的唤起过程以及审美意象的生成过程便是美学意义上的“起兴”。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发生学的基本观念,“兴不是一般的创作冲动的发生过程,而是指艺术杰作产生中的思维进路”,“揭示了由自然情感的兴发到审美情感的转换,再由审美情感自然外显为臻于化境的艺术形式”①。
一、“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艺术家通过对某种形式或形式关系的感知而获得情感是贝尔美学的基本命题,他认为,“艺术家在获得灵感的时刻所感受到的情感,不是在作为手段的对象中感受到的,而是在作为纯粹形式的对象中感受到的,也就是说,是在那些本身作为目的的对象中感受到的②。”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指出“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兴”的运思同样遵循了形式激发感情的理路。这个契合正是探求“兴”的运思形式的理论基础。
“感物而兴”是“兴”在创作论层面上的重要体现,也是“兴”的运思起点。在中国美学史上,《乐记》是“感物”说的滥觞。“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作为发轫,《乐记》已经揭示出了外物变化引起心灵波动的文艺创作原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陆机的《文赋》对“感物”说进行了进一步发挥,《文赋》序中说:“伫中区以玄览,遗情志於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尽管这里只是表明了四季变迁带给作者的思绪与浮想,实际上其“叹逝”、“思纷”的生发已经由自然景物拓展到了纷繁的社会万象。此外,陆机谈到“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既论述了物对心的感发作用,又谈到了作家之“意”对“物”的统摄与驾驭。钟嵘在《诗品序》中也提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将“气”作为“物”动的本因,使“物感”说覆上了氤氲的哲学色彩。
刘勰《文心雕龙》的《物色》、《比兴》、《神思》诸篇则将“感兴”作为审美运思的完成过程予以了整体把握,尤其是注意到了“感兴”致思理路的形式特征,是对前人“感物说”的重大突破。何为“物色”?简言之,就是具有形式美的外物,李善注曰:“四时所观之物色,而为之赋。又云有物有文曰色”,“有物有文曰色”,《说文解字》云“文,错画也,交象文”,李善此注颇为精当,尤其是“文”点出了纳入诗人审美视野的“物”的形式美。刘勰以“物色”为篇名,更是寄意深远,这就超越了《乐记》的“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文赋》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以及钟嵘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而将“物”外在样态的形式美纳入“感兴”致思的体察,也就揭示了“物”所以能感动人心的根由,将“感物说”推进了一大步。
《物色》篇中“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与“物色相召,人谁获安”道出了作为审美客体的“物色”正是以其独特的形式美触发了作者的心灵;“岁有其物,物有其容”则例证般地道出了四季的外在形态变化带给人的情感迁转,“献岁发春”使人“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使人“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使人“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则让人“矜肃之虑深”,不同的物候以其不同的外在形式美兴发起人种种不同的情感,形式美的变化正是心灵意绪变化的因由。这恰好印证了西方格式塔派美学家关于外物与人类情感之间存在“异质同构”关系的大胆创设。
如钟嵘所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人的自然情感为外物所触发,产生创作冲动,并且,人的自然情感与审美情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然而,“从主体的自然情感到审美情感,是需要进行形式化和意象化的表现的”,“艺术家将主体的自然情感经过形式化的过滤和普遍性的提升”,才能形成“具有符号性质的审美情感”③。关于何种形式能唤起人的审美情感,何种形式只能唤起人的自然情感,贝尔有着独到见解,他认为“物质美完全不能像艺术作品那样打动我们。‘有意味的形式向我们传达了它的创作者所感受到的某种情感,而‘美却没有,以此来解释‘有意味的形式和‘美的区别,这样做是颇具诱惑力的④”。贝尔的论述将形式划分为“有意味的形式”和普通形式,并认为前者能兴发审美情感,而后者只能唤起自然情感,可见,外物是否具备“有意味的形式”所要求的独特形式禀赋,是审美情感能否生成的先决要因,这就为审美情感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新的维度。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主体的创化之功,但主体的形式创化一旦脱离了“物色”所具有的“有意味的形式”的独特禀赋,就成了空中楼阁,主体创化与“物色”形式的完美契合,才能使作品臻于佳境。
不妨从《诗经》文本中为“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寻找例证,如《周南·汝坟》委婉而缠绵地表达了一位妇女对她丈夫的思念之情。作者在汝水边砍柴,并由此起兴,引发了她对在外丈夫的思念,预想相见后的快乐与不离不弃的欣慰,作者由此结构诗篇。毛传曰:“遵,循也。汝,水名也。坟,大防也。枝曰条,曰枚”,而所谓“肄”则是老树被砍掉之后长出的嫩枝条,女子行走在波光粼粼的汝水之畔,被砍去的老树尚且长出了新枝桠,可心上人却杳无归讯,正是水岸伐枚、老树新枝这独具形态美的“物色”,引发了作者对远行人的无尽思念,同时唤起了作者的审美情感,在“兴”的形式牵引下创就成篇。endprint
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
“感兴还不仅唤起了主体的情感,而且更在于以此为艺术创作的动力,将所感之物象化为创作中的有机审美意象……兴是一种强劲的推动力,使创作主体所感知物象,颇为自然地在心灵中创化为审美意象,又以作者所谙熟的艺术语言表现出来,这个时候,兴则更多地体现为主体的创化能力。所感之物,往往经过作者的审美运思而进入作品,而成为审美意象⑤。”张晶先生的这段论述颇中“兴”之肯肇,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兴”在所感之物象化为有机审美意象时所承担的艺术创作动力功能,独辟蹊径,发前人所未发。下文将循此运思路径,以《文心雕龙·物色》篇为中心,探讨在审美意象生成的过程中,“有意味的形式”所发挥的独特作用。《物色》篇云:“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段论述蕴含着丰富的美学内涵,在“物色”对诗人心灵的感召下,鲜明而生动的物象便在作者心灵中不断涌现,不断新生,绵延不绝,联类不穷,兴发起作者的不尽联想和磅礴意绪,因而会“流连万象之际”,以至“沉吟视听”,众声喧哗。然而,这些具有形式美的“物色”所召唤的众多审美意象毕竟缠绵错节,杂乱无章,如何以特定的形式和高妙的概括将其化约为整饬、有序的形态,凝定在文学作品之中,并以“突出的审美意象涵盖整体的氛围”,达到“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的审美效应,就离不开审美主体对客体的裁剪与统摄。这种主体创化的能动性与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理论再一次产生交集。
且从二者对艺术事项的评价中辨析同异。刘勰说“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泽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描述了《诗经》、《离骚》和汉赋三者间的演化与流变,并将《诗经》和汉赋的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进行了对比,前者是“诗人丽泽约言”,后者则是“辞人丽淫而繁句”,而刘勰则明显倾向于《诗经》“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的美学风貌,认为《诗经》中一些简约而传神的艺术表现(如“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等)能够“一言穷理”、“两字穷形”,状物形神,历久弥新;相反,他对汉赋中的一些末流则嗤之为“写物图貌,蔚似雕画”,认为“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指责汉赋中的模山范水、淫辞丽句,使本当具有创化能力的主体受役于外物,卒使“兴义销亡”。
将《唐风·杕杜》与《有杕之杜》做比较,“杕”是指树木孤生独立的样子,“杜”即杜梨,又名棠梨,两篇诗作中,茕茕孑立却又枝叶繁茂的杜梨树兀立在作者面前,它独特的形态美勾连其作者的情思,让他思绪蹁跹,联类无穷,而足以让作者触动的则或许是它的生机,或许是它的独立,或许是它的婀娜,或许是它的生命力,抑或别的,但其余的意象却如贝尔所说的“两万片叶子”一样无关紧要,因为它们体现不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形式意味”,故此,《杕杜》的作者仅仅撷取了“其叶湑湑”、“其叶菁菁”以“反兴”他的孤独无依,而《有杕之杜》的作者则仅仅撷取了“生于道左”、“生于道周”以“兴发”他的求贤若渴,这便是刘勰所说的“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也是贝尔所说的“去掉无关的细节”。
再以人所熟知的《周南·关雎》篇为例。首句是人们公认的起兴之句。传曰:“兴也。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雌鸡之有别焉。”这是说雎鸠有喻后妃之意。朱熹《诗集传》释“雎鸠”为“王雎”,是一种形体较为庞大的水鸟,古人说此鸟“挚而有别”。鸟儿在河洲雄飞雌从、双栖双宿,兴发起诗人无尽意绪,他只在有意无意之间撷取了最具形式意味的“挚而有别”使雎鸠对鸣和君子求偶系连,而其余意绪则都是“与信息有关的无关枝节”,因其“无助于创造形式意味”而被剔除,如此以来,全篇简而有法,“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足见,《诗》“兴”之“简化”亦可解为构筑“有意味的形式”之需要。
在贝尔的理论王国里,简化具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有意识的,一种是无意识的,前者一般是出于传递信息或者象征的需要而做的形式注解,它“不是艺术家的情感所造就的,而是由他的理智所创造的⑥”,只是充当了“形式的情报员”,因而也就破坏了艺术的完整性,折损了形式的“意味”;而后者则是在无意之间基于审美情感自身逻辑而做出的选择,充分体现了形式的“意味”。这两种形态又呼应了刘勰所分析的汉赋、《诗经》各自代表的美学原则。汉赋之末流,其意象选择是基于理智的,折损了形式的“意味”,固刘勰批评说“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文心雕龙·诠赋第八》),《诗经》中起“兴”则多是本于情感逻辑的自然简化,因而能够“以少总多,情貌无遗”、“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简化的两种形态,或许正是“诗人丽泽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的原因所在。在此,《诗》“兴”的“以少总多,情貌无遗”与西方美学语境中的“简化”命题呈现出朦胧的关联
注释:
①张晶.“感兴”:情感唤起与审美表现.文艺理论研究,2008,(2):103.
②克莱夫·贝尔.艺术.薛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9.
③张晶.自然情感·审美情感·道德情感.文艺理论研究.2010(1):80.
④克莱夫·贝尔.艺术.薛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8.
⑤张晶.“感兴”:情感唤起与审美表现.文艺理论研究,2008,(2):105.
⑥克莱夫·贝尔.艺术.薛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