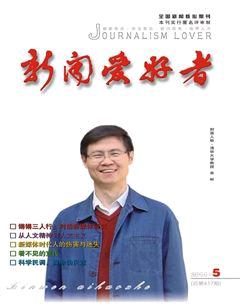立足中国土
李彬
20世纪末,正当时论欢呼雀跃“千禧年”,新自由主义的“新四化”——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俨然席卷世界、攻城略地之际,牵连中国城乡亿万家庭的“下岗”与“三农”问题感觉陡然升级,一度差不多接近“崩溃的边缘”,一时间引起上上下下的广泛关注与深切忧虑。有个段子说,某领导去农家访贫问苦,问大家最缺什么,回答竟然是“陈胜吴广”。这个故事尽管极端,但也表明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改革”一度导致何等严峻的社会矛盾。于是,由此开始,特别是2002年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推出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社会政策以及惠农政策,包括减免直至彻底取消农业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城镇化建设等,不仅逐渐缓解了社会危机,而且也制约或扭转了“原教旨”的市场化导向。
在此期间,一批脚踏实地的学者以马克思“改变世界”的情怀和张承志“泥巴汗水”的学问,探求真知,引导舆论,影响决策,为改革开放的健全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如老一辈的社会学家费孝通、陆学艺,以及新生代的温铁军、曹锦清。1999年最后一期《读书》杂志,不无巧合地发表了一篇头题文章《“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论事说理,深刻实在,而作者是“主流学界”名不见经传的温铁军——做过生产队长的知青,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任母校2004年成立的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2000年,同样鲜为人知的上海学者曹锦清出版了《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副题“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再次聚焦相似的现实问题。这是一部当代中国的实证研究著作,既真切记录了转型中的基层社会现状,细致考察了错综复杂的突出矛盾,又对其来龙去脉作了入情入理的分析。所以,一面世就获得各方包括高层的青睐,迄今已重印13次,2013年又有“增补本”问世,成为费孝通《乡土中国》之后传播最广的乡土著述。
20世纪40年代后期,费孝通根据自己在西南联大讲授“乡村社会学”的内容,为《世纪评论》撰写了14篇连载文章,后来结集出版,遂成为现代学术经典《乡土中国》(1947年)。在这部薄薄的5万余言的“小册子”里,作者阐发了一套富有洞见、充满想象、鲜明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学术思想,既赢得中外学者的称赞,也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其中,尤其值得深思的是费孝通“观察与思考”的立足点。众所周知,这位曾经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学者,一生始终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贴着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研究学术,著书立说,从而确立了在国际学界的崇高地位。而这种学术姿态与问题意识,正是平常耳熟能详而又可能麻木不仁的“实事求是”,也是新闻学家、百岁老人甘惜分力主的“立足中国土”。《乡土中国》开宗明义就提示了这一学术自觉意识: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这段看似平淡无奇的文字,含有颇堪深究的意味。首先,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历史如此,现实依然,纵然经过一百多年现代化潮流的冲刷,这个特性以及总体判断今天看来同样富有概括性和解释力。时论之所以忽略这一点,也在于其漠视了制约中国一切发展的基本国情:人口众多而资源有限,同时又不得不追赶现代化目标——且不说国际环境制约。其次,上述观察与判断是从整个社会奠基其上的基层而非上层看去的。如果不是面对960万平方公里陆地国土的广土众民,而是从近代东西方接触边缘的特殊社会如“上海滩”进行审视,那么所见所思自然另当别论。再次,常被漠视、轻视、蔑视的乡下人,千百年来一直构成中国社会的基础或主体,无论过去“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还是如今“为人民服务”的“民”,说到底都是“农”民——涵盖“农林牧副渔”民。一句话,乡土中国就是中国,乡土中国才是中国。所以,谁理解了这一点,谁就真正理解了中国;谁把握了这一点,谁就切实把握了中国。新世纪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虑,同样首先取决于对乡土中国状况及其总体态势的观照,无论是“新农村”还是“城镇化”,无论是“西部大开发”还是“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无不围绕乡土中国这一基点展开。十八大以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总书记习近平先后把平山县和兰考县作为自己的联系点,更是为此提供了现实范本。用“三农”问题专家贺雪峰教授的话说:“占大多数的农民有出路,中国才有出路。”
五四之后,鉴于“全盘西化”的虚妄,一批知识分子日渐认识乡土中国及其意义,纷纷走向田野,从不同方面探究现实问题,关注中国的基层与主体,从而不仅深刻影响了社会历史的走向,而且产生了一批学术思想的经典之作,包括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经济学家、柏林大学博士陈翰笙的学位论文《中国的地主和农民》,社会学家、英国博士费孝通的学位论文《江村经济》,美国博士晏阳初、新儒家梁漱溟等乡村建设的经验模式与理论成果等。当今,又一批知识分子沿着前辈道路,深入田垄,入户农家,围坐炕头,脚踏实地做学问,实事求是探真知,同样完成了一批无愧前人、无愧时代的学术力作,如阎云翔、温铁军、曹锦清、高默波、马戎、贺雪峰、应星、吴毅、景军等人的著述。阎云翔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应星的博士论文《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高默波的《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吴毅的《小城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等,尤其适合一般读者,学术文字写得如同非虚构作品,读来引人入胜,令人叹赏。
作为“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黄河边的中国》不同于一般正襟危坐的学术著作,而是采用夹叙夹议的叙事笔法,由此不仅呈现了原生态的现实情景以及面对问题本身的鲜活思考,而且像出色的新闻报道似的使普通人也能够明白问题所在及其实质。全书60余万字,洋洋大观,包罗广泛,其中特别集中、给人印象深刻的话题有农民负担、计划生育、党政腐败、干群关系、信仰危机等。作者揭示的种种现象与矛盾,既是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是当下影响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重大课题。试举几例,即知大概:endprint
当今中国似乎有三套语言:一是传媒官话,空洞无物。二是校园讲义,没有根基。这套从西方传入的学术语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找不到它们的所指,成为漂浮在知识分子表层思维与语言中的浮萍。三是民间语言,尤其是酒席语言,反映出变动着的社会事实与社会情绪,语言活泼而富有生趣。[1]7-8
这股弥漫于中原大地且遍及各社会阶层(主要是农民阶层)的社会情绪,由正反两方面的情绪组成:对毛泽东的怀念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们得到了土地,又得到了自由,他们通过土地与自由第一次得到了温饱并逐渐改善了自身的居住条件,这是农民兄弟们一致认可的基本事实。但中原(其实应包括整个中西部广大地区)民众何以如此强烈地怀念毛泽东,怀念毛泽东时代且同样如此强烈地对改革开放后的现实状况感到不满呢?……关键的原因恐怕在于社会风气的恶化、地方党政的腐败与沉重的农民负担。[1]563
从正阳到新蔡,从新蔡到平舆沿途凡是有墙的地方,差不多都刷着各种大幅标语:
“谁发财,谁光荣,谁贫穷,谁无能。”
“八仙过海显神通,致富路上当先锋。”
“家家上项目,户户奔小康。”
“十万大军搞劳务,二十万户上项目。”
“家家有项目,人人有活路,天天有收入。”
“户种两亩棉,增收两千元。”
“家养两头猪,致富不用愁。”
在中原大地,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顺口溜”:其一流行于民间,称为民谣。其二流行于墙上,称为官谣。套用《诗经》的用语来说,前为“风”,后为“雅颂”。民谣表达的是“社会情绪”,官谣表达的是地方党政的政经目标。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官谣的制作者们为什么不去追查每句口号的现实性?每家养猪两头,就能致富吗?至于“发财”与“光荣”之间,“贫穷”与“无能”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只讲“发财”不论手段,只以贫富论荣辱,论能与无能,这不正是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吗?[1]565-566
对地方党政腐败的无奈,对反腐败的悲观,对腐败结果的危机感,在河南各社会阶层都存在。一位党校副校长说:“腐败是反不了的,结果必然是改朝换代。”一位果园承包主说:“再腐败下去,必然天下大乱,到时我就是土匪头子。”某集团公司接待办主任说:“只有像毛泽东那样,发动一场群众运动,才有可能制止腐败。”如今,这位复员军人以为“只有打仗才能解决腐败问题”。从这些激愤的语言中,我不仅感受到内心的震惊,也预感到若隐若现的政治危机。[1]710
关键的问题还是“旗帜”与“信仰”问题。中共十四大报告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来党校学习培训的广大地方干部并不认为已经解决了,甚至许多党校教员也不认为已经解决了。现有的理论无法回答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一个难以讳言的事实。在各种苛捐杂税重压下的广大农民,怎么会相信地方官员是代表他们利益的呢?面对着日趋加剧的贫富分化,怎能叫人相信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呢?老百姓们不相信,地方党政官员本身也不相信。如今当官到底为什么?县、乡干部集中学习讨论,稍谈片刻即入两大主题:升官与女人。这并不是个别现象。把聚集私人财富作为当官目的者,也不乏其人。没有一面能将全体党员与党政干部凝聚起来的“旗帜”与“信仰”,实在是地方官吏腐败的一个更内在、更深刻的原因。[1]606
最令我担忧的问题是:各级地方政权存在着日益脱离社会,且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趋势。用现代通行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官僚化与特权化的强大驱动力。官吏的以权谋私等权力腐败现象,仅仅是上述趋势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已。河南民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五六十年代是‘鱼水关系,80年代是‘油水关系,90年代是‘水火关系。”说的是近半个世纪来干群关系(其实是地方党政与群众的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从“鱼水”到“油水”再到“水火”关系,形象地说明了地方政权逐渐脱离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发展过程。
有人将上述趋向归咎于地方干部的个人素质问题。……有人说是“政治体制”问题,说缺乏有效权力监督的集权体制应对上述倾向负全部责任。在我看来,上述分析,皆为表面、肤浅之词。地方政权脱离社会且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趋势,或有更为深刻的根源。
除了毛泽东的“群众运动”与西方的“民主制”之外,是否能找到第三条道路或方法以解决公共权力的“脱离”与“凌驾”问题,这是一切关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思维头脑共同探寻的重大问题。[1]716-718
本书叙事起于千年古都的开封,而2014年承蒙河南大学不弃,聘我为“黄河学者”,这个名衔在我感到沉甸甸的,既因为“黄河入海流”的悠远文化,也由于“行行复行行”的乡土中国。站在黄河边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新四化”,特别是青山绿水的变异、自然资源的减少、乡村社会的衰败、草原牧场的退化等,会更深切地理解中国“问题”与社会“主义”,同时也更懂得中国是一部无字的大书,乡土中国由于承载千万年文明传统,则是穷其一生也不见得能读懂的天书。《黄河边的中国》一开始先就如何打开而非解读这部大书、天书作了分析,谈到如何观察与思考、如何进入社会生活的真实现场等经验。通常认为,观察与思考主要受制于主观因素,如态度认真、学识渊博、思路清晰等,而往往无视客观“视点”——观察与思考的立足点。事实上,如同常识所知的情况,站在不同的位置就会看到不同的景观,立足不同视点面对世界也同样会发现不同的问题。这里,曹锦清论及两种相反的视点,一是“从外向内、从上向下”,一是“从内向外、从下向上”:
何谓“外、内”“上、下”?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由外向内看”,就是通过“译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向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1]1endprint
两种视点虽然形同双目成像,互为补充,就像我们常把“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连在一起,甘惜分也将“回到马克思”与“立足中国土”相提并论,但曹锦清更趋向于“内”与“下”的视点,他本人也曾有过一个由“从外向内、从上向下”到“从内向外、从下向上”的视点转移。20世纪80年代,如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一头钻入“译语”,徜徉于西学中令人信服的“成套价值目标”与“各种认识工具”。就像有人揶揄的:探究中国问题,不先面对实际问题,而是不远万里,跋山涉水,绕道纽约、伦敦、巴黎,取经拜佛,求学问道,引入一套一套的“译语”,取回一套一套的“经义”。可惜,无论“译语”与“经义”怎么变来变去,中国问题貌似安之若素,依然岿然不动。为了认识现实中国,打开这部大书、天书,1988年,曹锦清打点行装,重返农村,完成了一部《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1992年)。1996年,他又来到河南,漫游中原——华夏文明摇篮,将开封、信阳、驻马店等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谈、所思,写入前书的姊妹篇《黄河边的中国》(2000年),再次体现了“从内向外、从下向上”的视点。
其实,这种观察与思考的视点,也是老一代新闻工作者的常态,属于新中国新闻业弥足珍贵的传统,正如习仲勋1951年在西北地区报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标题所示: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虽然这一传统受过极“左”的干扰与扭曲,但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做一个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记者”(何盈),始终是一代新闻人的专业理念与价值追求:从邓拓到范敬宜,从穆青到南振中……范敬宜说过一句有名的话:“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有句土语也很传神:“只有眼皮贴着地皮,才能看见草根。”范敬宜层出不穷的报道“点子”,以及一生不同凡响的新闻成就,无不源于他数十年的基层阅历,无不植根于透彻理解与把握的乡土中国,特别是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如其词中倾吐的:“望白云深处千万家,情难抑。”遗憾的是,在拨乱反正、与时俱进之际,我们一不小心把这些传统丢弃了,弄得今天的新闻仿佛时尚似的越来越倾心都市繁华,越来越远离田间地头。十几年前,范敬宜在一首打油诗里曾经写道:“朝辞宾馆彩云间,百里方圆一日还。群众呼声听不见,小车已过万重山。”眼下随着新媒体、高科技的发达,此类问题更是愈演愈烈,而一些记者也貌似越来越有白领小资的“范儿”,而与乡土中国渐行渐远。新世纪以来,新闻界开展的“三项教育”“三贴近”“走转改”活动,也旨在扭转新闻工作的“精英路线”,力图恢复“群众路线”,亦即曹锦清所说的视点转移。
清华大学一向秉承“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的学统,正如清华学子费孝通身上所体现的风范。十余年来,新生入学,不管什么专业,也不论个人兴趣,我都首先推荐两本书: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与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新闻学院2003级本科生李强同学受此启发,利用大二寒假去农村调研,完成一篇4万多字的《乡村八记》。由于范敬宜院长的推荐,这篇学生习作的第一记以《二姨家的年收支明细账》为题,刊于《人民日报》2005年4月3日头版。人民日报记者李泓冰还曾就此发表评论《从费孝通到大学生李强》:
李强的身影,在今天确实有些孤独。以至于我们想给他找一个精神伙伴的话,不由自主地就上溯到了比他年长70多岁的费孝通。这中间的历史跨度,确实太漫长了一点。
年轻的李强之所以让人“惊异”,他的《乡村八记》之所以弥足珍贵,是让我们看到了某种希望。先有徐本禹主动下乡支教感动了中国,后有李强主动“沉入”乡村去懂得中国,如果知识分子关注乡村的理性与热诚,真的能从此蔚为汪洋,而不仅仅是偶一为之的社会实践,那么,这真的是解决“三农”问题、城乡差别问题的又一希望之所在了。
在我看来,对80后、90后的记者与学子来说,《黄河边的中国》尤其具有启蒙价值,具体说来至少有三点:认识中国的视角;研究问题的方法;表达思想的话语。
关于认识中国的视角,时新的潮流不断暗示:离高层越近,离真理越近(高层的“真理”说到底也是来自基层);离纽约、伦敦、巴黎越近,离真理越近(即便人家的“真理”也需要自己的消化);离书本特别是洛克、哈耶克越近,离真理越近(哪怕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的真理一旦成为“本本”“教条”也误国误民)。受此影响,年轻记者与学子往往一门心思巴望乘着全球化飞船,奔向赫胥黎笔下美丽的新世界,或者误把他乡作故乡,让自己的心胸成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然后以现代潮流反复淘洗的大脑反观中国,以一套套时新的“译语”从外向内、从上向下地打量中国,结果不免处处拧巴,格格不入。为此,首先需要“返璞归真”的视点转移,让自己的观察与思考、采访与报道能够实实在在“立足中国土”,而非爱丽丝梦游仙境一般的云里雾里,更非八卦、娱乐、微博似的迷三倒四。为了让思想冲破牢笼,探寻现实中国及其现象、问题、规律及本质,曹锦清有意对各种现成的、权威的、时新的理论保持自醒与警觉,甚至将它们暂时“悬置”起来,让自己处于一种无知无识的“赤子”状态:
所谓“悬置”,既非“抛弃”,又非用以套裁社会事实,而是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理论、概念处于一种“待命”状态,调查者本人则时时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状态,直观社会生活本身。“无知”是相对于“熟悉”而言的,而“熟悉”,或“习以为常”恰恰是理解的最大敌人。只有“无知”“陌生”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让开放的心灵去直接感受来自生活本身的声音,然后去寻找各种表达的概念。调查过程,其实是“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补充的过程。只有通过这条艰辛之路,才能指望找到能够理解社会生活的真正理论。[1]3
关于研究问题的方法,如今也似乎颇为混乱。按照一种流行说辞,好像天底下的研究方法只有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人文方法,一类是现代的实证方法;在此基础上又明里暗里提示人们,只有后者才是研究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与不二法门,而前者是主观的、随意的、浅科学或前科学的乃至不科学的(令人困惑的是孔子、庄子、柏拉图、马克思以及古今无数思想家该当何论);最后图穷匕首见地挑明,原来所谓实证方法就是用一堆统计、问卷、数据、图表等,去揭示活生生的、变动不居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及其规律。这种流行的方法论,在新闻学界也渐成说一不二之势,以至于不少学生一事当前,既不考虑研究的问题及其价值,也不深入社会生活的实际场景,更不对各种现象及其构成因素的复杂关系进行考察,不对其间的历史渊源与来龙去脉展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而不得不闭门造车先弄一套“方法”,诸如表格、数据、问卷什么的,仿佛一旦设计停当,社会生活的全部奥秘与宝藏就会在阿里巴巴“芝麻开门”的咒语中应声而开了。生机勃勃的盛唐人嗤笑冬烘先生,说“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而今可谓“不问天地人,先弄方法论”。endprint
其实,方法如同兵法,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只要胜利,就师出有名。对研究者来说,所谓“胜利”就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问题层出不穷,千变万化,方法也当因地制宜,不拘一格。问题不同,情景不同,方法自然也就不同。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兵法,同样也不可能有千篇一律的方法。而只要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实际上都属于实证范畴。实证实证,无非是实际证明、实地考察、实在分析,或者说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如此而已。就像范长江采写《中国的西北角》时参考的顾祖禹历史地理巨著《读史方舆纪要》,当然方法中也可以包括一些现代数量统计等手段。不论问题而先谈方法,就如同纸上谈兵,焉有不败之理。不难想象,掌握纸上谈兵法的学生一旦进入新闻界,面对纷纷扰扰的社会问题以及林林总总的现实,难免茫然无措,不知从何入手。因为,略微有点中国社会的生活经验,就知道这套“科学方法”基本不灵,既无法以之获取多少事实真相,更不用说探寻问题的本质了。甚至,由于脱离实际,人云亦云,新闻报道还难免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指出的:“当前中国的情况颇为吊诡,到处都在打着为农民讲话的幌子,却在为刁民讲话,为土地食利者讲话,为农业企业讲话,为农村中和农民中的强势群体讲话。而真正最弱势且最广大的9亿农民——小农+农民工,却已经从媒体上悄然消失。”[2]那么,如何才能了解现实生活的实情,揭示中国问题的真相呢?《黄河边的中国》对此既提供了一套实际有效的路径,又阐发了一些深切洞明的思路:
社会生活的真实,决不会主动地向调查者敞开的。“家丑不可外扬”与“熟人、陌生人之间的界线”,是村落文化内固有的两大特征。前者,各家长、村长、乡长们各自小心翼翼地遮蔽起来;后者,使一切陌生人成为“来路不明,形迹可疑”者。乡村社会生活的这种遮盖性与防范性,使得调查者难以自由“入场”,即使“入场”,也难以畅通地获取所需的经验资料。西方社会学中常用的“问卷统计”调查法,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基本上是无效的。因为使得问卷法有效的基本前提——社会生活的敞开性和无防范性——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基本上不存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且有层层防设,就遑论问卷法了。[1]120
最后,表达思想的话语也是不容忽略的问题,属于“走转改”的题中之义,前人之述备矣。这里仅举一例,即见当下流风之一斑。某学生写了篇文章,拿给教授审阅,结果标题中的“视野”被改成“视阈”,因为据说后者比前者更有学术水平。怨不得如今一些学生的语言机械僵硬,也无怪乎如下文字畅行学界:究其“微化”和“碎片化”的变化本质而言,是社会要素、市场要素透过这种“裂解”所获得的因应时代发展和社会改变,从要求的功能重新聚合重组的“前阶”。如此党八股、洋八股,让人不由得想起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中的提醒:“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看看《乡土中国》,多么平易近人,平白如话,又多么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我们自己虽说是已经多少在现代都市里住过一时了,但是一不留心,乡土社会里所养成的习惯还是支配着我们。你不妨试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在面对面的社群里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报姓的。
1938年,艾青在《我爱这土地》里吟出催人泪下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他在另一首《献给乡村的诗》的序里写道:“这个无限广阔的国家和无限丰富的农村生活——无论旧的还是新的——都要求在新诗上有它的重要篇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乡土中国在不失赤子之心者心中,不仅沉淀着异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蕴含,而且展现着无限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恰似2013年入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哈尼梯田,既是天地人合写在大地上的一篇美丽诗章,也无异于诠释了诗人荷尔德林的名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参考文献:
[1]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2]贺雪峰.谁是农民?[J].经济导刊,2014(3).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曾维康:《农民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郑 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