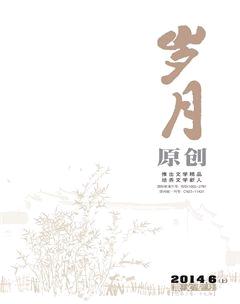梁实秋的雅舍
高维生
我沉在过去的时代里,为了写梁实秋阅读大量的传记和史料,看一些老旧的照片,在历史中寻找人的影迹。2008年,我第二次去重庆来到北碚,住在西南大学附近的一家旅馆,这里距离雅舍不远。我是在下午拜访雅舍的,衡门上的斗拱下,有一块黑色嵌金字的“梁实秋故居”的匾牌,里面是一条纵伸的、不规则的青石台阶。过去的建筑消失,重构的空间发生变化,被赋予新的意义。老的雅舍为我们提供特殊的历史情景。我来的时候,两扇传统的木门敞开,站在大门前,注视“梁实秋故居”几个大字,身后是一条繁忙的马路,人流和车辆穿行而过,耳朵充满各种噪音,很难让心静下来。雅舍在上面的平台,我要攀登长长的石阶。这条石阶路,不是为了创造景观而设,是采取因地制宜。梁实秋初到重庆,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民风民俗,自然与古老的北平不同。浓重的当地话,梁实秋听起来费力,有的话猜半天,才明白讲的什么意思。吃住行是人的生存本能,尤其住为重要,总不能天是房地是床,睡在露天中。梁实秋对当地的建筑感兴趣,觉得此地建房容易,最经济实惠。砖不是用来砌墙,是用来代替柱子使,四根砖柱互不牵连,上面搭上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篦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地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这样的房子在北平,只能作为储存杂物的仓库,薄薄的竹篦墙,遮住人的目光,挡住风雨,不能抵挡冬天的酷寒和风雪。梁实秋住的“雅舍”,用唐代白居易的诗比喻:“吾亦忘青云,衡易足容膝”。梁实秋生活在古老的大家庭中,长大以后,又考入清华大学,然后去美国留学。他经过欧风美雨的洗礼,见过大世面,吃过正宗的西餐,住过大洋楼,看到过不同的建筑,“我的经验不算少,什么‘上支下摘、‘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漂泊久了,梁实秋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地融入进去,不会得水土不服。人无论住在哪里,住得时间久了,对那所房子一定发生感情的变化。这段生活是梁实秋的重要经历,雅舍是一个文本,综合地反映历史,时代的踪影浓缩其中。写出的文字,孩子们的打闹声,朋友们喝茶聊天的话语声,人身体的气味,构成雅舍的复杂空间。在战乱的年代,梁实秋来到后方重庆,远离炮火的危险,已经很幸运了。他和友人建起“雅舍”,其目的不是享福,只想生存下来,不存有大的奢望。雅舍是一所陋房,梁实秋将它安排得有条理,赋予它浪漫诗性的名字。住进去两个多月,梁实秋对空间多了情感。阴灰的雨天过去,一缕阳光从窗子投映进来,就是这朵光线,使房子里有了温暖的关怀。人们搭建简陋的屋子,建筑的材料、竹子、茅草、泥土,脱离开大地,经过双手的构建,实现想象的形式。窗棂上的每一根竹子,显现时间的印记。在一天中,光缠绕其上,梦的韵律,奏出光与物的序曲,唤起人的情感。茶怀中冒出的香气和光融化一起,他感觉房子有家的暖意,不仅是蔽风雨的空间。有窗子能向外眺望,看着挑担走过的人,注视风雨的无常变化,有了创作的冲动。“然不能蔽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1940年,梁实秋在清华时的同学刘英士在重庆办《星期评论》杂志,约他写稿。提出给他辟一专栏,要求他每星期写一篇,每篇不超过两千字。梁实秋便以“雅舍”之名,将专栏定为“雅舍小品”。第一篇就是写“雅舍”,署名“子佳”,于1940年11月开始发表,一般是每期一篇,也时有间断。“雅舍”专栏一问世,便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子佳是谁?人不知,但也有猜疑是梁实秋的,到处都议论纷纷。作家徐仲年说:“你们说子佳是梁实秋,这如何可能?看他翻译的莎士比亚,文字总嫌有点别扭,他怎么能写得出《雅舍小品》那样的文章?”文艺理论家朱光潜给梁实秋写信说:“大作《雅舍小品》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抗战胜利后,梁实秋回到北平,将这34篇《雅舍小品》辑为一册,后来在台湾出版。以后多次再版,都供不应求。同时,梁实秋在台湾继续写作“雅舍小品”109篇,多年畅销不衰。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雅舍小品》流传。“北碚通”李萱华,是当地的文史专家,为寻找和保护雅舍做出了贡献。我在他编写的《梁实秋与雅舍》中,读到他为此事奔波的前后,还有他撰写的文章。寻找雅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由于时间过去太久,其间经历过战争,解放后的政治运动等众多的因素,使得很少有人关注雅舍的生存。李萱华在无望的时候,偶然碰到老舍的儿子舒乙。这是重大的转折,1944年,舒乙随母亲来到北碚的父亲身边,母亲在编译馆上班。有一段时间生病,每天去刘大夫家治疗。有一天在路上,母亲指着刘大夫家后面不远处,山坡上一所不大的房子,对舒乙说,那是她的领导梁实秋先生住的地方。舒乙回到北京向母亲询问当年的情况,确定了准确的方位,并写信告诉李萱华。消失多年的雅舍终于被发现,舒乙写下了当时的心情:……和李萱华先生相识之后,我回到北京,和母亲核实之后,便写了一封信寄给李先生,画了一张示意地图,请他按图寻访,说这个方位是绝对正确的。同年,我遇到梁实秋先生的大千金梁文茜律师,两个人大谈雅舍。她正好也是1943年随她母亲逃到北碚,和她父亲团聚,就住在雅舍里。梁大姐的记性真好,她给我画了雅舍的平面图,哪儿放床,哪儿放桌子,标得清清楚楚。今年春天我又有川鄂之行,是应日本中山时子教授之邀做“老舍之旅”访问团的向导。来到北碚老舍旧居,正好碰见老朋友李萱华先生,他高兴地告诉我,已经在反复核实之后找到了雅舍。它居然还在!是我告诉他的那个地方!我们马上驱车去看,果然不错。梁先生住的时候,房旁有梨树。今天,这个地方叫“梨树村”,的确因梨树而得名。在马路边向上爬大约70步石板台阶,来到一个小平台上,有一座方形的小房子,这便是梁实秋先生故居雅舍了。所不同的是,南北两侧各接出来一间小平房;竹坯墙也变成了砖墙;住户由原来的梁家和吴景超龚业雅两家变成了五家。梁先生原来住的一侧现在的门牌是48号和49号。当年,梁实秋先生为了让邮差和朋友们知道他们的住地,在马路边上立了一块指路木牌,上书“雅舍”二字,这便是雅舍的来历。听当地居民说,这里明年就要拆迁了,在原地要盖新楼,听了不觉大吃一惊,刚刚见到的雅舍再过一年将不复存在了。我一边照相,一边想:我很幸运,我找到了雅舍,看到了雅舍,为雅舍照了相,几乎是在最后的时刻!中山时子当场表示了惋惜之情,她拉住李萱华先生的手说:“雅舍举世闻名,世界有多少人在向往着它,以求一睹为快,如果拆毁了将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希望李先生能向本地政府反映,一定要争取将它保留下来,请务必转告!”回到北京后,我在朋友们的鼓动下正式向北碚区区长写了信,建议将雅舍作为重点文物单位保存下来。2013年10月,我打通于昊燕的电话,请她向舒乙先生要一张他在雅舍前的照片,将这段真实的影像,收进梁实秋的书中。但有些照片舒乙先生手头没有,这也许是别人的拍照。有些历史可能就是这样,缺憾才值得回味。过去的时间,变成永恒的历史,我们通过各种资料和档案,进行大量的工作,将历史呈现出来。当时的雅舍,找不到一张照片,梁实秋留下的文字地图,说它的准确位置在半山腰,这是肯定的了。我一阶阶地踏着石磴,向上面的雅舍走去。回味梁实秋的散文,读到他写下的情景。这前面原来不是马路,而是一片水稻田,往远处再望过去,就是绿色茂盛的远山。这里旁边还有高粱地,有大块的竹林,蓄满水的水池,沤泡的粪坑,在房后面是长满荒草和杂树的土山坡。“若说地点荒凉,则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亦常有客到,大抵好友不嫌路远,路远乃见情谊。客来则先爬几十级的土阶,进得屋来仍须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雅舍不算太大,一共有六间房,梁实秋占用其中的两间,吴景超、龚业雅及他们的孩子占有两间,其余的两间,为教育部教科用书编委会代主任许心武和秘书尹石公使用。梁实秋在《北碚旧游》一文中记述雅舍:“六间房,可以分为三个单元,各有房门对外出入,是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刷灰,地板颤悠悠的吱吱作响”。竹篦墙不牢固,门窗关不严实,房子里透风漏气,在里面走动,声音稍大一点,邻居都能听得清楚。“邻人轰饮作乐,咿唔诗章,喁喁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隙处荡漾而来,破我岑寂。”在这个空间中,谈不上舒服性、私密性和封闭性,薄薄的竹篦墙,由竹子和泥土结构一起,各种气息渗透进来。梁实秋排除纷杂的声音,使自己安静。梁实秋对抗空间传播的声音,寻找一块净土,追求化作一行行文字。一到了夜晚,这里便成老鼠的天下,只要灯一熄灭,它们便出来撒欢,四处闲逛起来,梁实秋说是“自由行动”。有时老鼠发坏,推动一两个核桃,顺地板的坡度自上而下溜去,要不跳上桌子推倒烛台,或偷吃盘中的灯油。最可恨的是蚊子,黑暗的蚊子阴险毒辣,根本看不到它的来临,只能听到嗡嗡叫声,在脸前飞来飘去,在人的身体上咬一口。雅舍这个诗意栖居的地方,却是它们横行霸道的场所。重庆的夏天闷热,房子里没有一点风,睡觉人的身上,几乎不遮盖东西,便成了它们的人体盛宴。恐怖的经历是前所未有的“聚蚊成雷”,梁实秋用吓人的“雷”字,给人造成轰炸后,一种悲惨的感觉。一个大师学贯中西文化,伏在简陋桌上写的小品,感染千万读者。他能驾驭文字,面对一群小丑般的蚊子却无可奈何。黄昏蚊子出动,从各个角落里钻出,“满屋里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想象当时的样子,梁实秋在和蚊子的斗争中,不知耗费了多少时间。梁实秋居此陋室,以乐写苦,怡然成趣,真是个“把生活当作艺术享受”的人,显得多么豁达、洒脱,没有表露出忧国忧民的心绪,这毕竟不大合于当时的世情。然而,众所周知,文学作品具有内容的多功能性,所以往往在某一时代不很合乎时尚的作品,在另一时代可能会变得颇为行时。50年代以后,读者和时代的需求已不同于抗战时期,人们希望在紧张的劳作之后,借助一些文学作品来调剂生活,获得娱乐,轻松一下心弦。《雅舍小品》的闲适性,正符合了这种需求,而且它蕴含着丰富的人生经验,能启发读者思考生活、珍惜人生,因而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当然,梁实秋并没有闲适到“不食人间烟火色”,他的散文也没有超脱尘世,仍然不时闪射出时代的折光和现代文明的光芒。其作品中对形形色色世相的讽刺、对人生的杂感、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沉思,无不表现出他的真知灼见。雅舍也有浪漫的情景,一幅展开的画面,感染着人的心情。“‘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我来到雅舍,回味描写的文字,从中发现宁静中的美。重庆多雨,蒙蒙细雨之际,雅舍被水湿包围,有了朦胧的诗意。梁实秋写作累了,推开窗子向外眺望,雾一团团地堆积,吸一口潮湿的空气,看不到几米外的东西。下雨的天气,窗子不能敞开,听雨的清脆声,只能透过玻璃看。雨天的人容易伤感,雨丝愁思一般,牵扯人的思绪走向远方。人的情感脆弱,经不起雨声的折磨。屋顶湿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素然一声而泥水下注,此刻满室狼藉,抢救无及。此种经验,已数见不鲜。“雅舍”之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但洒扫拂拭,不使有纤尘。我非显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来理发,故丝织西湖十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但是陈设虽简,我却喜欢翻新布置。西人常常讥笑妇人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妇人天性喜变之一征。诬否且不论,我是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旁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夹一只茶几。我以为陈设宜求疏落参差之致,最忌排偶。“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对于漂泊的梁实秋来说,雅舍只是途中暂时的栖息,不是归他所有,“仅是房客之一”。雅舍两字一分开,体味字中的意思,突然有一种人生的沧桑。不是苦辣酸甜所能替代,不管怎么解读,正如梁实秋自己说的“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亦分辨不清。”这是一个大问题,简单得一清二白,却是人生的复杂公式,不是什么人都解得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