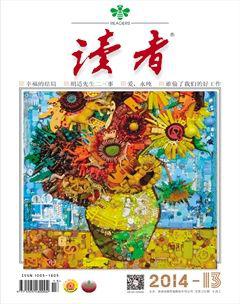就这样老去
闫红
张爱玲的《对照记》里,收入她祖母的三张照片,一张是“如花似玉”的十八岁——“如花似玉”这个形容词,是张爱玲说的,她锦心绣口,不吐陈词滥调,实在是这个被人用滥了的词放在她祖母身上,前所未有地合适。照片上,李家小姐亭亭然站在母亲身边,修长飘逸,眉目清婉,恰如一朵开放在晨风里的白莲花,而她眼角唇边的一抹笑意,“也许是在笑钻在黑布下的洋人摄影师”,少女的活泼忍不住从大家闺秀的矜持下透出来,楚楚动人。
1888年,李鸿章把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了流放归来的张佩纶,张大她十多岁,此前娶过两任妻室,皆已去世,留下两个男孩。
李鞠耦订婚时,已经二十三岁——跟张爱玲遇到胡兰成的年纪差不多,旧时女子到这个岁数,如花已开到十分,李鞠耦还待字闺中,一方面是因为她父亲太看重她,想要多留她几年,另一方面的天机,则由张爱玲在以她姨奶为原型的小说《创世纪》中道破:
姊妹两个容貌虽好,外面人都知道他们家出名地疙瘩,戚宝彝(即李鸿章)名高望重,做了亲戚,枉教人说高攀,子弟将来出道,反倒要避嫌疑,耽误了前程。万一说亲不成,那倒又不好了。因此上门做媒的并不甚多。

如果说,张爱玲是以她的旷世才华外加矜持冷清容易紧张的个性使得自己高处不胜寒,李鞠耦则是因豪门背景变成了剩女,“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怎么着都会有点焦虑吧,现在,一个男人被指定给她,按照张爱玲的说法,她就会去想他的好处。
如果是这样,那么,张佩纶不见得就是一个不可爱的人,他是一无所有没错——两千两银子的流放费用还是李鸿章替他付清的,但李鞠耦这样的千金大小姐对于权势金钱是见惯了的;他的潦倒仕途,与曾经激昂并张扬的生涯参差对照,亦有一种动人之处,仿佛是在人生的跌宕起伏中淬火,一旦回归,就如王者归来。
然而,在张爱玲的《对照记》里,我看到他唯一的一张照片,正是流放归来时所照,非但不像我想象中那么清癯——我总有个偏见,清癯的人才能智慧——反倒有点脑满肠肥之相,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
当初的他,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狂歌痛饮,飞扬跋扈,便是对他还算佩服的李鸿章,私下里亦可以肆意针砭,毕竟他俩一清一浊,并非全然的同道。现在,他官场中箭,落魄归来,投到李的门下,承李不弃,依旧对他高看一眼,还把女儿许配给他,可是,内心张狂如他,如何能扮演一个驯服懂事乖巧周到的女婿?何况李家还有上下人等,不是所有人都有李鸿章的卓越眼光,李家的大少爷李经方就对这位妹夫十分地看不上眼。寄居在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府之中,置身于那样的眉高眼低之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李鸿章有时也会咨询他对于时政的看法,开始,张佩纶还愿意说说,但他很快就发现,他的说法丝毫不能影响李鸿章,他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截然相反。若是在意气风发的过去,这些分歧也许不算什么,他内心的强势使得他能够做到和而不同。而现在,不一样了,他受李鸿章天高地厚的恩,应该扮演好一个优秀的幕僚,提出的主意不被采用,自然有种挫败感,另外一方面,可能还会感到某种耻辱。
他渐渐地沉默了,在李鸿章的府第里,刻意地将自己隐遁,甚至李鸿章的七十大寿,阖府上下张灯结彩,衮衮诸公络绎不绝,连皇上和太后都送来了匾额贺礼,真个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张佩纶却躲在房间里,和李鞠耦下了一天的棋。谁会喜欢这样刻意反高潮的人,除了对他无比欣赏的李鸿章,李家的人很难喜欢这位“古怪女婿”。
最讨厌他的,还是那位大舅子李经方。甲午年间,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李经方跃跃欲试想要挂帅。张佩纶以自身经验知道,李经方也不过是纸上谈兵,一旦上阵,十分凶险。他坚决地向李鸿章提出了反对意见。
这事最后是被搅黄了,李经方的恼怒可想而知,以致有他要“手刃”张佩纶的传言。起码他曾托人到皇上那儿放过水,光绪帝降下旨意,说“革员”张佩纶发遣释放之后,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实属不安本分,要李鸿章立即把他撵回老家去,不许逗留。

李鸿章上折辩护无效,张佩纶只好离开,不过他没有回原籍,而是带着老婆孩子去了南京,“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花遮柳掩的江南,适合栖息疲惫的灵魂,张佩纶自言:从此浪迹江湖。
有很多文人,经历过这样的路途,从“热衷”的朝臣,到淡定的隐士,比如诗人王维,亦有过意气风发的年轻时代,帅哥、才子、状元、高官,站在人生的制高点上,应有尽有。然而,一场安史之乱,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势,他决然地从喧嚣中转身,与山水草木耳鬓厮磨。
张佩纶似乎也想走这条路,他和李鞠耦感情之好是公认的,日记里亦常有两人饮酒煮茶赌棋读画的记载,还合著武侠小说《紫绡记》及一部食谱,虽然在张爱玲眼中,那小说枯燥无味,食谱也乏善可陈,但旧时婚姻,能够如此和谐,已经难得。不过,我总觉得他是在刻意“秀恩爱”,不能够意气风发,那就走风雅闲适路线吧。可是,到底,他也没有因为这美满姻缘而变得快乐强大起来,阴郁的表情,几乎贯穿他的整个晚年。
张爱玲说她祖父母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诗酒风流,“我姑姑对于过去就只留恋那园子,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杏花开了,她母亲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事实上,这宅子原是一座侯府,按现在的话叫二手房。民国时候,刚搭上张爱玲的胡兰成感觉良好,也当自己是个“高干子弟”了,兴头十足地跑去怀旧,却见:
一边是洋房,做过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唯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
这座宅子如今在南京航海职业学校院内,初夏时节我一路寻去,传说中的三座小楼还剩下一座,曰“小姐楼”,挂着“老年活动中心”的牌子,连废池颓垣都已不见,四周皆是崭新锃亮的现代建筑。我去的时间不对,大门紧锁,从木格的窗子望进去,不过是一个个不算很宽敞的房间,也许是后来隔成的。
草草看罢,转身离去,一回头,隔着翠绿的浓荫,看那朱漆斑驳的云头与阑干,在匝地蝉声中一语不发,忽然有一种恍惚,想很多年前,张佩纶是否就站在那云头与阑干之间,望尽斜阳?而他的命运转折点正因为“海事”,旧居如今为“航海学校”征用,也像是命运的讽刺。
张佩纶到底不是王维,他不能像王维那样心如止水。最初的抗拒与低调,未尝不是一种撒娇,只是,当撒娇无人理会时,就可以换一个名称叫作自取其辱。
他后来变得那么冷,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吧,害怕再次被内心的热情灼痛。来到南京的张佩纶几乎不与故旧联络,他的恩师李鸿藻就跟李鸿章抱怨,张佩纶一封信都没有。李鸿章笑笑,其实张佩纶对他这个“恩师”岳父,同样有所保留,李鸿章一度邀他出山,协助自己,张佩纶以避嫌推托,实在躲不过,去了一趟,很快就找个理由溜掉了。我一点不认为他这是淡泊,而是,一个曾经那样恣肆放纵的人,怕是很难心平气和地在别人的帐下听喝吧。他拿得起,却放不下,他勇于抉择,却无法坦然接受抉择的后果。
张爱玲的晚年,同样选择了离群索居,那种心意如铁的坚硬,与乃祖同出一辙。难怪她说,遗传真是神秘飘忽。
1901年,李鸿章去世,对于张佩纶来说,这个世界上最欣赏他的人去了,自己始终没能拿出什么印证他的赏识。张佩纶越发纵酒,当是在月光如水、寒蛩细吟的夜晚,那个胖胖的中年人慢慢地浮上一大白,纵横心事,如脚前枝丫的投影,欲说还休,不说也罢,斟酌处,便是一生。
1902年,张之洞代理两江总督,驻节南京。二十多年前,他俩分别是清流的两只“牛角”,命运却推着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越走越远,如今一个是封疆大吏,声震四方,一个却宦海潦倒,为人笑柄。按照陈宝琛在《张佩纶墓志铭》里的说法,张之洞几次提出要见张佩纶,皆遭拒绝。但也另有一种说法,张之洞为了避嫌,并不愿意在正式场合与张佩纶来往,甚至托人带话,建议张佩纶搬到苏州去,张佩纶断然拒绝,大为不爽。
不管是怎样一种芥蒂,在那个旧历年的年底,得到了消弭的机会,张之洞终于来拜访张佩纶了。
隔着二十年的光阴,隔着一重又一重的往事,还有彼此心中有数的恩怨芥蒂,四目相对的一刻,是否有泪盈睫?故人别来无恙乎?怎能无恙?时间的锣鼓兜头而下,充塞着四周的缝隙,“就谈身世,君(张佩纶)累欷不已”,张之洞这样回忆。
这是一次残酷的见面,张之洞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张佩纶不如意的一生,仕途蹭蹬是其一,而且,他还是那样地不彻底,从热衷到颓唐,从清流到淮戚,他说自己孑然孤立、一无倚著。我想,这倚著,指的应该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体,而是纵然他心高气傲,有所坚持,却还是在湍急的命运中,随波逐流,逐渐迷失了自己。
不是所有人,经过命运的淬火,都能炼成金刚不坏之躯,有的是焚毁,有的是夹生,张佩纶究竟属于哪一种?和张之洞谈话时,张佩纶流露出了生不如死之叹,看来,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皆不能安慰一个负荷太重的灵魂,他在黑暗中的挣扎,越发使自己伤痕累累。
和张之洞分别不久,张佩纶去世,死在大年初七,享年五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