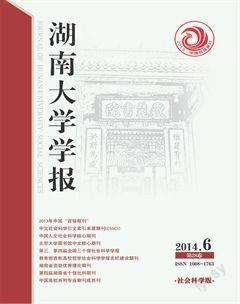香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二元发展路径初探
[摘 要] 自回归以来,围绕香港法治实践的激烈争鸣,可简约为“法治一元论”范式下的形式法治主义者与实质法治主义者之间的博弈。“法治一元论”难以准确地解读法治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利于凝聚港人的法治共识。依循“法治二元论”范式下的香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二元发展路径,既可有效地调和相互冲突的法治观念,又能确保香港法治的良性发展,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
[关键词] 法治一元论;法治二元论;形式法治;实质法治
[中图分类号] D921.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6—0146—08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Dualist Paths of Formalistic Rule of Law and Substantive Rule of Law in HKSAR
GAO Zhong
(Law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China)
Abstract:Since the handover of the sovereignty, there has been heated discussions on HK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which can as a matter of fact be briefly described as the gaming
between the formalist and substantialist theories of rule of law under the paradigm of the monist theory as far as rule of law is concerned, which does not correctly depict the basic mechanism of rule of law, casting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reaching of the social consensus. Following the dualist paths of the formalistic and substantial rule of law can effectively reconcile the conflicting conceptions of rule of law, ensure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rule of law, and guarantee the longterm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n HKSAR.
Key words:the monist theory of rule of law; the dualist theory of rule of law; formalistic rule of Law; substantive rule of law
“法治”这个术语处于一个十分独特的状况。虽然人们对法治的涵义可能持有相异甚至是截然对立的理解和信念,但它仍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正当性的政治理想。[1]这种现象在香港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一国两制”原则和《基本法》的护佑下,开埠以来,港人从未获得过如此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然而,在这种法治昌盛的镜像背后,围绕香港法治理论和实践的争鸣亦可谓跌宕起伏,波澜不断。2013年初始某些香港学者发起的违法争“真普选”,追求“高层次法治”的占领中环运动(以下简称“占中”),更是将法治争鸣推向风口浪尖。香港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和政制改革的关键时刻,理性地界定和厘清围绕香港法治的论争,有利于凝聚港人法治共识,探索符合香港客观实际的法治发展路径。本文试图将香港法治争鸣置于“法治二元论”的分析框架内,在反思和借鉴“法治一元论”在理论和实践上之得失的基础上,提出香港应依循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二元发展路径的对策。香港知名学者、前特区政府高级官员刘兆佳先生从新政权建设、提升特区政府管制能力以利于“一国两制”正确实施的角度,在政治學和社会学框架内检讨过去和寻觅对策。而本文则是从“法治二元论”的视角分析相关问题,亦可谓殊途同归。参见刘兆佳:《回归十五年来香港特区管治及新政权建设》,商务印书馆(香港)2012年版。
一 对香港法治争鸣的解读:认识论
和方法论的反思
按照香港舆论界的惯常表达方式,可将香港法治争鸣视为反对派和建制派两大阵营之间的论战。
本文仅从学术层面概括香港舆论界两类相互冲突的法治立场。如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饶戈平教授所言,在法律语境内,“爱国爱港”即拥护香港回归祖国,拥护及遵守基本法。不论圈内圈外(建制派或反对派),只要符合上述标准即是“爱国爱港”的体现。引自曾钰成:“‘爱国爱港人士不应以阵营划线”,《文汇报》(香港),2014-03-31。反对派的核心立场是:1)“阴霾笼罩香港法治”等观点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行使《基本法》终释权的正当性;2)“民主赤字论”强调,代议制责任政府的缺位和立法会普遍代表性的不足,是特区立法和政策的社会受认性不高的症结所在。唯有尽快实现“真普选”,香港方有“真法治”;3)“高层次法治论”、“有限违法论”等观点将“依法办事”贬为低层次法治,以“恶法非法”为理据,将公民违法求“真普选”视为高层次法治。
建制派的回应则是:1)在香港法治问题上出现种种争拗的主因是,香港社会中一批有较大影响的法律学者、大律师及某些政治团体,不愿接受《宪法》、《基本法》确立的“一国两制”新宪制,总是在重要时刻、重要事件上刻意挑起法治纷争,扰乱港人已形成的法治共识;2)“人大常委终释权”属《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宪制性权力,是对港行使最低限度国家主权的法定要素;3)法治有规矩,公义无准绳。所谓“高层次法治论”是以某种伦理道德哲学为据的“伪法治”观。违法求普选将拆除香港通向政改的法治轨道,使香港步埃及、泰国、乌克兰等国“民主乱象”的后尘。
回归后的香港法治一直主动或者被动地回应着新宪制背景下诸多因素的影响,故各种法治理念获得了竞相争鸣的契机。在“特首普选”步伐日益临近以及政治、法律、民生等争议交织于一体的背景下,香港法治问题更趋复杂化。综合学界已有的理论成果,如“厚”、“薄”法治概念的动态解读方法[2]、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类型分析法[3],可在一定程度上解读上述“各论各的法治”的奇特现象。人们脑海中的法治概念其实就如同一座天平。左端托盘是严格的形式法治理念,右端托盘则是全面正义型实质法治理念。天平向左或右倾斜,形式法治主义或者实质法治主义的倾向就越明显。
但上述分析方法既有长处,亦存在不足。长处是,可将纷繁驳杂的法治理念类型化,从而揭示不同主体在法治判断和评价时出现分歧的主观原因。不足是,描述性有余,规范性不足。因为法治毕竟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事业,直接关涉到法律治理的实效和人民的福祉。法治理念并非纯粹只是学者在书斋里的抽象演绎,而会在实然上影响人们对法律条文、法律现象的理解和判断。某种法治理念一旦处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必定会深刻地影响法治运行和法治建设的基本定位和发展走向。在法理上,建制派观点其实可视为法律实证主义特征鲜明的形式法治观,即倡导“依法办事、司法独立、法律安定性、恶法亦法”的法治精神,主张守法首先须遵守《基本法》,香港政改亦无例外。《基本法》或存瑕疵,但在依循法定程序修订之前仍须一体遵循。反对派观点则可纳入到型谱宽广、自然法色彩浓厚的实质法治理念范畴,即有条件地认可依法办事原则,倡“恶法非法”,强调透过独立、能动的司法保障和扩展个人权利,主张香港普选应依循“国际标准”一步到位,而非固守《基本法》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不愿承认“单一制”国家模式下香港区域法治的内在特殊性。
上述建制派和反对派的立场在本质特征上其实均是“法治一元论”的表现形态——要么恪守一元化的形式法治观,要么倡导某种形态的一元化实质法治观。前者试图克服法律实施过程中实质正义的不确定性“幽灵”,因为“在当今时代,各门各派的观点令人眼花缭乱,对是否存在一个能够获得一致认可的关于良法、善法的说法,我们有时不得不持悲观态度”[4]。该法治理念与香港法治传统和港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守法观念相吻合。后者则以“良法”、“普选”为道德旗帜,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人权普世性的呼声,客观上为部分港民要求“完全自治”、“民主完全西化”、“司法权力中心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其问题是,可能使“一国两制”原则和《基本法》的准确实施始终面临不确定性的风险,损及法律的安定性。回归后不久发生的香港居留权系列案件所引发的巨大的社会、政治风波,即是这种实质法治理念主导下司法能动主义的结果。[5]现实昭示,上述两类相互冲突的法治理念如难以得到有效调和,极可能导致港人法治观念的严重分化,损害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
香港回归以来,公众游行的数量上升6.5倍,即1997年约1000宗游行,2012年约7500宗。集会游行越来越暴力化和激进化,警察执法变得更加棘手。参见“律政司专员:不应利用司法程序达政治目的”,《大公报》,2013-03-21。
部分西方学者如杰弗里·乔威尔已意识到“法治一元论”范式下的形式法治观和实质法治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试图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但却发现困难重重,因为一旦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引入“恶法非法”的理念和实践,仍难避免政治道德哲学和正义理论所带来的两难困境。[6]在中国内地法学界,亦有学者在进行着这方面的反思性探索。葛洪义教授认为,对“恶法非法”理念的倡导,助长了法官批评法律的不正常现象。“法律之善恶需要探寻”是一个危险的理论。仁慈是立法者而非法官的权力。学者、老百姓可以对法律提出批评,甚至说某些法律是“恶法”,以促进法律的修改和完善。但法律部门的官员没有这个权力,他们的职责就是维护法律的权威。[7]刘作翔教授质疑一种比较盛行的观点——“法治经历着一个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逐步迈进的过程,实质法治是法治的高级阶段”。他认为,发达的法治状态应该是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并存。中国当下处在一个动辄就怀疑法律的阶段和环境,这是不利于中国法治良性发展的。[8]上述论断虽然并非直接针对香港,亦未明确点出“法治一元论”范式的实质法治观,但从其分析的视角和立场来判断,却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对实质法治观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亦是值得商榷的。正如张文显教授所言,“法治是一个融汇多重意义的综合观念,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9]换言之,法治这个概念已实然地承载了人们对诸多价值的追求和理想。这既是客观现实,也是无法回避的理论现实。但是,各种“法治一元论”形态的法治理念潜含着“厚此薄彼”、“相互解构”的内在张力,实不利于引导法治的良性运行。正是基于对当下法治理论现状的反思,笔者主张以“法治二元论”为视角,将法治的普适性经验与香港区域性法治的特殊性相结合,寻觅既定制度框架内有效推进香港民主、自由、人权、秩序等价值协调发展的对策。
二 法治二元发展路径的探索:
基于“法治二元论”的逻辑展开
(一)“法治二元论”的核心立场
法治即法律的统治;宪法和法律享有至上权威,是法治与人治最根本的区别。法治二元论者认为,法律的统治既应体现于立法领域(与民主政治相关联)的实质法治,也应彰顯于法律实施领域的形式法治。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属一国或地区不可或缺的两种法治实践活动,即以立法和法律实施所处的两个不同时空为界,立法领域践行实质法治,法律实施领域践行形式法治。两者各有其独立的运行场域和存在价值,依循不同的发展路径。发达的形式法治有利于实质法治的稳健发展;完善的实质法治可强化形式法治的社会受认性,降低其运行时的阻力。政治权利的扩展、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民生福祉的不断提升等多元实质价值诉求属于立法场域实质法治建设的对象,依循由“薄”到“厚”稳步迈进的路径。在法律实施领域则应始终践行以“普遍守法”为核心的形式法治,追求“薄”的价值定位。笔者深知,“法治二元发展路径”的理论模型和纷繁复杂的法治实践之间不可能绝对耦合,但对于那些正处社会、政治转型期的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香港、中国内地、埃及、泰国等,在法治理念和行动策略上,有意识地探寻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二元发展路径,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香港法治首先是香港《基本法》的统治,《基本法》是香港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基石。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划定一条相对明晰的“理论界线”的核心标准应当是在香港有效的法律,其中既包括《基本法》本身,还包括《基本法》第十八条所确认的法律,如立法会颁布的法例、附属立法、基本法附件中列明的适用于香港的全国性法律、司法判例、习惯法,以及司法审判时可供参考的国际人权法理和其他普通法辖区的案例等。具体而言,香港新宪制框架内有权创制法律的主体所实施的法律之立、改、废等行为属于实质法治范畴。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运行领域当属形式法治规管。司法先例的创制以及违反基本法司法审查虽在实然上可能牵涉“法官造法”(或曰“法律发现”),但因其发生于法律适用领域且须受《基本法》和“遵循先例”的约束,故其在本质上仍属形式法治范畴。
如布莱克斯通所言,“只有衡平没有法律,会使每一位法官都成为立法者。這将给人们带来无尽的迷惑。”转引自[比]卡内冈:《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欧洲法律史篇》,薛张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50页。与此逻辑一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有关条文的解释及其做出的相关决定当属新宪制下香港形式法治的有机构成要素。
香港实质法治的基本定位是,应始终秉持多元、宽容、开放的原则,结合香港的实际,为港民广泛的民主参与提供合法的渠道和手段,为政党政治的日益成熟提供制度化的平台,
正如亨廷顿所言,“政治稳定依赖制度化和参与之间的比率。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须随之提高。”[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3-83页。使港人多元的实质正义诉求得以通过合法、理性的对话达成妥协和共识,最终以法律的立、改、废等方式予以确认。通过由“薄”至“厚”的实质法治建设步骤,逐步实现民主与实质法治的有机整合。香港形式法治的基本定位是,在《基本法》及其第十八条确认的各类法律实施过程中,应始终恪守形式法治诸要素,依法办事,维护司法独立,呵护法律的安定性,恪守“恶法亦法”的理念。违反基本法司法审查权以及“人大常委释法权”属于香港形式法治的特殊表现形态,均应依循“谦抑为原则,能动为例外”的实践理性,因为“即使是在普通法系国家的司法审判,所谓正义高于确定性,只是罕见的个案”[9]。其中,形式法治应成为超越港人价值分歧的底线共识。
法治二元论者所强调的香港形式法治并非缺乏“实质”,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就是维护既定规则所确立的实质内容(或者实质正义);而香港实质法治亦非缺乏“形式”,多元正义观念的博弈和整合必须依循既定议事规程和法律程序。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互为前提和基础,两者殊途同归,同构“香港法治”的蓝图。香港回归以来错综复杂的政治、法律问题,实际上可简约为“变法与守法”的实践理性问题。将“变法”视为立法领域实质法治建设的对象,而将“普遍守法”作为法律实施领域形式法治的重心,可找准问题的症兆和解决问题的途径,理性引导舆论争锋,使香港法治始终沿着二元发展的路径稳步前行。
(二)法治二元发展路径的例证
香港舆论界常将新加坡作为比较的对象,但大多限于经济、金融方面的比较和借鉴。新加坡虽然是一个主权国家,但与香港在历史背景上却有许多相似性。如均经历了百余年英国统治,同属英式普通法体系,在发展之初均涉及到英国制度文明的承继与创新等问题。甚至和回归后的香港一样,法治理念的激烈争鸣一直与新加坡建国后的法治发展相伴相随,但其主流法治理念始终支撑和指引着新加坡的法治建设。新加坡主流法治理念及其实践可佐证“法治二元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更为详细的论证,可参见高中:“法治二元论视角下新加坡土地征收低补偿规则研究”,《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12年第12期。
1.新加坡法律治理的核心特点: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二元发展路径
新加坡究竟是否属于“法治国家”,一直是激烈辩论的话题。正方认为,新加坡毫无疑问是法制完备、执法严明、司法独立、行政高效和廉洁的法治国家。[10]反方却认为在新加坡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实施的不过是赤裸裸的法律暴政,是一个除经济业绩外在法治和人权保障上毫无建树的威权主义、法制主义、家长主义国家。[11]笔者认为,“法治一元论”范式的两种主要学说或立场——“法治即形式法治”或“法治即良法之治”——是导致如此截然对立评价的理论根源。这两种学说实际上均难以令人信服地解读类似于新加坡这样的法治后发型国家的制度建设沿革与现状。现以“法治二元论”析之。
在“变”与“不变”之间的理性抉择是新加坡实质法治建设的典型表现。新加坡在宪政构架上承继英国威斯敏斯特体制,即由定期大选产生的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组阁,但为了确保管治效率,抛弃了两院制议会结构。在法律渊源上,延续制定法、普通法皆具拘束力的英国法治传统,但在法律位阶上更为强调制定法优于普通法,以树立国会的至上权威。迅速修订成文宪法,取消人身保护令和陪审团制度等,并在公法领域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新加坡国情的成文法律。这些实质法治建设上的举措为建国初期法律和秩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确保了执政精英的治国理念和大政方针得以顺利地转化为成文法律。随着新加坡社会价值日益多元化,执政者不断改良宪政体制,修订某些备受诟病的“恶法”,使新加坡实质法治建设始终依循“薄”到“厚”的渐进式路径前行。
形式法治所蕴含的诸要素已成为新加坡法律运行过程中的普遍共识。“法律至上”、“依法办事”的观念渗透于行政执法、司法、公民交往等各项具体行为中。以权压法,以言废法,在新加坡被视为背弃法治精神的“恶行”。“司法独立”一直是新加坡政府小心呵护、不敢逾越的敏感红线。新加坡法院高质量的审判水平亦为世人所称道。
“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机构”2008年实证调查显示,香港、新加坡被排在最佳法院制度前两名,而“世界法院评估项目组织”2010年法治测评结果是,新加坡列高收入国家民事审判质量和效率第1名。均源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Judicial_system_of_Singapore#endnote_compliantjudiciary新加坡法官在“民告官”案件审理时确实一直表现出司法克制的立场,即使偶有违宪审查案件,往往采取的是“合宪性解释”的进路,以体现对国会的尊重。这种谦抑主义的司法文化可能会使人感觉新加坡法官过于保守,但在另一方面却有利于判例法与制定法的协调一致,确保法律的安定性和可预见性。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治国经验的论述亦体现了其对法律实施领域践行“恶法亦法”理念之重要性的认识。[13]或如英国法学家戴雪所言,“立法所有妥善性(如合情合理)与人民的中意未必互为因果。”[14](P43)持“恶法亦法”理念者其实并非必然在良知上认同这些“恶法”,而是强调法律一经制定和生效,就必须尊重和服从,非经正当程序,不得损害其权威。这种主流法治理念及其实践深刻地影响着新加坡民众对待法律的态度,强化了法律“定纷止争”的功能。
在法治二元论者看来,新加坡形式法治发达但某些领域的实质法治建设则相对滞后,如公民经社文权利的保障很到位,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等方面的政治自由则显不足。这确实是客观事实。但新加坡所采法治二元发展路径,仍有可借鉴之处。其一,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始终遵循形式法治,避免了政治与法律“两张皮”而执法、司法和守法者无所适从的困局;其二,在立法领域的实质法治建设过程中通过定期的民主大选和人民行动党占多数议席的优势,有步骤地不断吸收和整合各种实质法治主义思潮的影响。换言之,执政党、反对党乃至海内外舆论对法律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仅局限于实质法治场域。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各司其职,泾渭分明,彼此形成强大合力,共同推进新加坡法治和政制的改良和完善。
2.港英时期法治:与新加坡法治模式的比较
假定代议制政府的产生和法律的制定均存在民主的缺失,不符合法治一元論者(如实质法治主义者)的“良法”、“良政”判断标准,那么港英时期法治亦难以被视为“真法治”。但令人费解的是,许多反对派人士仍将港英时期法治奉为理想模式而倍加赞誉。暂且不论这是否涉及双重标准,至少理性地看待港英时期法治,对客观地解读回归后的香港法治是有意义的。
港英时期,英国政府将英式普通法体系和香港当地客观实际相结合,使英国法律文化中“法律至上”的法治传统、“依法办事”的政府运行原则和“司法独立”的法治要素在主要由华人构成的香港社会生根发芽。客观的状况是,回归前的香港确已具备极其发达的形式法治体系。就该时期的实质法治状况而言,自上世纪70年代始,为了调和针对英国管治风起云涌的阶级矛盾和挑战,数任香港总督通过推行委任制的方式,逐步吸纳华裔精英人士参与港务管理,同时在制定法层面加大了对港人民生福利的保障。但如果将民主普选和代议制责任政府视为实质法治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那么回归前的香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其实质法治无疑是相当滞后的,远不及建国之初即已具备“一人一票”定期普选的新加坡。这应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中英联合声明》(1984年)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0年)的出台,实际上为回归后香港新宪制下的实质法治和形式法治奠定了国际条约和国家宪制性法律的双层保障。例如,不仅保留了香港已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港人生活方式,而且规定了一系列创新性实质法治举措,如赋予香港特区司法终审权,保留普通法制度,进一步扩展了港人基本权利和自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在《基本法》中载明,行政长官的产生根据香港特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回归前香港法治的特点可简要概述如下:形式法治发达,实质法治有较为充实的内涵却存在相对滞后性,但《基本法》已为回归后实质法治的飞跃性发展提供了契机。
不过,受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香港在回归前夕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动态。例如,末代港督彭定康绕过《基本法》,迅速推进政制改革,将原来的九个功能组别选举改为直选。通过修订《英皇制诰》等港英宪制性文件,为违宪审查提供了创设司法先例的机遇。港英时期的这些作法事实上扰乱了回归后稳步推进香港实质法治的《基本法》原意,强化了部分港民加速推进政制改革的预期。而回归前的数起涉及“违宪审查”的判例则预埋了回归后形式法治场域制定法与判例法相冲突的种子。回归后不久,司法审判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诸多社会运动和政治力量竞相博弈的角力场,这即是佐证。
综上,独立建国后的新加坡和回归前的香港均可被视为全球形式法治的典范。回归后的香港虽然言论自由、示威自由异常发达,但整体良好的社会秩序恰恰彰显了香港形式法治极强的抗震性。仅此而论,新加坡亦难与其媲美。但在实质法治方面,新加坡政党政治无疑更显成熟,
关于政党政治于现代政体的特殊意义,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3页。其实质法治运行机制整合多元价值诉求的功能更强。新加坡实质法治建设的经验值得香港借鉴。
三 香港法治二元发展路径:形式法治的
坚守和有所侧重的实质法治建设
(一)恪守形式法治:以“普遍守法”为核心
《基本法》赋予港人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但仅规定了一项基本义务——遵守法律。故以“普遍守法”为切入点,对香港形式法治进行扼要分析。“普遍守法”在概念上包含了两重含义。其一,所守之法的普遍性,即《基本法》及其列明应遵循的法律。遵循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终释权”对《基本法》相关条款作出的解释和决定,以及香港特区法院的生效判决和裁定,是守法的应有之义。中国宪法本身亦蕴含了港人不得作出有损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行为的“不作为义务”。[15]其二,守法主体的普遍性,即守法主体既包括广义上的特区政府(含行政机关、立法会、法院)及其官员在内的在港人士和各类组织,还包括了中央及各有关机关在处理涉及香港和内地之间事务时对《基本法》的遵循。只有将“普遍守法”贯穿于香港形式法治运行的全过程,彰显于依法办事、司法独立、“恶法亦法”等价值定位中,香港形式法治方能得到有效的维护。香港法治争鸣实际上均涉及到对“普遍守法”的准确理解问题,而理性地把握以下六大关系则是关键所在。
第一,《宪法》与《基本法》。《宪法》是中国的根本法、母法。《基本法》虽然是香港重要的宪制性法律,但仍不宜视为香港“小宪法”,而应是《宪法》派生出来的子法。这既符合中国法律的整体构架和效力层级,亦有助于澄清和避免“小宪法”这个称谓滋生出的误解或误读。
第二,“全国人大常委终释权”与“香港司法终审权”。
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梅思贤爵士(前澳大利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曾撰文对“终释权”和“终审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辟分析。See Sir Anthony Mason:The Rule of Law in the Shadow of the Giant: The Hong Kong Experience,623 S.L.R.,v.33,2011,623.这两项权力均源自《基本法》,是香港形式法治的核心构成要素,对其中任何一种权力的否定或抵制既不理性亦非守法的体现。获得宪制性授权的这两大主体均应恪守《基本法》第158条之规定,各司其责,共同捍卫香港的形式法治。迄今,全国人大常委对“终释权”的四次行使是极其审慎的,在操作上亦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终审法院两任首席法官明确强调,司法终审权在新宪制框架内得到了有效的维护。[16]但一些香港人士以维护香港司法独立及法治的名义对“全国人大常委终释法”始终持排斥、敌视乃至对抗的态度。在香港政治和法律领域,之所以风波和矛盾不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形式法治这个底线性共识始终处于摇移不定状态所致。“全国人大常委的终释权”的依法行使有利于宏观地调控香港政制改革的稳步前行,确保《基本法》的正确实施。这是中央依法治港,确保香港法治有效运行不可或缺的法定要素。
第三,港人“民主愿景”与“守法底线”的坚守。追求平等及普遍的选举是港人的民主愿望,符合政治文明发展之大趋势。但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不应以抛弃“普遍守法”为代价。唯有恪守此形式法治底线,方能使特首普选和立法会议员的普选始终依循法治的轨道稳步前行,因为“基于所谓正直及重要的目的而破坏法律”是不可取的反法治之举[14](P24)。一旦既定规则被抛弃,香港形式法治将面临巨大压力,更难保实质法治的良性发展。泰国、埃及、乌克兰在近年出现的民主乱象(如“街头政治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形式法治未能得到坚守所致。
第四,立法监督与议员守法。立法会肩负着制定符合《基本法》的法律条例和监督特区政府依法行政的宪制责任。立法会议员遵循议事规则,理性、和平地推进法律的完善,可向市民传递尊法、守法、“循法而变”的正能量。遗憾的是,迄今仍有一些议员屡次通过暴力示威的违法方式激进地推行己见。这种现象看起来似乎很民主,示威自由似乎得到了张扬,但却背离了“普遍守法”的精神。此风日盛则香港形式法治堪忧。正如哈耶克所言,“如果所有未实现的欲望都真的可以变成向社会提出要求的权利(掩饰为社会正义),那么个人责任将不复存在。”[17]
第五,政府公信力与官员守法。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以行政长官为代表的特区政府公信力既依赖于不断完善的民主政治运行机制所形成的社会受认性,亦离不开包括特首在内的问责官员和一般公务人员对“依法办事”原则的遵循。例如,近几年香港媒体热议的牵涉某些官员的“僭建风波”,虽有某些人因政治动机而小题大作、刻意搅局之嫌,但在客观上却是对“官员守法”的提醒。在表达自由高度发达的香港,公务人员(尤其是问责官员)极可能不经意地滑入“不守法”的状态而成為政治抨击的靶子。政府形象和问责官员的公信力树立不易,但因违法等原因丧失公信力则可能是顷刻间。
“依法办事”原则在某些领域仍有待加强的例证,参见“承诺10日必复 食署67%个案食言”,《文汇报》,2012-11-15;“海关知识产权懒执法 逾半5年未结案”, 紫荆网,2012-11-15,http://www.zijing.org
第六,司法独立与法官守法。香港回归后的司法独立在国际社会享有盛誉。法官依法独立审判,不受政府、舆论的左右,一直是香港法官群体的座右铭。运行良好的独立司法机构离不开法官对法律的坚守,而法官应守之法首先应当是《基本法》。对《基本法》条文的恰当解释和适用,是法官守法的实然体现。如缺乏对“一国”宪制构架和法律体系的整体把握,难免会在维护“两制”时误读《基本法》,作出与其原意相悖的误判。上文提及的香港法治争鸣,在背景上与司法能动主义色彩明显的数起判例显然是存在关联性的。《基本法》确保了普通法制度在香港特区的延续,但该普通法已演变为新宪制下的普通法,而非港英时期普通法制度和理念的简单复制。法官在个案审理时应当逐渐适应和吸收大陆法系司法解释原则和技术中的有益成分。事实证明,司法克制的实践理性和“合宪性解释”司法审查进路,在香港语境下有利于维护立法、行政、司法三者间的均衡。可见,法官守法,于香港法治有着不同寻常的建构性意义,因为“法律条文某种程度上与各种宗教的教规一样,不能逾越。这是法律人对法律虔诚、保守和谨慎的体现。法律人当然并非只是被动地诠释和执行法律,他亦能动地改变法律。立法的全部过程也就是法律制度变革的全部过程”。[18]
(二)推进实质法治:“变”与“不变”的理性平衡
香港实质法治是整合政治社会的现实运行和公民社会的政治理想之间冲突的制度性平台。如上文已述,香港回归前的管治历史和回归后的客观实际均显示,在质和量两个方面提升香港实质法治,有利于提高特区政府的社会受认性,确保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而欲稳步推进实质法治,应将“变”与“不变”的理性平衡贯穿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民主、民生与法治。民主与法治是否存在相关性,是仁智各见的问题。但经验已证明,没有法治保障的民主往往导致社会、政治的严重脱序,而缺乏民主的法治也难以确保长久的社会受认性。因此,制度化建设的速度应当和民众参与国家治理的程度相适应。法治二元论者认为,民主的制度化正是实质法治建设的重心之一,至于制度化的民主成果能否得到落实则依赖于形式法治的保障。香港政改的核心宗旨是不断扩大港人选择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既然是政制改良,就应当在现有法律基础上求“变”,而非推倒重来或援引臆想的规则。正如香港知名学者丘成桐所言,只有在政府不代表民意,像希特勒或前苏联情形一样出现很明显地压迫人民的状况,民众方能不守法。而特区政府实施的并非独裁政治。
丘成桐先生实际上是针对“高层次法治观”的正面回应。参见丘成桐:“学者不应鼓动学生犯法”,大公网,2013-06-17,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3/0617/1694518.html固守有违《基本法》的政改立场,以求一蹴而就地达至香港民主化目标,
其中,韩大元教授的立场可视为内地宪法学界的一种代表性观点。参见“韩大元:普选方案不能够绕过提名委员会”,2014-03-16,星岛环球网,http://news.stnn.cc/hongkong/2014/0316/76737.shtml在思想自由、表达自由的层面,当然无可厚非。但从有效协商和沟通来看,却可能耽搁制定“普选”的具体规则这项更为紧迫的任务,即所谓“两利相权,应取其重”。
草根阶层的民生问题与民主、法治息息相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的长期浸染下,香港虽属全球最自由的经济自由体,但在保守财政理念的制约下,特区政府在民生立法和政策实施力度上确实不尽人意。房价过高、贫富悬殊等问题使特区政府的受认性面临严峻挑战。无论是从壮大“爱国爱港”力量或是确保法治的德性得以彰显的视角来判断,民生福利制度在质和量上予以提升应成为香港实质法治建设重心之一。
其二,《基本法》的修改问题。《基本法》是香港回归前制定和通过的。当时,如何践行“一国两制”这项全新的事业并无成型的经验可循,但《基本法》最终文本依然汇聚了内地和香港各领域精英的智慧,是充分协商和讨论的结晶,其文本质量和实施效果有目共睹。当然,某些条文或存瑕疵,也是难以避免的。就此,存在着两种对立性观点。一种观点是,《基本法》存在着某些不利于“两制”和“港人治港”的模糊性规定,故应尽快修法。法随时变,即使来不及修法,但至少应按照不同的时代背景来理解和适用《基本法》,方是高层次法治的体现。另有人则认为,《基本法》授予香港特区自治权过大,确保“一国”最低限度管治权力(包括司法主权)的规定明显不足,应通过修法予以完善。更有学者认为,应在《基本法》附件三增列“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基本法》有关条文的解释”作为在香港实施的全国性法律,藉此一劳永逸地解决不必要的政治、法律争拗。暂且不论宪制性法律在修改程序上的复杂性和耗时性,即使单就应修改的内容而论,在香港当下政治争拗不断的情形下,欲达成大致共识亦绝非易事。因此,暂时搁置修法争议,将有限的智识资源集中于2017年“特首普选”和2020年“立法会议员普选”,无疑是香港实质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
其三,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港人的基本权利。落实《基本法》第23条之立法(即制定《香港安全条例》)是香港特区政府肩负的宪制责任。在2003年前后,特区政府曾试图推进该项立法但却在立法会最终表决时遗憾地搁浅了。之后,推动第23条立法演变为特区政府不敢轻易触碰的“烫手山芋”。客观而言,以立法方式維护国家主权和宪制安全是各文明国之通例,作为“一国”之行政单元的香港更不应有例外。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就已经形成共识,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自行立法,以期实现《基本法》所确认的港民基本权利与国家安全保障之间的理性均衡。在2003年立法咨询过程中其实也已有充分的酝酿和沟通,最终提交的法律草案实际上兼顾了国家安全和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是具备社会广泛共识的文本。可见,在民主社会,通过持续性的商谈对话,再复杂、敏感的法律议题,也并非不能达成妥协和共识。欲稳妥推进香港实质法治,应当在第23条立法问题上“脱敏”、“去魅”,适时重启立法咨询程序。
[参 考 文 献]
[1] David Clarke.The many meanings of the rule of law[A].Kanishka Jayasuriya, ed., Law, Capitalism and Power in Asia[C].New York: Routledge,1998.
[2] Brian Tamanaha. On the Rule of Law: History, Politics, Theor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91.
[3] P. Craig. Formal and Substantive Conceptions of the Rule of Law: An Analytical Framework[M].Public Law,1997.467.
[4] (比)卡内冈.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欧洲法律史篇[M].薛张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24-153.
[5] 高中.合理期待规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确立和适用——以2002年至2012年的典型案例为分析样本[J].法商研究,2013,(02):58-69.
[6] J.Jowell. The Rule of Law Today[A].Jeffrey Jowell and Dawn Oliver (eds).The Changing Constitution[C].Oxford,1994.71-77.
[7] 葛洪义,冯善书.关于司法改革的对话[N].南风窗.2010,(13):15.
[8] 刘作翔.不能把形式法治看得太低[N].北京日报,2012-12-24(04).
[9]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532.
[10]高中.法治二元论视角下新加坡土地征收低补偿规则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2012,(04):50-63.
[11]吕元礼.新加坡为什么能:和谐社会是怎样建成的[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扉页.
[12]蔡定剑.新加坡模式不值得中国借鉴[N].河北青年报,2010-11-30(05).
[13]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中国对外贸易总公司现代出版社,1994.157-169.
[14](英)戴雪.英宪精义[M].雷宾南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15]郝铁川.香港基本法争议问题述评[M].香港:中华书局,2013.1-10.
[16]茹志俊.香港司法独立坚若磐石[N].大公报,2013-01-15(A10).
[17](英)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112.
[18]江平.法律人的守与变[N].法制日报,2014-03-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