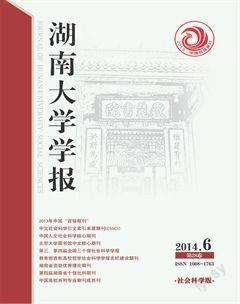时间观流变与当代西方文学发展趋势研究
于红冈
[摘 要] 时间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文学的发展深受时间观流变的影响。当代西方文学作品里出现了大量常规逻辑不可能出现的时间构架和意象,产生了循环叙事手法、意识流写作手法及死亡叙事等不同文学叙事手法。其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时间发展直线与圆的统一,时间感受主体与客观的统一,死亡与永恒的统一。
[关键词] 时间观;西方文学;叙事手法;对立统一
[中图分类号] I10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6—0118—04
Study on the Rheological Concept of Time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ture
YU Hongga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China)
Abstract:Time is an eternal theme in litera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rheological time concept.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ture emerged a large number of time frames and images which are impossible in conventional logic, and different literary narrative techniques come into being, like the circular narrativ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writing technique and death narrative. Its development trend is embodied in the unity of liner and circle time development, the unity of subject and object of time perception, the unity of the death and eternity.
Key words: concept of time; western literature; narrative techniques;unity of opposites
时间一直以来都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对象,它无处不在却又缥缈虚无,看不见,摸不着,因此时间常常被人们比喻成沙漏、落花流水、环形监狱、迷宫等,这些比喻形象地描绘了时间的特性。时间同时也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每当哲学界、科学界等不同领域对时间作出新诠释时,文学界便会吸纳新定义使其融入文学创造中,文学作品往往利用不同的时间观和时间意象来传达作家的真实创作意图,20世纪西方文学中出现了与“时间”密切相关的新的文学叙事手法。
在早期乃至中世纪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反映时间主题时突出的是神与人的对立关系,通过时间的传统意象传播了“神”的强大意志, 时间的妖魔化加强了人们对生命与自然的赞美以及对青春的消逝与无常死亡的恐惧和悲伤。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文学则体现了时间可以延长及轮回的唯心主义时间概念,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反映了时间“线性”发展的特性,同时又反映了时间“循环往复”的特征。进入20世纪,受爱因斯坦“时间膨胀”论等观点影响,人们最终认识到时间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抽象的自然存在物。时间这个无所不能的“神”一旦被否定,更多的作家认识到时间能够魔幻般的创造合成,文学的线性时间流可以被随意切断,时间主体与周围世界有无限可能的关系。[1](P158)
20世纪中后期, 西方文学作品里出现了大量常规逻辑不可能出现的时间构架和意象。其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灵活改变客观时间长度和顺序,通过时间发展直线与圆的统一,时间感受主体与客观的统一,死亡与永恒的统一,把时间的悖论性特质呈现出来。
一 时间发展直线与圆的统一
文学创作中时常出现将时间表征为流水的意象,暗指时间流逝一去不返的直线式发展。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种考虑社会变迁问题的思维方式让历史直线论者认为每件发生的事情均由一条必然的因果链所决定。时间的直线式发展意味着时间是一种永不停息的线性的单向运动,时间往往被认为有始有终,不断流逝,一旦消逝便无法挽回。就如同人的一生,从婴孩呱呱落地,青春和美丽转瞬即逝,很快就要面对死亡的必然。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就汲取了这种生老病死万物枯荣始末分明的时间表达方式。
时间的表征又可以体现为圆弧式循环运动。古埃及人用衔尾蛇的图像来表达宇宙中不可捉摸的时间之谜,他们将时间画成一条羽蛇,蛇嘴衔着蛇尾,周而复始永不停滞地流转着[2](P13)。无独有偶,在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中,时间也是循环往复的,比如古时候人们用天干、地支相配组成历法以显示阴阳五行大地五气的变化,每60年为一个循环周期。轮回式的时间观念将时间看作是迂回的和可重复的,时间始终沿着自身运动的永恒周期做圆弧式运动。时间的变化协调于自然状态,如昼夜交替,四季变化,农时更替,都是时间的圆周式发展。倘若我们回顾历史,就不难发现,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是一个又一个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圈。正如柏拉图的“人世轮回”思想,人类一次又一次被洪水和其他灾害所毁灭,只有一小部分人存活下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一次又一次从灭亡中恢复,人种数量不断的增加,文明得以不断的延续和发展。历史周而复始,不断循环,这就是典型的历史循环论。[3](P72)古希腊诗人荷马在《伊里亚特》第六卷描写了人类与绿叶等植物一代出生一代凋谢的相似性, 人生如同樹叶的萌芽和枯亡,新的一代崛起,老的一代死去。
循环轮回式时间观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更为久远。早在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历史学家赫西俄德就曾阐述过历史循环往复于五个阶段:社会平等、安逸、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黄金时代”到人性堕落、战争不息的“铁器时代”等。其后,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也将人类世界描绘成了一个世间万物在某一天回归伊始重头来过这样的轮回。19世纪爱尔兰文学家威廉·巴特勒·叶芝在他的多部诗作中描绘了特洛伊古城一再燃烧的轮回场景。20世纪,英国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小老头》等通过一个老头子的独白描绘一种空幻的感受,体现了齐始终、等生死的时间轮回的定义。[4]
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学开始呈现出时间观上纷纭复杂的直线与圆的纠缠态势。20世纪西方最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就在其理论著作《批评的剖析》中提出“文学循环发展论”。他从自然界的循环往复中派生出四种文学叙事类型:喜剧、浪漫故事、悲剧和讽刺,并将每一种叙事类型与春夏秋冬相对应。正如冬去春来一般,讽刺文学发展到极端之后又将出现喜剧文学。文学意象的循环和文学叙述结构的循环是弗莱“文学循环发展理论”的基础,但是弗莱也曾强调他所说的循环不是简单的周而复始,而是螺旋式上升,是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阿根廷当代杰出小说家博尔赫斯大胆尝试循环叙事手法,创造了一种新的写作流派宇宙主义,也被称之为卡夫卡式幻想主义。在博尔赫斯关于时间命题最直白的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里,空间上小径分叉交错的花园隐喻着时间这个无形的迷宫,道路错综复杂,出路扑朔迷离,但是多种可能性并存。小说《交叉路径的花园》才是一座真正的迷宫,其谜底就是时间。[5] 博尔赫斯强调时间的非线性,而好比一张结构复杂的关联之网,其中每一个结点既是一条路径的结束又是另一条路径的起点,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重叠、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体现这一时间观流变发展趋势的文学作品还包括美国作家阿兰·莱特曼于1992年发表的小说《爱因斯坦的梦》。在该部小说中作者借助爱因斯坦的名字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时间问题的玄思,他利用物理学上的一些说法,搭起三十个时间世界——比如在某个世界里,因果错乱,将来和过去纠缠不清;而在另一个世界里,时间则完全倒流,人们度过老年之后再回到童年;再或者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相连,人停留在生活的某个时刻动弹不得……整部小说以时间为主人公,以时间的流淌为主要情节,展示了时间的无限可能性。在这个关于时间的多维世界里,莱特曼以一位哲人的眼光,对时间反复地品尝回味。[6]
直线式和轮回式的不同时间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看法。其实,就人的一生来说, 没有纯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现在和将来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托、相互转化。过去发生的事情不会完全消逝, 而会延绵伸展到现在甚至是将来。人作为个体短暂的一生虽然表现为直线发展,有出生就会有死亡,但另一方面, 人类生命之潮犹如浪涛般,潮起潮落,后浪推前浪。生命代代相沿,生生不息,这又揭示了时间呈圆周式循环往复的特质。现实生活与文学作品中个体生命的变化与整个人类生命的繁衍都体现了时间发展直线与圆的统一。
二 时间感受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人们所说的客观时间其实就是地球时间或自然时间,也称为物理学时间。该时间观的典型代表牛顿认为时间是绝对的,时间可以用来测量和计算地球上普遍的物质运动,包括人的生产、生活和人的生命。古希腊人是时间测量概念的创造者,他们以天体的空间位移作为时间的存在形式。毕达哥拉斯学派说“时间就是天球”,柏拉图说“时间是天球的运动”,人类依据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和自转的周期来计量客观时间,显示时间的自然推移和变化。客观时间具有纯粹的自然性,无存贮性和无替代性。客观时间的顺序和延续过程不受人的影响,完全是按固定的节奏机械地、必然地进行,永不停息。
主观时间则不然,它关注时间内的具体经过,强调人们在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情感和直接经验。因此,主观时间由于人的认知和体验不同,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时空观把人类的先天感官形式作为时空感觉的生理基础。他认为时间是人类先天内感官的形式,内感官是内心借以直观自身或者他者内部状态的。[7](P6-10) 法国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也在此理论基础之上,提出直觉主义和心理时间学说。他认为客观时间忽视了时间的流动性,用钟表和日历上的标准单位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牢牢锁定。事实上,时间川流不息,过去、现在和将来相互交错,互相渗透,彼此没有绝对的界限。柏格森提出时间的本质特性是“绵延”,在我们的意识深处,“绵延”才是真正的时间。[8](P65-71)
对“心理时间”的探讨正好迎合了西方文学发展的“内转”倾向,為当代意识流小说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理论依据。随着工业文明的持续冲击,异化程度加剧,资产阶级理性主义逐渐为非理性主义思潮所取代。当代人试图通过突破传统现实主义描写方式和客观物理时间的规约,来表达人类的复杂心理状态和内心世界。深受柏格森直觉主义心理时间影响,20世纪意识流创作大师弗吉尼亚·伍尔芙和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还有法国的普鲁斯特等创作意识流文学作品的作家,他们着力描写人的内心世界,从此意识流小说走向世界,形成了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一个分水岭。伍尔芙以此成功创作了《墙上的斑点》、《达洛威夫人》、《到灯塔去》等意识流代表作品。普鲁斯特创作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没有激动人心的情节设置,没有时间叙事连贯性,在故事中经常插入各种议论、感想和人物内心世界剖析。詹姆斯·乔伊斯创作的《尤利西斯》也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作品。小说描述了一位苦闷彷徨的都柏林小市民,广告推销员利奥波德·布卢姆于一昼夜之内在都柏林的经历,乔伊斯采用意识流手法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凌乱交错的时空。其他重要的意识流作家如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也深受柏格森的“心理时间”学说影响,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表现的就是人被囚在时间里面的那种不幸。[9]
之后当代西方作家们纷纷将意识流写作手法作为小说创作的基本手法,把笔触转向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采用幻觉、梦境、自由联想等手段来体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在意识流小说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流动,互相渗透,不可分割。过去渗透在现在之中,现在又蕴涵了将来,每一个片段都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米歇尔·布陶在其小说《变化》里描写了主人公从巴黎乘火车去罗马时在车厢中所度过的20多个小时所发生的事,故事并没有按照客观事件的线性推移进行讲述,而是通过短短20多个小时内主人公内心意识活动,展现了他过去20余年的私人、家庭生活过往以及他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设想。
后现代主义作家继承了这种反传统的文学实验,其创作更趋于人本主义描写。他们更是将文本描写的任意性和不连贯性发挥到了极致,以期展现人类理性沦为科技理性,人们的生活状态更加混乱、矛盾加剧、社会极端化、片面化和畸形化等社会现实生活困境。因此,后现代主义西方文学创作强调其写作和阅读行为的随意性,如约翰逊写的活页小说,就可以让读者去任意安排拼凑阅读的次序,无论读者从哪一页读起都可以,小说以简短的片段和章节组成,而各个片段之间相互独立,互不衔接。
然而,意识流创作和后现代主义写作手法的大量运用,并不是说明“主观心理时间”可以完全取代客观物理时间。20世纪现象学学派创始人胡塞尔在他的“描述现象学”中阐明非本真的客观时间是如何受到本真主观时间决定的,或如何因此而得以可能的;因而得以首次在现象学领域完成了对主客观时间关系的确立[10](P20)。他提出的一些分析方法,对20世纪初以来的西方哲学与人文科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即便如此,胡塞尔因其在现象学中的先验唯心主义与彻底主观主义的立场、观点而不断受到批评与质疑。意识流小说旨在告诫世人单调、线性推进的钟表和时间观念,使人与直接的生活经验相剥离,因人而铸就的矢量时间的格局使人与自然走向岔路,最终导致主体与客体相分离,主体不断地异化。意识流作家超越了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的简单二分,实现了理性的外部客观时间与感性的内部主观时间和谐统一,呼吁处在客观时间异化状态下的人类需要意识到自身的不完整性,在时间坐标网中紧紧攫住意识的碎片,并令其折射出智性的灵光。[11]
三 死亡与永恒的统一
美国作家阿兰·莱特曼曾在其小说《爱因斯坦的梦》中设想了一个人类长生不死的世界。岁月悠悠,什么都能完成,什么都可以等待。但是这样的生命无穷无尽,每个人也会有无数的亲戚,一个人无论要干件什么事,先得征询父母、祖父母、列祖列宗的意见。长生不老是如此代价,谁都不能独立自主,谁也不自在。到后来,人们想通了,要想活,唯有死。就这样,有限战胜了无限。[6](P25)
这种对于时间生命的思索体现了西方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在死亡中认识生、在身处绝境之时体悟绝对自由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者特别重视时间之于人的存在的意义,保罗·蒂利希认为时间是人类存在无法摆脱的焦虑:“焦虑就是有限,它被体验为人自己的有限。这是人之为人的自然焦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的自然焦虑。”[12](P36)克洛诺斯·萨图恩就曾经使用食子的神话来表示时间,意喻时间会吞噬自己生出来的东西。而古希腊人将希腊神话中的克罗诺斯当作时间老人,因为这个巨神用一把镰刀阉割了自己的父亲。罗马人的时间之神,他手握一把用以收割的长柄大镰刀,象征着死亡[13]。所以,镰刀作为时间的意象,经常出现在各种诗歌和小说之中。时间慷慨地给予人类最美好的东西,同时又显示了巨大的破坏力,世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会被时间吞噬, 被时间无情地破坏和摧毁,它能让一张青春的脸渐渐布满皱纹, 让健硕的躯体逐渐萎缩而丧失活力, 最终悄无声息地消灭人的生命。对生存状态的焦虑来自于人类感受到自身存在的有限性。时间无时无刻地向人们昭示着死亡的在场,生命的有限性给个人生成赋予了绝对的意义。
纵观西方文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死亡叙事的特质。探寻死亡与存在间的紧密联系是文学无可回避的主题,亦是文学审美的要津。人生是五彩缤纷的,死亡因其方式的不同,也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诸如献身性死亡、灾难性死亡、预感性死亡、偶然性死亡、新生性死亡、保护性死亡、抗拒性死亡到生存性死亡。哥伦比亚当代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其代表作《百年孤独》中就采用了大量的死亡叙事,霍·阿·布恩蒂亚在杀死嘲笑自己的人后,为了免遭被害人的鬼魂困扰,不得不远走他乡,最后被绑在栗树上孤独地死去。阿玛兰塔整天为自己织着尸衣,孤独地等待着死神的召唤。在一场香蕉工人罢工运动中,政府下令机枪向罢工人群扫射,霍·阿卡蒂奥倒在了血泊中。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堆尸体上。透过些许微弱的光线,他看见了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尸体塞满了一节节火车车厢,之后像废弃了的香蕉被扔进了大海。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仅用这些纷繁复杂的死亡方式呈现了死亡叙事的多样性,还对死亡叙事进行了“陌生化”处理,如霍·阿卡蒂奧被枪杀后,他的鲜血从门下溢出,淌过客厅,流到街上,最后竟然奔流起来。吉普赛人梅尔加德斯病死后,尸体被抛入了大海。不久因无法忍受死亡的孤独,他回到人间,却又再一次淹死在河里。[14]
正因为有了对死亡的恐惧,才使得人们更强烈地追问生命的意义。因此,只有在死亡中,当每一个时刻奔向死亡,才意味着此在通过自我,这才能绝对地说“我在”。所以,文学作品借由死亡叙事警示我们:没有死亡的生命本质上不是生命, 死亡才是个体生命和生活的最终确认,只有死亡才能证明活的价值和意义。没有死亡,我们便不会为生命的短暂而忧虑,不会意识到生命的可贵和脆弱,不会为自己的努力付出而得到的收获而喜悦。文学对时间、生命和死亡的犀利反思,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15]
自古以来,死亡与永生一直是世人思索的命题,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时间是宇宙的重要构建,也是衡量生命长短的尺度。人生是如此的短暂和脆弱,这种生命危机感又进一步转化为对死亡的焦虑和感伤。人类生命的有限和无限实质上就是对限制与超越问题的探讨,死亡与永恒的矛盾二重性,让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死亡中悟出永恒。死亡与永恒的悖论辩证地统一存在,死亡是一座必须跨越的桥梁,只有通过它,才能达到永生的彼岸。
“時间”本身就包含了无数的“悖论” 特征:比如“循环—直线”、“主观—客观”、“有限—无限”、“死亡—永恒”等,当它们同时以某种形式呈现于文本中时,揭示的正是时间最深刻的本质。每一次矛盾着的双方冲突较量、迸发出的火星都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永恒命题。时间观念的相悖,使文学具有了对立统一的审美张力,借此不同的方式分割和组合时间成为了当代西方文学中普遍实践的艺术。有限与无限、死亡与永恒之间的冲突,造成“陌生化”效果,引领读者不断的思索时间和生存问题。
[参 考 文 献]
[1] 韦虹. 西方文学作品中时间概念的嬗变[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11,(2):75-79.
[2] Henry Estienne.Art of Making Devices[M].Translated by T. Blount, London,1646.13.
[3] 柏拉图. 法律篇[M]. 张智仁,何勤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72.
[4] 刘丹妮.文学与时间:文学作品体现时间定义的三次转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9-21.
[5]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M].王永年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6] 阿兰·莱特曼.爱因斯坦的梦 [M]. 黄纪苏译, 桂林: 接力出版社, 2005.
[7] 李琍.论康德的主体与时间[J]. 江西社会科学,2002,(6): 6-10.
[8] 谭裘麒.唯有时间(绵延)真实柏格森自我意识本体论初探 [J]. 哲学研究, 1998, (5) :65-71.
[9] 徐莹.论福克纳作品中的时间观[D].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5.
[10]肖德生. 胡塞尔对主客观时间关系的确立[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20-25.
[11]田燕,胡健.论厄德里克小说中的后现代情怀[J].求索,2013,(8):164-166.
[12]保罗·蒂里希. 存在的勇气[M]. 成穷,王作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13]E.Panofsky, Studies in Iconology, III: father time[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14]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M].范晔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
[15]潘冬梅.关于罗兰·巴尔特“作者死亡论”的思考[J].中国文学研究,2013,(3):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