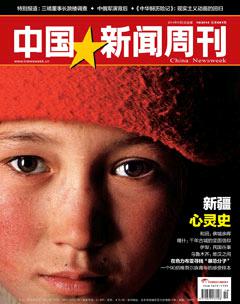不爱红妆爱“药妆”
安然
上一周,妮可·基德曼亮相戛纳的时候,她主演的电影《摩纳哥王妃》遭到了冷遇,而她那张能够应验“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的脸,却上了报纸的头条。英国《每日邮报》在刊登了她十年前和现如今的两张对比照片后说:不得不推测,这张永远光滑的面孔,是Botox所起的作用。
今年是Botox(A型肉毒毒素,中文商品名保妥适)首次被发现具有除皱美容作用25周年。这种原本用于治疗眼睑痉挛、斜颈症和偏头痛的注射液在进入临床应用最初的13年里都默默无闻,随后却因为偶然被发现可用于皮肤除皱而立即名声大噪。它的这段和壮阳药伟哥类似的“歪打正着”的出身,折射出美容和性一样,都是泛媒体时代热衷于制造的“娱乐至死”的健康话题。如今,“疯狂的毒素”之风愈刮愈烈,美容业最时髦的做法是:推荐人们在20多岁皱纹形成之前就预防性地注射Botox。
步Botox的后尘,瑞典Q-Med 公司的产品Restylane(成分是透明质酸)经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批准进入市场。这种透明的凝胶状制剂同样通过注射进入皮肤,少量的透明质酸与皮肤组织相融合,并吸收和锁定水分子,注射后30分钟内皱纹就能消失。与Botox的使用类似,“患者”需要每隔半年重复注射才能保持效果。
尽管如此,美国皮肤科学会的专家们仍然信心十足地认为,像Botox、Restylane这样的药物美容手段大有发展前途,理由是:它们和整容手术相比没有损伤,和名目繁多的化妆品相比效果确切,而且治疗过程快速、简便、安全。
心急的商家早就杜撰了一个生硬的名词——“药妆品”来统称这些具有药物作用并在化妆品市场上大受青睐的产品。越来越多的药厂正沿着这个路子研究开发用于美容的生物活性物质——全球120多家药妆品公司正在分吃超过百亿美元的市场大餐。
也许是受Botox经验的启发,利用药物原本的副作用来实现美容的效果也算是药妆品研发的一种套路:治疗锥虫病的药物Vaniqa被开发成一种脱毛剂,用来去除和抑制女性汗毛;抗高血压药Minoxidel被重新注册成一种叫Rogaine的生发药后卖得更火。美容药正发展成一个大家族,抗日光损害、去色素、去痘、防干燥以及抗皮肤衰老新药的审批文件纷纷摆到FDA官员的办公桌,然后走向市场。
1993年,美国宾州大学教授Kligman在其“果酸护肤美容法”盛行之时,提出“介于药物和化妆品之间的产品”这一概念。其实,说到药物的美容效果,中药的历史要悠久得多:三国时期, 孙权之子宠爱的邓夫人在外用中药治疗疾病时, 不经意间发现她的面部皮肤比往日更显白里透红、妖艳动人。历史上用于养颜驻颜的中药配方不胜枚举:人参的益补气血;珍珠粉的嫩肤白面、驻颜消斑;当归的养血活血行气;黄芪的补气生血和茯苓的润泽皮肤等。
如今,尽管“药妆品”的说法在美容业人人皆知,但是各国药政部门出于严格区分药物和化妆品的考量,并没有将这一名称列为一个单独的类别。在欧洲,药妆品属于“活性化妆品”或“功能性化妆品”,对于这类产品没有相应的法规进行管理。日本专门为药妆品设立了新的类别“医药部外品”,获得审批之后的医药部外品在市场上与普通化妆品一样,可以在药房、药妆店和超市等渠道销售。
中国将化妆品分为“特殊用途化妆品”和“一般用途化妆品”,前者包括育发、染发、烫发、脱毛、美乳、健美、除臭、祛斑及防晒等九大类,其生产与销售需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但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并不认定“特殊用途化妆品”就是“药妆品”,而且将标识为“药妆品”和“医学护肤品”的行为视为违规。尽管如此,薇姿、雅漾、理肤泉等药妆品牌仍在中国大行其道。
美国FDA则将这类超出化妆品定义的功能性产品作为非处方药来进行审批和管理。“能够改变人体结构和功能的产品都被视为药品。例如,透明质酸是构成皮肤的成分之一,Restylane具有改变皮肤形态结构的药理作用,所以理应被当作药物。” FDA化妆品部主任琳达·凯兹解释说,FDA不会把“药妆品”这样含混的概念用作新的产品类别,“在FDA的词典里,药就是药,化妆品就是化妆品,我们使用不同的法规进行审批和管理,不能混淆。” 而且,根据风险和效益对等的原则,相对于用来治病的药物而言,FDA对用于美容的药物在审批程序上要求更严。
尽管如此,许多整形外科医生发现,药物美容突然间时髦了起来。像Botox、Restylane这样的注射美容越来越受追捧,虽然这些方法不是永久性的,需要重复进行,但是由于它们做起来安全、方便,所以正被那些白领阶层的人们津津乐道,并被称为“午餐时间的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