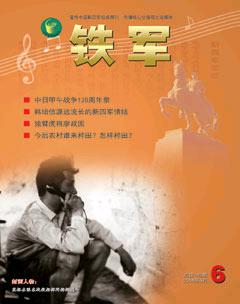心中的延安
稚玥
“如柏,在没有你的漫长岁月中,我有许多梦。我梦想:当我乳腺癌手术查出扩散后,连续8年的放疗和化疗,在我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下,你会走进我的病房,给我些安慰和鼓励;我梦想:我在你亲手经营的小院里剪花锄草时,你静静地坐在我的身后看着我……”1984年3月27日,金如柏将军病逝,这是他的夫人郑知文女士心中深切的思念,那绵长的爱、深厚的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春天里满是泥泞
“1939年,我16岁,一个活蹦乱跳的女孩子,为了不当亡国奴,从这个大门走向了革命”。“1925年五卅运动,我也和同学一道上街游行,进一步懂得一些什么(是)列强欺压中国,中国是个睡狮。”这个“女孩子”出生于1923年,今年已90岁高龄,她是《苦难辉煌》的作者金一南教授的母亲郑知文女士。上街游行的热血青年是开国少将金如柏将军,他和郑知文女士携手走过的苦涩、艰辛与幸福,在今天看来,苦亦甜,因为那些逝去的日子,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
当2009年出版的《苦难辉煌》一书销售突破400万册的时候,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金一南教授在2013年八一建军节又推出力作《心胜》。心中的力量源自信仰,信仰是从哪里来?金教授曾在讲课或写书时总在追问:“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信仰从哪里来?又要坚守着信仰到哪里去呢?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坚守,这份坚守抑或执著,就如同当年不愿当亡国奴的青年都要历经生死也要走到革命圣地延安一样,那么,金一南教授和他父母亲心中的延安在哪里呢?
在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展厅里,“途经七贤庄的爱国志士及国际友人”的名单上,郑知文女士的名字也在其中,她就是从那里出发走上革命的道路。
出生在书香门第的郑知文女士,刚踏上革命道路时还不到16岁,她在《飘落的日历》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开封沦陷,那时我正读初中二年级,学校停办,留在开封就要当亡国奴;我和几个同学商量着要从家里偷跑,一同到延安……”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郑知文从开封出发到延安,千里奔波,但她义无反顾;而在那个大浪淘沙的革命年代,21岁的金如柏从江西吉安永丰出发,追赶上了红军的队伍,这一走就是一生。他是独子,却没有选择留在老母亲的身边,而且他也明知“我走后家一定会完”,但他也是义无反顾在1930年的大年初一,瞒着家人,走上了从江西到延安的万里长征路。
金一南教授在看到父亲母亲走过坎坷的人生路后却依然信念不改、志向不衰、意志如钢,他写道:“中华民族的崛起实际上从父亲母亲那一代面对民族危难、毅然跨出家门的时刻已经开始。虽然我们这个家庭不过是沧海一粟,而且伴随这一进程经历了无数磨难,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由衷的骄傲,因为经此非凡年代,这个家庭参与了、见证了中华民族从苦难到辉煌的崛起历程。”
有人把苦难视为苦难,有人将苦难视为财富;有人将辉煌视为辉煌,有人则将辉煌视为过去。有人在苦难中沉沦,有人在辉煌中迷失,因此,视苦难为水火,苦难就将吞噬掉那些自我消沉的人,相反,踏过荆棘,闯过困难,把苦难作为人生的一次体验,那么,苦难也会作为人生厚重的一笔财富;视辉煌为终点的人,辉煌也就真的会成为过去,而视辉煌为起点的人,则必将站在更高处开创未来。
金如柏将军和郑知文女士,从江西、河南都走到了心中的圣地——延安。“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得出这一论断的不只是陈嘉庚,还有1944年10月23日即将离开中国的史迪威,他对一个跟随他在缅甸战场浴血抗战两年半的“娃娃兵”意味深长地说:“孩子,你知道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哪里吗?我告诉你,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延安,对于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来说,就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所在地,能走到心中的延安,也就走近了希望,走近了胜利。
飘落的日历
金如柏在全国解放后把自己的母亲接到了身边,可是,母亲却已近双目失明。时隔20多年后,在“文革”中被关押了5年的金如柏,也认不出已经长成大小伙子的两个儿子了。无论是国难当头,还是在天灾人祸面前,金如柏和郑知文都选择了坚持、坚强和坚守,那种“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的夫妻情,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年代,更显得温馨、温情与温暖。
“手摇柏枝情意长,我坐监牢你不忘。天河出在人间地,见面不言心齐放”,这是金如柏在“文革”关押4年后,听到妻子机智地报了家人平安的消息即兴写的小诗。郑知文在无意间发现了丈夫,但她却不能上前相见,情急之下,她看到一位抱孩子的妇女,就赶紧大声说出6个子女及自己的近况。尽管那位妇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金如柏却是那么的知足,他在路边摘了一个松枝,远远地向郑知文摇了摇,而远处的郑知文只能勉强挤出一丝苦笑。
那个满地泥泞的年代,留下了多少心酸的记忆。在金如柏被关押十几天后的一次批斗会上,郑知文听到走廊传来“金如柏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那吆喝声喊得震天响,她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拿上杯子,倒了一杯开水,快步向会议室走去,她见到了面色苍白的丈夫金如柏。造反派一巴掌打掉了水杯,郑知文的手被烫红了,水杯碎了,她的心也跟着碎了,因为她看到了丈夫那既无助又无奈的眼神。
那眼神,真的是刻骨铭心,郑知文一辈子都不能忘。金一南教授曾在当工人烧瓶子时,把自己双手十指的神经都烫死了,所以,他能从热锅里取盘子,但是,当他看到母亲那心疼的目光,他就再也不当着母亲的面去做这件事,因为他怕伤母亲的心,他记得父亲病故前,用那双饱经风霜的手拉着他们几个孩子的手说,“要对你们的妈妈好,像对我一样。”金如柏最担心的是妻子的脾气急、性格硬,“急,就容易伤人;硬,就容易折断”,但在金如柏去世的20多年后,这个大家庭依然和和睦睦,郑知文和6个子女把这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维持得长幼有序。
然而,越是看得到月落日出,越是看得到花开满园,越是感受到亲情可贵,郑知文心中的感慨也就越多越深。她梦想:“假如我早些懂得保健知识,也许可以延长你的寿命。我甚至梦想:有朝一日你会突然站在我的面前对我说:我回来了,过去一切都是假的,只有我站在你面前,这才是真的。我心里明白,这些梦无法成为现实,但她是我的精神寄托,这些梦将陪伴我度过余生,直至永远!”走过的苦涩,熬过的艰难,那些相濡以沫,那些相扶相帮,都是极为珍贵的美好回忆。
待到雪化时
金如柏留给儿子金一南的记忆是1983年他病重住院,在病房里金一南第一次为父亲洗脚,“脚上一块块老皮,洗起来硌手,那是红军时期有一段连草鞋都没得穿,赤脚行军,赤脚冲锋,还要扛着沉重的马克沁重机枪,走小路或无路的山”,因此这硌手的双脚见证的是当年革命的出生入死。而当金如柏病逝后,金一南第一次回到父亲当年生活过的故乡永丰,站在那几间潮湿破旧、屋里黑到几乎难有一丝光线的土坯房前,他思考的是,穿了一辈子军装的父亲,什么是他生命的本来颜色?
金如柏将军终身难忘这样一件事:1931年苏区打“AB团”,与他同屋的一个战友被拉出去,指为AB团。执行的战士挥刀时有些手软,那个战友扶着鲜血直流的脖颈还在喊:“我是CP,不是AB团哪!”这些往事使他直到晚年回忆起来仍会热泪盈眶。然而,谁又能想到在金如柏54年的革命生涯中,竟然有21年是在委屈中度过的。但是,他却不记恨甚至是在“文革”关押期间给他带来伤害的那些战士,因为他知道那些战士也是执行命令。
“他是个受了很多苦的人”,这句话是1984年3月金如柏病危时,他的老战友女将军李贞赶来看他时说的。隐忍不发,不是看不懂,而是执著坚守自己的信仰,那些年,那些事,那些痛,每当回想起这些往事时,郑知文都有一个梦想和希望,那就是:“当我们国家的许多历史真相披露时,我梦想如果他知道,肯定会比我们高兴,因为他是一个亲身经历者,一个满身伤痛的胜利者。”
飘落的是日历,永恒的是精神。回首他们走过的那段岁月,留下的是信仰,不朽的是人格。大写的人字站在天地间,长存的意志立于苍穹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采,那一代人给我们讲述的是走过苦难后的辉煌。当我们仰望天上的群星璀璨夺目时,还依稀可见他们当年的血水、汗水和泪水。前辈傲霜迎雪,我们也该顶天立地,因为他们在天上看着我们。共和国也不会忘记那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和平和阳光的先人,他们是真人,不怕死,不畏难,不觉亏,用生命诠释忠诚,给世人留下了精神高地,就像雪山之上的松柏,万年长青。 (责任编辑 束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