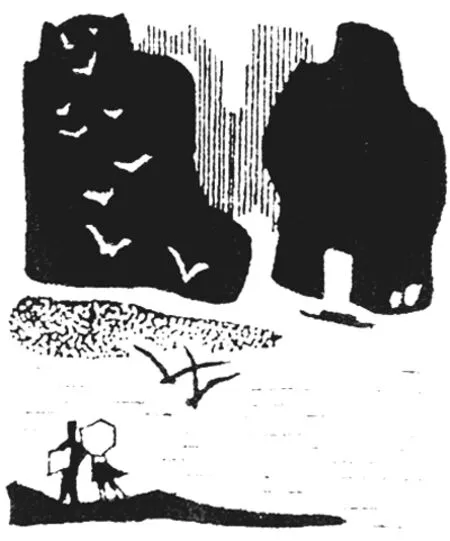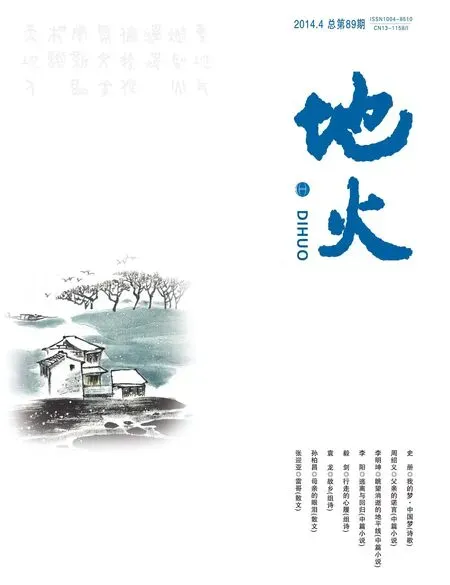这里黎明静悄悄
——北大港湿地记
■ 侯建英
这里黎明静悄悄
——北大港湿地记
■ 侯建英
漫水桥
三月,已迫在眉睫。冰河消融,少了冬的映像。一路沿坝西行,河水在流淌。
井生要走的漫水桥,多少有些离奇。这条再普通不过的独流碱河,又该怎样衍生它那并不浪漫的边幅呢?料峭的寒风,吹不散的雾。我和他和她,已经在路上,品茗晨曦里那摇曳的早春。
河水涨了又涨,在这春天。这路,也只有在冬天,或者是在缺水的季节,路基才会渐次地裸露。
车过漫水桥,一切都已孑然。于是,本能的不安,便与这说不出的信任短兵相接。这条路,对于井生来说,已走过无数次了。那东往的河水,快要淹没了北走的车轮。井生加了二挡,点着油门,不熄火,也不迟疑。标着前方露出水面的路基,匀速地前行。两边的河水被轻轻地推开,水波漾去,层叠出无穷的波澜,极像行游在独流碱河上的一叶扁舟。船头惊鬼,船尾惊贼。这样的比喻,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
上了岸,井生告诉我们等着尾随在后面“宝石花”们。之前,岸上的两个人已然成了相机中的风景,我得意地冲他们笑了笑,仿佛是要告诉他们,看,这一切其实并不难做到。
“宝石花”们,比起我们想象的要安全得多。他们乘坐的大轿车,亦如水中黄色的航母。他们笑着,并向我们招了手。这里的水面,泛着鳞白的银光。一条河,甩在了身后,还有两个赏河景的看客。我问井生这漫水桥的缘由与典故,他笑着,递过他精美的电子杰作。
漫水桥并没有缘由与典故,这桥或许只与这荒蛮深处的油井有关。一些巧合被无数个路过它的人,赋予了使命。这漫水桥,也被无心浪漫的人点缀得极好。
过了漫水桥,另一种荒凉,迎面扑来。烧过荒的黑土地,与金色的苇丛穿插。几处荒冢弥漫着亘古的气息,那些并不遥远的先辈,享受着他的子孙们极好的敬泽。因为,它们存在的形式是那么的高大。这里的生命从未泯灭,我以为,他们是活着的,守护着先祖遗存的悲凉步履。
路越长,便越是细窄。但这荒凉,终究会有驿站。我预习着井生递过来的电子杰作,这功课也一定是要补的。传说中的震旦鸦雀,闲淡笃定,一种鱼飞过,遁入无息的深邃。那冰雪葱茏的境地,是一种绝美的沉浮。一切的机缘都将重合。不是么?我这样问过你。
北大港湿地护鸟站
到达北大港湿地护鸟站,大概是八点钟的样子。护鸟站耸立在高高的土堤上。原本浩瀚的苇场,已然成为临时的停车场。“宝石花”们先后下了车。今天是“宝石花”青年志愿者服务团队创建北大港湿地服务基地启动仪式活动。有幸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不得不感谢朋友的眷顾。
保护湿地,共建美丽家园。井生策划的这一活动主题,也是相当的精彩。我并由衷地从心底钦佩这种生态理念。毕竟,能落实到行动中的事情,其实并不多见。
在护鸟站,林林总总的照片挂了满墙。没等脚跟落稳,井生便再去漫水桥接他看鸟的朋友。漫水桥,其实并不十分凶险,但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高度的谨慎。
天空依旧阴霾,远处的水面凫游着成群的生灵,黑压压的,斑点般的游动。一些冷,钻进脖子里,那些曾经葱茏的植物已衍生成另一种辉煌。在水天间,空灵而隽永。
“宝石花”们,继续着他们义工的职责。“宝石花”青年志愿者基地的牌子被郑重地钉在墙上。在挂牌仪式上,井生说,这不仅仅是块普通的牌子,这背后有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一种理念被根植,一种传承在蔓延。湿地,我的相知与乡谣,可以放心的是,它可以继续它的大美了。
浩瀚的芦苇场,像极了童年的麦场。一垛垛,纷纷扬扬。那垛场里,不时会有几只野鸡飞起飞落。井生知道哪一种鸟会在这里栖息,也包括它们所在的巢。
井生为大家准备了志愿者义务捐赠的望远镜,我们一字排开,向传说中的天鹅湖致意。之前的讲解,已分化为两条不同的路径。对鸟的杀戮已渐行渐远,这里只有平静和微澜。我们的存在不得不隐匿。
在湿地,最庞大生灵,非天鹅莫属。那些黑色的斑点,永远都是天鹅的陪衬。这天鹅成双成对,决不参差。它们俩俩扎进去,将脖颈一提,一打转身,背离岸上这些看鸟的痴人。太阳渗出轻霾,映照在高支的三脚架上,那些虹绿的光环,穿透玻璃和断片,剌剌地晃动着绚烂的光波。
这天,还是依旧的冷。我和她躲在鸟站另一间塑钢房外,看深邃的水面游来游去的精灵,也探看“宝石花”们竖起的那面呼啦啦的旗帜。鸟站已被赋予了使命,这段属于我们的历史,沉重与希冀并行,时间像是个泡影。在水边,我们俩,投映在平静的天鹅湖面。有一种融入,不知不觉。
几块饼干果腹后,太阳的温度也跟着上升了许多。《早报》的记者收起了三脚架,静静地离开了鸟站。该是收工的时分。“宝石花”和他们乘坐的航母,离开了苇场。他们匀速地向着漫水桥方向,驶去……
天鹅湖
不想这么就走了。井生今天的任务,不仅仅是一种誓言,他要带他曾经并肩过的两位班长,深游他所爱着的湿地。又一次,我们不谋而合。
班长老郭第一次深入湿地腹部,虽然他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十个春秋。对于骨子里淡定的老郭来说,兴奋藏在心底。
从鸟站,又辟出一条路。这里虽然冷僻,但依旧不缺少探秘者的痕迹。井生讲的巫鸟,我并没有见过,但大概知道,它们会在七月,成群地飞到再北的盘锦。夏季还要去迁徙的鸟儿,又有怎样浓深的乡土情结。它们成群地飞去,又是怎样的一种集体意识。然后呢,在那里再分散开去,做窝、产卵、繁衍,甚至鸠占鹊巢,几路搏杀。有些事,我不大明白,也不太知道。我和我的冥想,再一次升空,但那飞越多半是空穴来风。
车过望鸟台,才有了仰视的高度。因为有一群爱鸟的人,这里才有了鸟站,才有了望鸟台。因为没有钥匙,我们无法登塔。走得远了,便会遇着驻扎在湿地深处的渔家,那砖红的房屋外,有渔网、三马子、绿菜、木凳和大小的盆……每一个驿站,都是相约锁定的风景。
湿地,这片无声的宁静下,会有多少隐匿了的生命、生息、挣扎或者彷徨。因为杀戮,从来不曾在这里消失。井生亲历了,那场残暴血腥的惨烈场面。成片的野鸭连遭暴雨后,被无情地挂在网上,清理的过程极其艰难。救不过来,也无法救,因为太多太多,野鸭多半已经死去。累,无助,痛哭,那片曾经让他们痛心过的地方,又一次刺痛了井生。
井生的滔滔不绝,全然离不开他所深爱的这片湿地。我们的聆听,不仅仅是一种尊重。陈班长和郭班长一样,依然淡定从容。他俩也并不与我们两位美女搭讪。只是一味地听井生,讲天鹅、讲东方白鹳,讲夜晚大灯下,莽撞惊魂的野兔,讲一个关于离他们很近,却从来都很遥远的湿地。这里的一切生灵,都会被一个,或者一群人关注。生于斯,长于斯,守护于斯。因为,我不爱,谁来去爱。
我们终于到了天鹅聚集最多的地方,这片浅浅的湿地,有水生的螺蛳与蒲根之类的植物。出泥的蒲根,着实地坚硬,黑褐色的核,拉了毛愣愣的蕾丝。那核里的一点点甜汁,早已在齿间淀出水粉。这蒲根,已有多年未食。此刻,童年是一片疏离的章节。
浅浅的湿地,栖息着成片的天鹅。这一回,较之前的景色应该更为壮观。一种绝对的静止,打乱了我美好的期待。显然它们是昨晚或者凌晨刚刚迁徙而来的,在历尽千险后,沉睡在一个疲倦的早春里。
蒲根水暖雁初浴,梅径香寒蜂未知。天鹅的美食也是蒲根,井生讲来道去的蒲根,刚好与这香寒的水暖轻轻地重合。
我们的车,停在路边。被路边干透了的芦苇掩映得极好。几辆车,接了龙。一些寂寥的看鸟人,恪守着这里的安静与本分。井生与早在这里看鸟的人握了手。一些爱鸟的人,从来都不觉得陌生。
穿黑夹克的陈班长,抱了“大炮”,小心地把它架在平稳的三脚架上。那是一件仿旧的磨砂皮衣,与郭班长绿色的野战棉服,极其的搭配。井生由衷地赞美两位班长懂得时宜的绝妙装扮。郭班长告诉我,这里的天鹅大概有四五百只。我笑了笑,调侃地说,你数过?不用一只只数,这一片大概有多少只,然后,再分成若干片,一乘这数据就出来了。这么简单的概算,怎么我没有想到。一种顿悟,可以在瞬间缪然开阖。在无序的浩渺间,我只是一枚飘摇的蒲草。
陈班长将“大炮”放稳。我们依次地领略了,那静寂的天鹅湖。不管是白天鹅、小天鹅或者是疣鼻天鹅,这里终究是它们的驿站。它们的家乡在遥远的俄罗斯远东。长途的跋涉,使沉睡的天鹅,少了优雅的身姿。它们一团团或者三两只拥簇在一起,偶尔伸了疲倦的脖颈,便又遁入雪白的天鹅绒里。
小孩子吵着要看天鹅,我便与她储备库的父亲攀谈起来。我问他,在哪里工作。他指着东边湿地深处的建筑告诉我说,就在那里。中石油麾下小的分支。他说他们一家三口,还是第一次来这里看天鹅。之前,并不知道这里还有那么多天鹅。是这样,可你在这里工作啊。我笑着,问他我们去你上班的地方玩要不要进门证。他说当然。我又一次笑了,便不再多问。
一辆黑色的捷达,停在路边。几个穿深色衣服的家伙,下了车。不土不洋,操着地道的津南口音。一条大金链子,绕着那人肥大的脖颈。那个家伙下车后,下意识地提了提他锅盔式的裤腰,定了定神,这才腆着肚子蹒跚地向着“大炮”走去。井生调了镜头,几百米开外的天鹅已是相当的清晰。井生又调转了“大炮”,多角度向他展示湿地的全貌。观鸟台在茂密的苇丛中,挺挺而立,台下,停了一辆白色的桑塔纳。和陌生人搭讪,是我的拿手强项。我迎上了锅盔,问他是哪里人,也是来这里看天鹅么?锅盔似乎有些冷淡,淡淡地说我们哪里是本地人,我们开车路过,来这里玩玩。我说东方白鹳事件,整得动静挺大的,来了不少记者,还上报了。锅盔这才点了点头,说听说过,有的还判了刑。现在非法捕捉天鹅犯法啊,会坐牢的,我们村就抓了一个,判了十五年。锅盔是个明白人。我嗯着,便也不再多问。
已近正午,黑色的捷达不再流连这里的风景。我们也收拾好“大炮”,继续向东向南驶去。
另一个景致,又会有另一种风情。黑色的斑点,浮满了水面。井生说那些鸟叫黑水鸡,如果细心,你会发现,它们永远与人保持一种绝对的距离。我们的车随时可以停下来。井生指着另一片黑色的斑点说,那是一群红头潜鸭。因为远,我们没有看出异样来。郭班长将“大炮”架在车窗上,一阵猛瞄,好不容易才看清楚,那的确是一群酱红色头冠的黑鸭子。白天鹅在纵深的水面,尽情地游弋。一汪水域,便是一个世界。那些以己水为圆心的水鸟,在互不侵犯的领域里,怡然自得。无论高贵与卑微,一个族群,都有着它们强烈的家族意识,并各自恪守本分,繁衍着属于它们生命的使命。噢,不是么,这些地球村的精灵。
一阵连拍后,陈班长正了正他的鸭舌皮帽。正午的阳光,洒在静美的湖面。暖阳破冰封,沧桑化轻薄。一种快意在陈班长的脸上洋溢。
西岸的观鸟台,向我们远远地招手。塔下的白点被再一次放大,纯白的车,黑色的影,一群银鸥低低地飞。
此时,我已穿越了时光的隧道,在冰雪葱茏的苇枝上,捕捉振动的频率。
道别天鹅湖,黑色的斑点不再与我们平行。开过漫水桥,橘色的磕头机,点动着沉重节率。井生,永远讲不完关于湿地的故事。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井,那些站。在冰冷漆黑的夜晚,站上,有一个采样的男孩,走进那片深深的芦苇,再也没有回来。他用他最温暖的泪水,告别了似火流年的青春。
有一种生命,会湮灭。有一种生息,在繁衍。此时,我们沉溺在坝上乍暖的料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