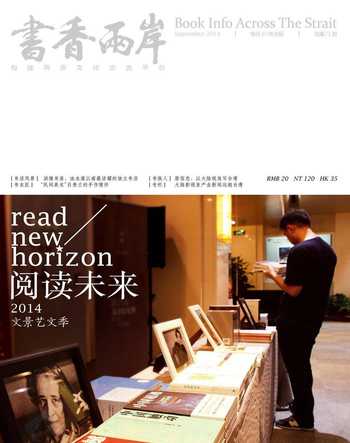我们为什么看不懂当代艺术
今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观赏到艺术品。尤其在大城市,不定期举办的各种雕塑展、画展,不断兴建的各类艺术场所、艺术景观,让艺术越来越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在闲暇的时候,除了阅读书籍、观看电影之外,有人也可能会选择一种新的休闲方式,就是走进美术馆欣赏艺术作品。
然而,对于当代艺术,不少人都会感觉不得要领,因为它五光十色,让我们眼花缭乱;它灵活运用影像、装置、行为等多种形式,让我们目不暇接。我们为什么看不懂当代艺术?通过讨论,或许有助于我们寻找到理解当代艺术的路径。
吕澎:这个题目在我看来其实是互通的问题,是学习艺术、艺术史和想要了解文化、历史的所有人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一次走进美术馆、展厅,都有可能遭遇到过去从未见到的艺术现象、艺术作品。对于从事艺术研究、艺术批评、艺术史工作的老师、专家来说,都会在面对这些新作品的时候产生很多疑问,所以实际上,我们为什么看不懂当代艺术,这个问题对于我和大家其实是共通的。我怎么来回应这样的问题呢?先非常简单地提示几个路径,来谈一下我的体会。
第一,在了解当代艺术时也好,了解艺术时也好,包括了解文学、诗歌,了解文化领域里面的所有创造或者新现象,我觉得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路径:我们应该有一个历史的判断。当我们看到一件作品,如果具备基本的历史知识,马上就会知道这件作品也许跟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社会发生关系,也许跟过去的某一个艺术现象、某一位艺术家或者某一种风格发生关系。不管怎么样,它总能够跟我们的知识背景发生联系。
第二,路径的问题,也就是教育。1949年以来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美术院校几乎没有美术或艺术的教育,也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人就是一张白纸。那时候我们有毛主席语录,有大字报,有刘少奇、邓小平的漫画,这些在大街上都能看到,因此当时的美术概念就是这些。当脑子里面只有大字报记忆的时候,突然面对一个从未见过的艺术现象(当代艺术),那么对它的反应很简单,就是看不懂。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教育,即知识来源。
第三,知识的更新状态。我们从大学毕业了,但是我们的知识还非常有限,所以当我们走进美术馆、展厅时还是看不懂作品。再加上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变化太快,导致出现新的艺术现象需要你重新理解,这就出现了知识的更新问题。我们看不懂一个艺术现象,总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把眼前的艺术现象、它的产生原因、它所要表达的可能性和我们的知识背景联系在一起,没有这种知识就不能理解这个艺术。今天的艺术本身的观念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简单地用形式、风格学分析的路径太狭窄了,我们也许要从政治、社会,甚至从文化、语言的角度重新观察眼前的艺术现象。
所以,我们为什么看不懂当代艺术?原因太多,包括从事专门研究的学者,在面对作品时,有时也会在没有了解背景的情况下无话可说。我们需要跟艺术家沟通交流,阅读关于这个艺术品的评论,再调动我们的知识背景来综合进行分析评估,渐渐地才能说出自己的观点。所以,看不看得懂当代艺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对涉及艺术的综合知识的了解,这是最基本的方面。
黄专:坦率地说,我回答不了“我们为什么看不懂当代艺术”这个问题,不过也许我可以换一个角度谈谈这个问题,我的问题是:作为普通观众,我们如何通过当代艺术获得“观看的自由”?
“自由”这个词,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思想、一种行动,但实际上,观看也存在着“自由”与“不自由”的问题。当我们通过语言、文字、艺术表达思想时,很容易体会到社会权力机制的控制,体会到不自由,甚至在微信、微博上,遭遇屏蔽的意见和时论很快就会使我们感受到不自由。
和表达的不自由比较,观看的不自由也许显得更为隐性。表面上看,观看是一种无语的主观行为,为什么也会涉及到自由问题呢?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在家里看黄色录像带,是有可能被抓起来甚至坐牢的;今天在家里看黄色录像带,可能在某些地区还会被抓,这说明在纯主观观看行为背后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权力管制系统,这是观看的“外在性”的不自由。但在这里我想讨论的是另一种更深刻、更基础的观看控制,即内在的观看控制,一种来自于主体自身的自控,一种“内在性”的不自由。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更大的不自由。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观看不可能是纯粹先验性的,我们总是在某种特定知识和生活经验中观看,对当代艺术的观看也是这样。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很想问问观众,你们是通过什么途径接触当代艺术的?
观众1:我自己学习当代艺术,在当代艺术博物馆也有工作,我是通过展览(接触当代艺术的)。
观众2:我年轻的时候也是美术爱好者,那时候就是想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从画册、画家讲座上放的一些幻灯片(来接触当代艺术),到现在互联网(的作用)就更大了,再有就是展览,还会向一些当代艺术的朋友了解一下。
观众3:我除了展览还通过互联网。
观众4:现在互联网那么普及,所有信息都能够从互联网上得到,为什么在中国会产生大家都看不懂当代艺术这样的现象?
黄专:我试着作为一个观众回答这个问题。我是学习艺术史的,现在也研究艺术史、策划展览,但我们最开始接触现代艺术主要是通过阅读而不是观看。我跟吕老师属于同一辈人,在八十年代初读大学时就已经关注现代艺术了。我最早看的是鲁迅翻译的坂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后来是赫伯特·里德的《西方绘画简史》、阿纳森的《西方现代美术史》。当时不要说西方的展览,就是看到西方作品印刷品的机会也很少,但1985年我在中国美术馆偶然看到劳申伯格的展览,这对我认识现代艺术是一次转折性的经验。这个展览提醒我们,在印象派、立体派、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这些现代主义风格谱系之外,还存在一个观念艺术的谱系。浙江大学沈语冰老师最近几年重新翻译了很多重要的现代主义的理论著作,希望我们重新反省一下我们自以为看懂了的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震撼”(shock)是十九世纪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新型的现代性的经验。进入“现代”后我们的世界变了,不光经济生活、社会生活、艺术生活,也包括我们的视觉观看经验都变了,“震撼”已经成为现代艺术的一种恒常价值,创造使人惊奇的作品成为艺术家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这个价值首先带来的就是艺术和传统观看经验的断裂,功能决定形式,看不懂也自然成为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手段,这与宗教艺术力图最大限度地使观众接受的历史动机完全不同。所以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是,所有观看其实都是关于知识的观看,而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于艺术史知识的观看,如果你希望“看懂”当代艺术,我建议大家首先了解一下它的历史。
第二点,我们对艺术品的观看通常不可避免的是片面、局部和断裂式的,很难真正看到艺术的“全貌”。巫鸿先生在《美术史十议》中有一个关于艺术品的有趣概念:“历史物质性”,就是说所有的艺术品并不自动显现为历史的形态,它需要经过历史研究才能真正被“还原”和建构为一件艺术品。所以我们通常条件下看到的一幅油画、一件雕塑或者一件现成品装置都只能叫“实物”,只有在历史研究中实现了它的语境还原和重建的艺术品才能被称为“原物”。对普通观众而言,无论是在书本上还是在展览中,几乎都很难观看到“原物”,总是某种片断的观看。杜尚的小便池并不是在它开始进入展厅那一刻就被视为艺术史“经典”的,它的“历史意义”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达达主义”运动尤其是五六十年代观念主义运动中被逐渐发掘出来的。其实,每件艺术品都是一种单体生命,艺术家将它生产出来以后,它就沿着自己的生存轨迹发展,并不完全服从艺术家的意志,所以,真正的观看应该是一种历时性的观看。对普通观众而言,“看不懂”一件当代艺术作品是十分正常的,每个人以片断的方式去观看当代艺术是一个合理的常态,承认“看不懂”当代艺术、承认反感当代艺术并不丢人。普通观众在观看当代艺术品时,常会受到各种艺术解释权力的暗示、诱导、左右和压力,它们会使我们产生“观看的焦虑”,所以,一个普通观众观看当代艺术时,首先要服从自己的直觉、趣味和经验,如果不喜欢就应该果断地拒绝,主动克服这种观看的焦虑;如果喜欢,我就建议通过艺术史的方式了解它们、审视它们、找到喜欢它们的理由。只有在观看时保持对任何可能的控制权力有意识的警觉,不轻易屈从时尚的压力,我们才能真正获得观看的自由。
第三个是对普通观众可能同样十分纠结的问题:当代艺术能不能进行“观赏”?一般观众去美术馆和博物馆的主要期待是观赏,对他们而言,艺术品首先必须具备观赏性。这种心理期待其实不是与生俱来的,例如对艺术品中的“美”进行观赏的习惯在西方至少是从十七、十八世纪才开始的:艺术品必须是理性和谐的,应该比例平衡、色彩悦目,而当代艺术,尤其是观念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审美,甚至是反视觉的。但我觉得,普通观众有权利讨论当代艺术的“观赏性”,甚至把它作为观看当代艺术的一个主要理由。事实上,最近若干年,一种新型的当代审美观正在慢慢复苏,近期西方举办的大量现代主义或当代主义早期的一些大师作品的展览,都具有鲜明的美学观赏特质和视觉效果。如果说当代艺术对于普通观众有什么意义,我的看法是,它除了“震撼”外,还应该带给我们更大的观看自由,而不是限制这种自由。“观看的自由”就是用理性的态度去控制、发现、表达自己观看行为的自由。如果我们在当代艺术中无法获得这种自由,即使我们真正“看懂了”当代艺术,在我看来也毫无意义。
主持人:当我们写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对于两个预设,我们大家还没有达成共识。第一个预设,什么是当代艺术?刚才两位老师也分享了他们接触当代艺术的路径,或者说接触艺术的路径,我们可以感觉到关于当代艺术这件事情,它的内涵和外延并不是很清楚的。其实绝大多数的观看者是以一个十八世纪观众的经验进入美术馆的,但是实际上从十八世纪到现在,中间至少隔了两件事,一件事是现代艺术,一件事是当代艺术。“现代”本身就是一个时间的观念,它不像之前的古典主义或印象派是有明确的主题和技法特征的。现代艺术已经是一个要用时间性质去界定的概念。而我们好不容易在现代艺术当中总结出了一些关于现代人的疏离、孤独的共同性质,还没仔细琢磨的时候,当代艺术又来到了面前。而“当代艺术”就更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我们本身就没有很好的界定。这样的情况下让两位老师答为什么看不懂当代艺术,是必须说一声抱歉的,这是第一个要讲的前提。
第二个预设,大家今天坐在这里不光是因为想知道我们为什么看不懂当代艺术,可能更想知道我们为什么看不懂中国当代艺术。我们现在在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都可以接触到世界一流的艺术家的艺术展览,但很多人会更关心的是,为什么我们不理解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动机、情绪或是作品。这个可能会涉及吕澎老师一直关注的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达成共识的第二个预设是,如果说我们看不懂中国当代艺术,其实我们首先看不懂的是中国当代史,是我们对今天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还不够理解,对于过去三十年、六十年的历史没有达成共识,所以对于这个历史当中所生活的人怎么思考不够理解,对于生活在这里面的最敏感的艺术家,他们是怎么思考的动机不了解。
希望大家能够始终保持住自己内心当中那份渴望观察和理解艺术,乃至我们的生活、外部世界的兴趣。这也许是当代艺术能够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即使承认自己很难完整地去理解清楚当代艺术,我们也永远不会放弃这种努力尝试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