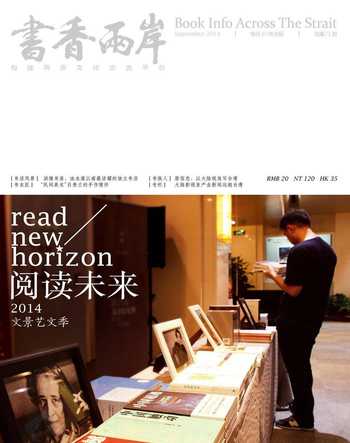敏感不是神经质
他们是敏感的,甚至神经质的。
一个是倍受关注的台湾新生代设计师聂永真,一个是当代颇具实践精神的文化人欧宁。
聂永真在文艺与商业、小众与流行的交融地带,身体力行,设计了不少精品,也有诸多对设计和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欧宁多年来在各个领域横跨,总是带来新鲜的力量。
这一场对谈,带来两位文艺先锋的思考。
聂永真:我之前完全不认识欧宁,之前看过他的一些作品,像《天南》杂志等,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来自于欧宁先生的。
两三年前在上海机场的书店里面看到《天南》杂志的时候非常吃惊,封面设计非常好看,一看就知道它是一本文学杂志。很多文学杂志的读者数量其实有一点有限。我那时候想了很久——这本杂志到底要卖给谁?可不可以让很美的信息或者看起来很好的品位,很完整地传播出去?我们作为一个设计师会觉得,如果这么一本看起来很好看的杂志可以被广泛传播出去是很好的事情,同时也担心,这样的美会不会跟读者产生距离?
欧宁:《天南》是比较神经质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杂志到底要卖给谁,因为当时创办这份杂志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市场调研,也没有设想它的读者是谁,只不过是有一种直觉——中国需要一本不一样的文学杂志。我们花了非常大的心思,从各方面,包括组稿、设计。视觉功劳归功于小马和橙子,他们在书的设计方面经验很多。
至于说是“神经质”的书,一些细节我非常执着,特别对编辑团队的要求很高。我本人是很偏执的,对一些很小的点,比如校对文稿的时候你用英文输入的括号和用中文输入的括号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们的间隔不一样,这样就导致字里行间阅读起来的那种视觉印象也不一样。这些很细的东西我们抓得很紧,因为一点点的不小心就可能会造成视觉上的一些瑕疵。就是在这样神经质的要求下从排版到整个视觉上的东西费了很大的工夫,所以基本上是一本比较神经质的杂志。
聂永真:我很羡慕《天南》出来的样子,它的样子是很独特的。台湾有很多文学杂志,它们必须让视觉包装看起来比较像生活杂志,比较大众化一点,因为编辑会觉得这样跟读者的距离会拉近一点,读者比较不会觉得这本杂志是冷的,但是往往在这样的拉锯之中,杂志最后出来的样子会变得很丑。台湾的大学有一些看起来还不错的杂志,像《小日子》等等,但是像那样类型的杂志,内容反而要变得更轻松一点,没办法太艰涩,要拉近跟读者距离。这是台湾跟大陆的区别,因为台湾的读者群太小了,我看到《天南》的时候觉得蛮开心的。
你刚刚提到《天南》是小马跟橙子做的,他们的东西充满了神经质。他们的设计作品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这个是表现在他们设计形象上面。除了这个形象,每个设计师或者创作人,扣除作品呈现之外,私底下一定会有一些与外环境格格不入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融入生活的环境。你扣除你的创作之外,或者在创作之前,有什么东西在生活上是你完全无法适应的,或者你一直以来都觉得它是错误的,但是它一直都存在着。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欧宁:我觉得自己适应能力还是挺强的,我在现实里面碰到什么问题都会很快地修正自己,我脑子也比较开放,不会接纳太强对错的方面。我现在生活在安徽农村,有一个比较难的事情,我周边生活的人特别敏感,所以在这方面我得非常小心地处理。我觉得他们这种敏感是有道理的,安徽那边的农民,特别是面临一个有外来移居者的环境时,他的这种尊严像玻璃一样的特别脆弱。
讲讲你自己。
聂永真:我自己的敏感都是非常小,比较无聊。
各位知道兰屿,最近台湾的7-11便利店要在兰屿开,很多人出来反对,他们说兰屿是台湾最干净最自然的一个地方,所以不应该有便利店的进驻。以都市人的角度看这样的便利店进入,会破坏兰屿的单纯生活,但是就兰屿人自己来看,他们非常期待便利店,因为他们太久被孤立在台湾岛以外的地方,为什么台湾有而兰屿没有。我们以城市人来看待在那个岛上的人和那个岛上居民的期待是完全有落差的,我觉得城市人有点自私,兰屿就是我们要休息的时候最后要去的那块净土,但是就兰屿人来讲他们更渴望跟本岛接触更多一点点。
欧宁:兰屿,包括跟我们现在安徽农村住是一样的,因为城市里面的人对农村或者对“净土”有一种想象,会觉得这个地方是被整个社会保持的净土。可是农村里的人觉得他们应该分享现代化,为什么这个地方非得给外面来的人保持一块净土,这里面理解的偏差也是很大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又是很敏感的,很牵动人心,所以有时候有很多的误解和争议就起来了。敏感这个东西有时候会发展成一个社会争议,敏感就是放大镜,在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东西在你眼里就放大了,有的人如果放大自己的话这个人就很自私,他的敏感都是指向自己的,有的人是指向他人的;他很顾及他人的感受,他的敏感会放大跟其他人相处的细节,他有时候会让对方觉得很好受,但是有时候也被误解成为有点神经质。
聂永真:讲到放大,我非常认同你讲的。我们在讨论敏感不是神经质的时候,敏感的确有一点点这样,把人家完全没有看到的点扩大,有一些生活上的小事,很多人都不会感觉到,但是我可能就会想要把它强化地讲出来,希望人家多想,可是有可能我讲出来之后我还是失败的,因为真的没有人有这样的感觉。
就像这一次书里面有写到的一件事情。在生活周遭有很多大型的卖场,卖场上面都有录像。台湾在十几二十年前就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标语,会提醒客人这个地方有录像,提醒的原因就是要降低失窃率,所以会提醒客人这里有录像,你不要做坏事,但是那个标语写着“录像中请微笑”。我在十几年前还是学生的时候觉得这个文案写得非常好,它没有冒犯人,它当然可以说“录像中请你小心一点”,可是没有这样。但是过了十年之后到现在这种敏感点会跟着时间而变,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倾向于很多事情传达的真实或者诚不诚恳,当我们现在看到“录像中请微笑”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敏感了,你在对我进行录像我为什么要微笑?其实我觉得无论如何,你告知我在录像中这其实已经是冒犯了,我觉得最完美的社会的生活状态没有录像,都是在彼此互信的情况下进行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书里提到,当我后来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会觉得不舒服,我觉得这是比较矫情的修饰过的词。
欧宁:你说的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因为如果放在《1984》那本书那种环境里边你肯定对这个是没有感觉的,你之所以变得敏感,是因为你私权的观念开始放大起来了,你觉得在公共场所有个摄像头监视着你,还让你微笑,你觉得自己被冒犯了。
还是回到刚才我问你的那个问题,你除了设计还写作,这种敏感的气质如何影响你的写作呢?
聂永真:我写东西是从大二开始的,参加诚品书店的写作比赛(照理来讲,我要参加设计比赛的),那时候只是好玩,想要赚一些奖金当生活费,所以参加很多比赛。那一次只得了佳作奖而已,后来三个月后有一天我接到电话,希望我跟第一名比稿。为了一个案子比稿,我就铆足了劲,做了这件事情,后来成了诚品的文案。后来意识到自己要帮诚品写文案,才觉得好像要在生活里面找更多的题材。诚品消费族群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中产阶级以上,我完全不是那个阶级的人,作为一个学生我必须要找到非常多的符号可以贩卖给那些人,可以帮助诚品消费,在那个时候它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为了要逼自己写出东西,我做了很多案子,久了之后就变成潜移默化,很多时候周遭发生了什么事就会自动进到你的脑袋里面,你就会觉得这个可以变成什么样的题材,或者什么样的放大的发挥,所以其实后来关于每期文字都会有一些跟设计没有关系的东西,但是这的确是设计师养成的东西,因为你对很多东西看不顺眼,就想要把它写出来,光这个前提这个步骤,就可以造就一个新的设计。我是这样过来的。
欧宁:作为一个设计师,你的阅读我也挺感兴趣的。你做很多书,每本书你都看完再做,除了工作需要的阅读之外,你平时还看一些什么样的书籍呢?
聂永真:我会把书看完吗?其实不会。但是我会看基本的一两个章节,会看书的信息文字(书讯),里面有非常完整的信息,介绍这本书的脉络是什么,看完书讯基本已经可以了,看文字是帮助我们感觉到这个文字的氛围,出来的情绪是什么样子,可能跟设计还是有关系的。不看完的原因矫情一点——如果全看完我会太进入,就会跟作家一样。其实我很多时候会害怕直接对着作者,因为作者有很多很完美的想象,我觉得不应该跟他对,因为设计师有很多想象,不看完想象空间会比较大,我把这个开放出来,同时开放给很多读者做想象,这是比较矫情的一点说法;比较不矫情的说法是没有人有时间看完那么多本书。
欧宁:我在2010年做展的时候邀请过王志弘,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给行人出版社做的一些东西,因为行人出一些特别冷门的图书,他做得非常另类。在台湾这几年书籍设计的线索中,你自己做的书跟台湾本土、大陆,亚洲有什么关系?
聂永真:我们开始做设计完全没有经过台湾早期设计的脉络,我们不是从那儿一直延续下来的。对我来讲,我就是欣赏台湾早期的东西,台湾早期相关联的书籍封面受到日本影响很大,包含文字造型等等,我们这一代有的也是受到日本的影响很大,但是受到最大的影响是来自于后期其他新的设计师。
欧宁:做平面设计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困境:设计这个工作经常是别人请你去做,有点委托的意思。你的工作委托者有可能会影响你的工作?设计师在这样一种雇佣、委托的关系中独立主体性在哪?
聂永真:像我一开始接台湾《小日子》杂志(它的前两期都是我做的),后来因为后面投资者改主,我做第三期的时候接收到非常多的信息,包含他们希望我的排字、集数、大小要求,或者新的文案信息多了一些商业的味道——在《小日子》上多一点商业气息,这个味道就全变了,所以我在第三期的时候直接跟他们讨论,想要把棒子交给他们接下来的人。这个就是我自己过不了的地方,我现在会尽量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先确认清楚主管干涉的程度一定要降到最低我才会接,不要让大家互相浪费时间。
欧宁:看你有做一些独立出版的东西,没有委托者,就你自己,在这个里面获得一种完全的自由。在台湾完全有这个条件自己做一个出版社,自己出自己的书,按照自己的兴趣。
聂永真:你讲的是像编号223的摄影集或者我自己的书,其实我自己没有出版社,有台湾出版社帮我做这件事情,那个出版社的规模比较小,他们几乎不会管我做什么。我编的编号223的摄影集,既然要挂我的名字做这件事情,他们本身就会有一个基本的想法,把他们的想法减到最低,以我的想法为主,这是比较幸运的。我觉得现在无论是大陆或者台湾,这个市场或者这个产业对待设计师的尊重方式有所改变,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想找哪一个设计师做哪一本书的时候,基本上就要放给他们做了,尤其是这几年有变成这个样子,不像更早期那么惨,主管一句话,搞得大家每个人都非常不爽。
欧宁:你对自己的名字是不是挺敏感的?你刚才提到有一点,如果有一本书署名“聂永真”,你就会对这个书最后的品质非常的在意?
聂永真:翻到我的名字,如果我把那本书做很烂的话就很容易被讲,我还是很在乎这个的。有一点其实是我非常想要避免的,有越来越多的书找我做设计,设计完之后会在销售的文案上面写这本书是聂永真设计的,我觉得这个有点强化过头了,每次遇到这种事我觉得对作者非常不好意思,因为作者才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人,还有他那本书的文字。每次我看到有这样文案,都希望他们尽量把分量感减到最低,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后面的附注。
欧宁:你现在工作室有一个团队吗?还是有点像家庭作坊一样的?
聂永真:家庭作坊,我妈也在帮我。包含我总共三个人,这就算团队。非常小的工作室。
欧宁:这样可以保证对聂永真这个名字负责。
聂永真:我常常被问到接下来会不会扩大,变成一个设计公司。其实我对这点也完全没办法。我觉得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有的人梦想就是开一间公司,把一些东西做大,而因为我非常需要自由,又希望工作室出来的东西我都可以盯到,变成公司的话有很多东西我就会顾及不到,变得比较商业,这点过不了自己这关,所以一直以来工作室就是三个人以内。
欧宁:平面设计也有点像手工艺一样,如果是两三个人,哪个细节你都可以轻易照顾到;如果是大团队就变成工业生产的东西,要设计很好的管理流程、质量,要接很多工作运转这个团队,就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组织方式。我觉得平面设计完全可以用手工业的感觉运作下去,这样可以保证出来的每一本书都经过你本人的手,但是可能这样做会比较累。
聂永真:的确会比较累,我自己觉得我是不能被叫做老板的人,如果有人今天叫我老板或者经理我都会觉得非常不自在。如果变成大公司,要面对非常多这样的东西,我会觉得我的人生变得非常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