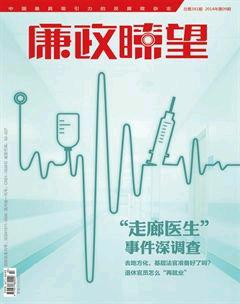争论的支点
一 个多月前,台湾惠文高中教师蔡淇华半夜难眠,给正在“立法院”“绑上头巾,春衫薄衣,热血抗寒”的女儿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告诉女儿:“青春岁月能和自己的国家谈一场恋爱,是一生最浪漫的事……能经历这一场成年礼,此后经年,一辈子的学习,有了支点。”蔡淇华此信,一度在大陆风传。
不过此信最打动我的一点,不是蔡淇华的政治抒情,而是他对女儿的一句告诫。前年他参访一所澳洲高中,遇到一名来自台湾的学生,问其在这里受教最大的心得,此人答:“这里的老师不要我用台湾二分法的方式写作文,老师告诉我,说服别人时,除了证明自己对之外,也要承认另一方也有对的部分,这样逻辑才对,也才能得分!”
相比“证明自己对”,“承认另一方也有对的部分”往往更难。我们所熟悉的争论,目的便是将对方说服,使对方抛弃他的谬误,臣服于自己的真理。这背后隐藏了一个简单而僵硬的预设:争论双方,只能有一方正确。这种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的观点,大抵即蔡淇华所嘲讽的“二分法的廉价辨证”。
比如民主与法治并不在同一条线上,而是互有交错。争论者明明只摸到一条象腿,为什么坚信自己把握了整只大象呢。唯有承认自身的有限,承认对方正确的可能性,争论才有意义,才可能引出真问题:民主与法治,哪个更重要;当民主与法治出现冲突时,我们该何去何从。
再举一例。我们为中国把脉,最终不是将病因归结于制度,就是归结于文化。由此生出两种论调,一种认为,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制度问题,只要改变制度,便可药到病除;另一种认为,中国的所有问题,包括制度问题,从本质上讲,都是文化问题,只有改变文化基因,才能正本清源。前者可谓“制度决定论”,后者可谓“文化决定论”。
事实上,哪有这么多决定论。世界原本多元,没有谁能决定谁,而是一种共生关系。倘将历史譬之为马车,它何曾独轮而行,制度与文化这两个车轮,齐头并进而不悖,缺一不可。
遗憾的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制度与文化之争,争论双方企图用一者否定另一者,一定要分出高下,这不啻是一种狭隘的表现,这种争论,可比两小儿辩日。破解之道,在于小儿心智的成熟,打碎二分法与决定论的幻象,坚守自我,同时承认对方的意义:你認为改变制度能解决中国问题,那就去改变制度,却不必否定他者在文化方面的努力;要是认为改变文化能解决中国问题,那就改变文化,也不必否定他者在制度方面的努力。
蔡淇华对女儿的谆谆告诫,让我想起了胡适。从批判“正义的火气”,到呼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数十年来胡适坚忍一心,就是要告诉人们,该如何说理,如何思想。他从不觉得自己真理在握,甚至不愿承认世间有“绝对之是”,陈独秀则相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
重读蔡淇华的信,我发现他至少两次使用“支点”一词。他说:“女儿,记得,我们正站在天平的两端,要誓死保护好天平的支点。那个支点就是——‘除了证明自己对之外,也要承认另一方也有对的部分……”这是争论的支点,对话的支点,更是民主的支点。
这同样可能成为人生的支点,正如蔡淇华对女儿的祝愿。